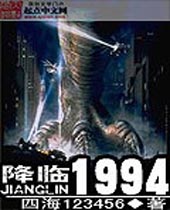5394-白星-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恶,把我上星期才买的新裤子都钩破了。”柯茨用两只手指捏住连叶子都有刺的树藤,把它拿开。“难怪我不想离开纽约,完了,现在连拇指都被刺流血了。”
“看来坐在中央公园是你唯一受得了的野外生活了,彼得。”
格雷正陪着这位纽约警官从黑熊溪上游爬下来,朝下面大约一百米的木屋前进。格雷背着枪,穿着猎鹿背心,背着背包。他们正沿着水边一条鹿踩出来的狭窄小径一前一后地走。水边有时会有大石头,溪水便在石头后面形成黑色的水池,垂挂溪边的刺刀蕨与掌叶铁线蕨显出爱达荷人引以为傲、宣称此地独有的最纯粹的绿色。微风拂柳、溪水淙淙,是典型的锯齿山树林美景。
他们来到一座水池边,水里长满植物,它们的根在泥巴里,茎叶浮在水上。格雷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塑胶袋,拔了一大把装进袋内,再装入背包。
“这是什么?”警探问道。
“水芹菜。”
《白星》 破釜沉舟掩饰不住的恐惧(2)
“它们真的长在水里面?”
“不然你以为它们哪里来的。”
柯茨耸耸肩。“超市的冷藏柜。”
格雷摇头。“小心,别让那些荨麻碰到你,”格雷弯下身躲过一丛荨麻,避免被它有毒的小刺刺到。
“我没那么城市乡巴佬,好不好?连荨麻都不懂得避开,”柯茨不高兴地说。
林中的树叶因昨夜的暴风雨而带有许多雨水,弄湿了柯茨的红领带、白衬衫和灰西装,让他裤脚也沾上了许多野藤的小刺果。
“你有没有带可以在户外穿的衣服?”
“我出差都穿西装。”柯茨懊恼地说。“你说你的木屋在山里的时候,我真的没想到是这样连柏油路都没有的荒郊野外,而且登山小径都该有扶手的,不是吗?”
格雷在两小时之前去特温福尔斯的山中小机场接了柯茨。后者在上山的车程中将三名调查局特工遭到杀害的事说了出来,格雷第一次见到柯茨的手发抖。现在,两人都觉得有必要以轻松的口气为对方打气,虽然心情其实都很沉重。
“小心,”格雷说,“河边的土很软。”
“哪里?”话才说完,他已踩进软泥中,膝盖以下立刻陷落,眼看要淹到腰部了。他忙乱地抓住一棵月桂树的树枝,想要把自己拉出来。
“来,抓着我的手上来,”格雷说。
这是一条他会走路就开始攀爬的小径,沿途的一切早已深植脑海,熟悉到认得出某块长石上新长了一丛苔鲜,某一处被大石头围起来的水塘的水比以前更绿,甚至树上原本浴缸大小的乌鸦巢可能被暴风雨刮落到其他地方,使得阳光照下来更多。
彼得·柯茨被他拉了起来,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湿脚印,湿了的长裤贴在腿上,衬衫也被拉了出来。幸好他的幽默感没有湿。“这真像几年来我带着你在纽约的黑巷里钻来钻去,这下该你得意了。”
“先生,是你自己要求到处看看的。”
“我是想让你有机会对我这城市佬炫耀。”柯茨跟着格雷回木屋去。“看你那得意的样子。你知道你跟我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吗,欧文?”
“我不敢问。”
“我了解各种犯法的勾当和罪犯,我了解生活的黑暗面,大城市的邪恶、残酷、无奇不有的浪费生命的方式,都市生活无比复杂的一面。而你,了解水芹。”
格雷大笑。
“这木棚是怎么回事?”他问。
“老了、旧了,被风吹坏了吧。”
“山上的风可真厉害,可以把木柱墙板砍成这样。”
“算你眼尖好不好?”
他们回到木屋,阳台前面停了辆中型越野卡车。虽然车子没有任何标记,但格雷知道一定是调查局的。前廊上,安雅·韦德指挥着两名技术人员,把运来的传真机、电脑等器材搬到木屋里去。接着又从车上搬了一副直径五英尺的碟型天线。
格雷嘀咕道:“我这地方快要变成休斯敦的太空任务指挥中心了。”
另有一辆黑白相间的警车停在碎石车道上,蓝色的警灯放在仪表板上方,而非车顶。警车门上有个复杂而古怪的警徽:一只麋鹿,一只抓着闪电的中古骑士铁手套,一把挖矿铁铲和一朵百合花图案。那是四十年代霍巴特高中学生设计比赛的得奖作品。霍巴特的警官靠坐在引擎盖上,看着调查局的人搬东西,其实更多的是看着安雅·韦德。
警官看到格雷时,脸上绽出微笑,跨过碎石子路走上前来,伸出手与格雷相握,另一只手则猛拍格雷的手背,笑得很高兴。
“快告诉我你终于打算回来定居,而且那边那一位是你的新娘?”
格雷笑着说:“沃尔特,我只是暂时回来一下。”
“而那漂亮的女人也不是你老婆?”
“天哪,当然不是。她是日本忍者杀手和宗教裁判所逼供专家的混合体,我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为柯茨及霍巴特的警长沃尔特·杜兰相互介绍。
“你戴着两个警徽,”柯茨指指警长胸前。“而且功业彪炳,勋章真多啊。”
“啊,我也是镇上的消防队队长,”警长拿起口袋盖上的另一个徽章,它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我还兼任卫生局局长。至于这四个勋章,是每服务五年镇议会就颁一个给我的纪念品,因为比加我的薪水便宜。我也当过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柯茨问道。
“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抓到土狼就可以领取联邦政府的赏金。记得吗,欧文?你和你爸一个月就抓到二百五十只,每一对土狼的耳朵可以领十块钱。没有人破过你们的纪录。”杜兰吹了声赞叹的口哨。
沃尔特·杜兰是格雷父亲生前最好的朋友,也是格雷一生下来,第一个赶上山来探望的人。格雷把父亲葬在霍巴特的墓地时,杜兰曾以哽咽的声音对他说,今后只要他需要父亲,就去找他。
“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这里的原因,彼得。”警长问道。
柯茨说着朱佐夫的事时,走进木屋里去。没多久,他端了一大盘三明治出来给所有的人吃。
柯茨问:“里面包了什么?”
“水芹,许多的奶油和盐。”
“没有夹烟熏牛肉?这简直像两片书立,中间却没有书嘛。”柯茨咬一口三明治。“嗯,其实还不错。”
“你为何认为那个俄国人将要到霍巴特来?”杜兰警长追问着。
“两个很简单的事实:第一,朱佐夫一路往西;第二,欧文在这里。”
“朱佐夫怎么知道欧文在这里?”
《白星》 破釜沉舟掩饰不住的恐惧(3)
“这我还想不通,”柯茨看看格雷。“朱佐夫从毕业纪念册和欧文的人事资料里知道欧文在锯齿山区长大。他可能猜到他会回到家乡来。”
“依你建议,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杜兰问。
“以霍巴特为中心成同心圆一路扩散出去,希望朱佐夫一出现,就被人发觉。”
“而你希望我也能提供协助?”警长有点心存疑问地说。“来保护欧文?欧文应该可以照顾自己。”
警官说:“我的任务并不是保护欧文,而是要逮到谋杀犯。我不会让朱佐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这个地区。”
柯茨由身上掏出一张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向警长请教这里的地形地势。七十五号公路是霍巴特唯一铺了柏油的连外道路,其他还有无数大小长短不一、通到这片山区来的碎石子路和小径。他还向对方打听霍巴特以北的那个小机场,所有可由山下小镇以徒步爬山方式溜到这里来的各种路径,还有究竟哪些地方可以架设路障。
柯茨终于得出结论:“我至少需要排两个班轮流把守各要道,每班至少要八十个人,总共一百六十人才够应付。警长跟所有附近各乡镇的警长一定都很熟,能请他们支援吗?”
警长一面吃完三明治,一面点头。“空得出来的人,都会来帮忙。”他从裤袋里掏出一盒嚼烟,问两个年轻人想不想嚼一块。柯茨和格雷摆手婉言谢绝。
他们正站在木屋西南方三十码的地方,格雷看见脚下长了些野草,就蹲下来开始拔,顺手朝右丢。警长也跟着蹲下拔了起来。
柯茨又问:“我需要借用你的设施,请问你的编制有多少?”
“编制有多少?你目前看到的,就是我的编制了。”
“什么?就你一个人?”
沃尔特·杜兰用山地腔自我调侃道:“霍巴特又不是曼哈顿,彼得。”
“局里有什么通讯设备?”
“几乎没有。因为我在外面跑时,警察局里就没人了;而我回到警察局时,外面也就没人了。”
柯茨蹲下来学着他们拔野草。“霍巴特警察局有什么我能用的吗?”他问。
“只有二十个塑胶制的橘红色路锥。”
“我的天,只有这个?”
“还有四具折式路障,一辆警车,四把各种不同的枪,一间只可关一个人、却连笨蛋都可以逃得出去的牢房。”
柯茨摘下眼镜揉揉发红的鼻梁。“贵局可以接电源吗?”
“那倒是有的。至于邮件嘛,只要冬天河水结冰,雪橇车通得过,偶尔也是能收到的。”
警长和格雷仍在拔着野草,而且越堆越高。再过去,靠近山沟的那边,野草就变成另外一种又高又尖、而且会割伤手的野藤了。
“你还帮得上什么样的忙呢?”柯茨问。
“我可以通知所有的居民,要大家把眼睛放亮点。任何陌生人进来,我立刻会知道。”
“今晚以前,算得出可以动员的人数吗?”
“我尽力。”
柯茨由口袋里掏出小记事本,讲了一大堆若发现朱佐夫的行踪应该如何联络,所有有关人士又该如何分布接应的细节。完全是大城市里特警队那一套。警长撅着嘴猛点头。
柯茨收好记事本之后,忍不住问道:“我很不愿意再次暴露我的无知,但两位为何不停地拔草?”
“这不是普通的野草,”格雷边拔边回答。“这是野麦。”
“野麦不是应该收割的吗?为何把它连根拔掉呢?”
“你看它茎干上长的芒刺,若被动物吃进去戳在喉咙里,会害得它被割伤,发炎致死。以前我养的一头骡子就是吃了它,等我发现,它已经因为喉咙发炎来不及救治了。”
柯茨拔起另一株野麦。“可是,你这里既没有骡子也没有马了呀?”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格雷仍继续拔草。
“我们都是讲究原则的人。”警长说。
柯茨站起来。“你们是两个喜欢拿我这个城里人开玩笑的家伙。不过据我看,在这片山里唯一的好处,就是随便往哪个方向走出去三十英尺就可以撒尿。”
柯茨往后面的野草堆走去,双手分开野藤往里走,他回头看见木屋边的安雅被一棵山月桂遮住,就拉开裤裆办事,一面还回头说:“在爱达荷上厕所不必花钱,真好。”
两个站在野藤堆外的人听着柯茨满意的轻哼和液体落地的声响。
杜兰警长咂着舌头问格雷:“你跟他说,还是我来?”
“能分享坏消息的人,才是好朋友。”格雷朝警官大喊:“彼得,你还好吗?”
“好极了,卸除体内负担是人生一大乐事。”
“真的吗?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等会儿你就需要治皮肤病的碳酸锌洗液了。”
柯茨傻愣了一下,突然大喊起来。“我的妈啊!怎么办?”只见他高举着双手拼命乱甩,似乎想甩掉手上的毒液。他扭头大叫:“我的天,现在我该怎么办?”
警长告诉他:“我会先把‘小彼得’收进裤裆。”
“可是我手上现在有毒,我不敢再碰啊!”
“想办法别用手碰到,再多沾一些毒液,它会肿得跟曼谷菜花一样可怕。”
“千万别叫我帮你做这事儿,”杜兰警长板着脸忍住笑。“我可不一定逮得住它呢。”
柯茨总算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把它硬塞回裤子里,小心地拉上拉链,然后又高举着双手转身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穿了袜子吗?”警长又问。“否则你的脚马上也会肿起来了。”
“我当然穿了袜子,赶快想办法救我出去啊。”
“就像刚才走进去一样,走出来就是了。”格雷说。“手举高就行。”
柯茨终于踮着脚尖走了出来,一出来就质问格雷:“你怎能看着我走进毒藤堆而不叫住我?”他用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的手背。“我的手已经开始痛了。”
《白星》 破釜沉舟掩饰不住的恐惧(4)
尼柯莱·朱佐夫以生硬的英语慢慢说:“回你车子,开走,你就可以活命。”
这句话就像《圣经》里的《启示录》那样,天打雷劈般当头罩下,鲍温发现他拿着致命的武器,对准四十英尺外一个应该是没有武器的人,但对方的警告让他发现他刚出生的女儿不必在今天失去父亲。脑后的钟突然不再发出可怕的滴答声了。
罗斯慢慢把枪朝天举起、自车门上收回,再慢慢地缩回车子里坐好,把枪放到旁边座位上,发动引擎,在公路上紧急回转,加速朝反方向疾驰而去。由后视镜里,他望见俄国人坐回车子去。等他开过一个高坡后,就看不到那辆银灰色轿车了。
骑警弯腰捡起女儿的相片,放回仪表板上。他把无线对讲器抓到手上,打算按下通话钮报告他没有追上俄国人。他自嘲地笑了一下,生命很少给人那样清晰的选择,他认为自己刚才的决定非常正确,他要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他值完这个班后还能看到他。
“我通常不吃我的手拿不起来的东西,”安雅戳戳她的晚餐。
烤马铃薯几乎要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