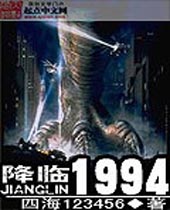5394-白星-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奥兰多,再给她们三天,”格雷说。“假如我忍受得了,你也应该可以。”
“可是那味道实在太难闻,”奥兰多的手在脸前搧着。“简直快把我熏死了。”
两个女孩为了寻根,哄奥兰多替她们买了一罐正宗韩国泡菜,而且坚持要吃一个星期,整个星期下来,屋子里全是冲鼻的泡菜酸味,取代了奥兰多的海地菜味道。
奥兰多来自海地,格雷面试她时,要她拿出绿卡好去登记。奥兰多只拿出一张照片,那是她的老家附近,一条土路边几间用防水纸当屋顶的茅屋,垃圾堆旁的晒衣绳上挂着一件千疮百孔的破衣服,她以蹩脚的英文说:“这是我唯一的文件。”格雷觉得这就够了。
奥兰多仍然穿得一身的五颜六色,格雷曾在圣诞节送她一条有铃铛、小鱼饰品和贝壳的银链,她戴上去后就不曾拿下来,走到哪里都叮作响。她的肤色较深,可是眼神永远带着笑意。孩子们都很爱她,但是对那套她在他们不乖时拿出来吓唬他们的巫毒法术还是心存畏惧。她有唱歌的天赋,格雷认为双胞胎的音乐能力来自她播下的种子。她也总在约翰为自己失去的手哭泣时,充满耐心和爱心地安慰他。她唯一的缺点是偶尔会失踪一个下午,那通常是因为她交了新的男友,却谎称患了谁也不清楚那是什么的“海地疹子”而请病假。格雷相信她那些男友后来都被她连皮带骨头地吃掉了。
“爸,你今天的心情有没有好一些?”洛琳问。
格雷拿开堆在沙发椅上的东西,端着茶坐下来。他无法对他们隐藏狄塞罗案的败诉引发的沮丧,他把持杯的胳膊放在陈旧的沙发扶手上。
“好多了,”他的声音像在叹气。他松开领带,露出颈间一块少见的紫色皮肤,探身捡起地上一本课本。“等一下那位叫柯茨的警官要来找爸爸,你们把这里收拾一下好吗?”
“爸,你们要检讨那场官司是怎么输的吗?”茱丽问道。
“你真会说话,”格雷喝口茶。“我们并没有输。”
《白星》 孤星高照怕狼,就别走近森林(5)
“《纽约时报》说你们输了,”洛琳还在取笑他。“那篇社论说你和你的老板搞砸了。”
“约翰,别再摇你爸爸的手提箱,”奥兰多转身回厨房时,制止约翰。“你会把东西弄坏的。”
他们住的公寓位于布鲁克林区一个叫湾脊的地方,附近有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开的小餐馆和披萨店,坐地铁要一个钟头才能抵达曼哈顿的办公室。公寓里的家具都很陈旧,当年离婚时,幸好他及时换了锁,剩下的几块地毯和结婚照才没有被他的前妻莎琳搬走。更好的是,他的三个小孩都没见过那个泼妇。
这时门铃响起,格雷起身去按对讲机,证实是柯茨才按开楼下的遥控门,让访客进来。他不知柯茨为何突然来访,查狄塞罗案的这两三年,柯茨从未主动找过他。
“我们或许应该警告奥兰多一下,”洛琳看看厨房的门。“来的是个警察呢。”
茱丽笑起来。“也许她该从防火梯逃掉。”
格雷挥手制止她们的胡闹,拉好领带走去开门。柯茨正一脚跨过三楼的最后几级楼梯,他的块头大在胸部而非腰部,所以步伐相当轻快,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其实我早就到了,只是去吃了几片奶酪蛋糕,真该在你进门之前逮到你来替我付帐。”
格雷笑着让柯茨进门,办狄塞罗案的三年期间,一起吃饭时柯茨从未自己付费,他的理由是:“我从未利用职权捞外快,至少要吃回来。”
两个女孩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纽约警官,睁大了眼睛猛瞧,约翰则站到格雷沙发椅旁的专用位置。
“好漂亮的孩子。”柯茨坐到沙发上,嘴角还黏了一小粒蛋糕屑。“看来府上就有一个具体的微缩的第三世界。”
从查狄塞罗案开始,柯茨就一直是一副邋遢样。格雷以为那是他的伪装,后来认为他的粗野大概是与生俱来的,但柯茨一再证明他的调查能力。例如为了查艾斯帝的赌博资料,他曾带了强力弧形灯不眠不休地在史丹顿岛的垃圾处理场翻找了四十八小时。还有一次在跟踪狄塞罗时,因为车子突然抛锚,他竟然拦下一辆公共汽车,逼司机去追狄塞罗的凯迪拉克,由曼哈顿桥飙进布鲁克林,一车乘客差点暴动。就算在零下五度的一月天,柯茨也照样在狄塞罗的牙买加湾外面值足十小时的班。第二天早上,急诊医院的医生只好把柯茨冻坏的小脚趾切掉。
柯茨对帮派分子的痛恨也令格雷很是佩服,一律以“杂碎”称之。他在出庭作证时,也这样称呼狄塞罗。辩护律师曾当庭提出抗议,要求定为误判,法官当然予以驳回。格雷对柯茨这位嫉恶如仇的警官也因此越发欣赏了。
柯茨一坐下来,就先踢掉左脚的便鞋开始按揉。“这天杀的脚实在很累人。”
约翰因这粗话猛吸了口气,两个女孩对看一眼,表示她们听过格雷严格禁止他们说的这些话,奥兰多则打开门缝偷看。
“欧文,你还真冷静,‘唐山佬’倒下去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走了,好像你的血管里流的是冰。”柯茨开口道。
格雷张开双手,没表示什么。当天下午他回想当时的情景,也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有点心寒与愤怒。看来他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天天搞得自己筋疲力尽、困惑迷惘,而且付出沉重的代价想要恢复正常,如今证明全都白费功夫。一个健康的人应有的反应或许该像安娜那样:全身发软,又晕又想吐。
“欧文,我知道你的手脚有很多伤痕,”柯茨又说。“但是你和我到健身房去的第一次,我曾问你脖子上的疤是怎么来的。你说那是大学时吃东西不小心被火腿卡住,救护人员割开喉管留下的。最近我问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气管切开术不会留下那么大的疤,所以我好奇地调查了一下。”
三个孩子全都静静地看着警官。
“我当年若能像现在这么勤快,早就当上纽约市长了。”柯茨说。“欧文,纽约警察局里的人都只认为你是个很拼、很正派的检察官。只要碰上你的案子,就会搞得我们疲于奔命。”
双胞胎站近了些。
“爸,你真的是个很正派的检察官吗?”茱丽缠上他了。
“我们早就知道你一定很厉害。”洛琳也不甘示弱。
格雷警告她们。“厉害到足以把爱插嘴的你们送上少年法庭。”
警官接着问:“你有啤酒吗?”
格雷摇头。约翰站在原地说:“我们的冰箱里有美禄。”
“看过联邦调查局送来的资料让我反胃,真的没有啤酒?”柯茨问。
“彼得,你为什么对我服役时的资料有兴趣?”
洛琳问:“为什么那个疤会让你觉得反胃,它只是一块紫红色的厚皮肤而已啊。”
警官问女孩:“你们老爸说过那个疤怎么来的吗?”
“是一条水蛭害的,”茱丽回答。“那没什么,我们韩国人拿水蛭当早餐吃呢。”
“我的孩子都知道那次意外。”格雷说。
“那当然,”柯茨把鞋套上。“有一天你在越南丛林里拿起水壶,大喝一口。谁知壶里有一条你灌水时跑进去的水蛭,它进入你的喉咙咬住不放,因为吸了你的血而身体膨胀,逐渐堵住你的气管,使得你无法呼吸。可是你的瞭望员不在附近,没有办法帮你。”
洛琳插嘴问道:“瞭望员是什么?”
“水蛭使你脸都青了,你只好拿刺刀在喉管上挖洞,又割了根竹管插到洞里当气管。呼吸虽然畅通了,还是没办法把那条水蛭挖出来。”
约翰很快走出来。“我要去找奥兰多拿美禄。”
“当时你在北越军和越共出没的敌后,最后你走了两天两夜才由敌后逃出来,到一个美军医护站急救,才把高高兴兴在你喉咙里吸得肥肥胖胖的水蛭取出来。”
两个女孩微微笑着。
《白星》 孤星高照怕狼,就别走近森林(6)
柯茨对两个女孩说:“我不知道你们会感觉怎样,不过如果我的喉咙里有一条水蛭,我会非常难过。”
约翰拿着饮料从厨房出来,把它和一根吸管交给警官,还不忘提醒:“拉开拉环,把吸管插进去。”
柯茨喝了口饮料。“虽然不是健力士啤酒,不过很好喝。孩子,你的手怎么回事?”
约翰看看爪状的义肢。“我忘记了。”他灵巧地用爪子前端在罐子上弄出一个洞,插入吸管。
“瞭望员是什么?”洛琳又问。
“你爸在越战时,是美军陆战队第一师、第四大队的狙击手。”
格雷立刻转向几个小孩。“孩子们,我和柯茨叔叔有重要的事要私下谈,请你们回房间去。”
他们听得出他认真的口气,立刻乖乖地消失了。
柯茨一口喝完饮料。“要是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匡地科(译注:联邦调查局训练学校的所在地)训练中心的某个靶场以我的名字来命名,我会非常骄傲。”
格雷的回答依旧冷漠。“我不认为你真的会感到骄傲。”
警官仍不放弃。“我今天下午打了个电话去那个靶场。你的一位老朋友、那里的中士亚伦·艾柏说,直到现在他们还时常提起你。他说,你是个传奇。”
格雷摸摸下巴。“或许吧,但那些日子早已过去了。”
“跟中士长通过电话,我还以为一进门就会看到壁炉架上放满你的‘温布尔顿’奖杯。”他打量了一下客厅。“但你家既没有壁炉,也没有可以放奖杯的好桌子。”
他的眼光移回格雷脸上。“我问这位海军中士,是不是指英国那个网球大赛的温布尔顿杯?他差点笑死,骂我没见识,告诉我‘温布尔顿杯’是指一年一度在俄州培利营区所举行的全国一千码步枪射击锦标赛,他说,你曾连续三年拿到总冠军。”
“我平常很少谈这种事。”
“你知道我当年在陆战队的绰号吗?”柯茨问。
“只能想象。”
“‘弹簧指’,我一分钟可以打出十五个单字,陆战队就叫我到基地去当打字教官了。我如果能用你的绰号‘白星’,不知会迷死多少女人!”
格雷没有出声,柯茨接着说:“艾柏中士告诉我,越共因为你总是留下一个用白纸折成的星星而称你为‘白星’”。
其实是先有绰号,才有纸星星的。在他出击的早期,敌人已因这名狙击手善于利用黄昏余晖而开始称他为“白星”。陆战队的狙击手都知道两句由水手的歌诀改成的打油诗:夜间天空红,乐歪狙击手。黄昏时刻那粉红、红色和紫色的暮霭,容易使得躲在丛林中的目标提早离开树林或灌木的掩护。初降的暮色给人一种幻觉,以为四周昏暗,别人看不见他们。其实他还是比四周的景物明显,替狙击手定位的瞭望员很容易就能从望远镜中看到目标。格雷总能利用天边刚出现的“白星”的光芒,从远距离望见丛林中移动的物体,只要有任何反光,就能命中目标。西方人称这颗提早出现的亮星叫“黄昏之星”或“金星”,越南人称它为“白星”。
有一次执行任务时,苦等了三十六小时,格雷无聊地从他的狙击记录簿上撕了一张白纸在手边折了又拆、拆了又折,胡乱地实验各种设计。他的下士瞭望员看到后说:“你折了一颗星星,正好和你的绰号吻合。”他完成那次狙击任务时,就把那个纸星星留下了。此后每次任务后,他就留下一颗星星,如果可能就留在尸体身上。
格雷后来才发现历史上许多有名的狙击手都曾留下某种类型的‘名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拿大二十一远征师的印第安裔狙击手约翰·柏达虚,在每次任务后留下一根羽毛。美国内战时,北卡罗莱纳州第十八军被人称为“合唱员”的班恩·波顿下士,宣称他可以从敌军射击过来的子弹方向准确地推算出敌人藏身的距离,再用来作为回击的依据。他总是留下一根松鼠尾巴。
当年法军在“奠边府战役”被越南游击队击溃时,有个越南游击队的神枪手能从地面打死天上飞过的法军驾驶员,那名神枪手每次都留下一段麻绳编织物。至于史上记载的头几名神枪手之一则是达芬奇,他在威尼斯城被敌人包围时,曾用他设计的步枪打死了几名士兵,至于达芬奇有没有留下什么标记,就没有人知道了。
“听说越共曾悬赏一名士兵五年的薪水当奖金,要取你的人头。”柯茨又喝一口饮料。“后来甚至在各地张贴你的画像,到处悬赏。他们从哪里拿到你的画像呢?”
格雷对于柯茨坚持要谈的话题逐渐认命。“我猜是由美军陆战队周刊上的一张照片复制的。”
“所以你总共歼灭多少敌人?”
格雷抬头望向柯茨头上的墙面,那里贴了几张约翰的蜡笔画,画里的天空都是红色的。“没几个。”他说。
“才怪,”柯茨大笑,那声音好像用树枝扫过尖尖的木头篱笆。“九十六个算没几个?艾柏中士说,这是美军战史上的最高纪录。我问他你为何退役,他说不知道,也可能是不肯说,各种人事资料上也都没有。”
格雷回答:“服役期满就退役了。”
“不对吧,”柯茨追问。“你二次返回越南,在服役期满前两个月由医疗机构送回圣地亚哥。”
约翰房间的门打开,他从房里出来,直接走到警官面前。他似乎很喜欢这位直率的执法人员。男孩问他:“你要再喝一罐美禄吗?”
“好啊,最好加一些伏特加。”
“没问题,我最爱伏特加了。”约翰笑着向厨房走去。
格雷起身拦住儿子,轻抓男孩的肩膀把他转过来。“你最好告诉我,你这辈子从没尝过伏特加。”
“我跟警官伯伯一样,每次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