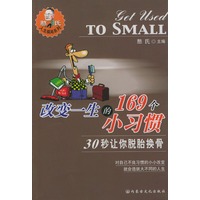4269-红碱草-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就是这个潮流,谁能不跟着?”郑义平手摸着满脸的胡子,想了想说,“我看哪,今后招工还能有。写的不一定不走,不写的也不见得能走。”
我看着郑义平:“那我写吧。”
回到宿舍,我从箱子里翻出方怡玫送给我的那支钢笔。手握着这支钢笔,只觉得沉甸甸的。我又想起方母的临终遗言,想起了与方怡玫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内心泛起一阵阵酸楚。方怡玫没写什么申请,却实实在在地扎根了。哎,这年头——扎不扎根由不得自己。我提笔写了扎根申请。
第二天,召开全连大会。达子说:“别的连人人都写了申请,咱连就胡立仁等个别人没写申请,扯了连里的后腿。对胡立仁要批评教育,提高认识。”
达子没点杜金彪的名,算给他留个面子。胡立仁却小声嘟哝着什么。
这些天下地干活,就是清理上下水沟泛上来的沙子。这沙子真细,真密实,一桶锹下去,只能撮上来一小块,比挖土方可费劲多了。每人一天分二十多米,累得胳膊酸痛。
胡立仁拿着桶锹,边挖边发牢骚:“这破活,真他妈累人。这地震要不然震大点,地都陷进去,就不用清淤了。”
杜金彪瞅着他:“震大点?不把你也埋地里啦,那你可就彻底扎根了。”
“埋里更好,省得成天清这破沙子。”胡立仁说着操起桶锹向下一挖,忽然大叫一声,“哎呀,什么玩意儿,这么硬?”
我一看,胡立仁从沙里挖出一块石头,再瞧他的桶锹,当时就卷了刃。
胡立仁气哼哼地说:“谁这么缺德,往沟里扔石头,这锹还能用吗?”
“嘟——”上午收工的哨音响了,达子大喊着:“收工啦,今天下午全营在俱乐部开会,不许缺席。”
俱乐部内,集中了全营的知青,台下黑压压一片。
水泥砌的台子上挂着横幅:“扎根农村干革命,誓叫卫红换新颜。”
台上摆着一张用红布蒙着的破桌子。台子的一侧坐着崔红英等几个人。
吴大山站在桌前,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我营在这里召开扎根农村誓师大会,农场革委会对这次大会高度重视,牛主任在百忙之中参加了这个会。让我代表全营的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对牛主任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
掌声过后,一个长得像个地缸子似的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挥了挥手。
吴大山说:“你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改变盘锦落后面貌,出大力,流大汗。现在又响应号召,主动提出扎根盘锦,特别是崔红英同志提出了‘扎根农村六十年,不死再干二十年’。对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代表营里表示热烈的支持。非常荣幸的是,崔红英被农场树立为扎根典型,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营知青的光荣。”
呱唧呱唧的掌声再一次响起,只是参差不齐。
吴大山摆了下手说:“下面请牛主任为崔红英颁发奖状。”
牛主任来到桌前,崔红英随之跟过来。牛主任拿起桌子上的一张盖着农场革委会大印的奖状递过来,崔红英郑重地接过奖状,向牛主任敬了个礼。
牛主任紧紧握着崔红英的手说:“你是我们农场的骄傲,我代表农场革委会向你表示祝贺。”
牛主任随即转过身,面对台下大声说道:“这个啊——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非常成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这个这个啊——你们自愿扎根农村,这很好嘛。我没什么准备,只是希望,这个这个啊——大家都能说到做到,用行动去实践扎根农村的诺言。这样嘛,你们会有更光明的前途。这个这个啊——我们国家才能永不变色。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是不是让小崔表个决心啊?”
吴大山朝牛主任点点头,牛主任迈着八字步回到台侧的椅子上。
崔红英精神抖擞地站在台中央,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慷慨激昂地宣读了她的扎根申请书。
会后,崔红英同牛主任等人一起来到了营里的小食堂。有人看见崔红英坐在牛主任身边,频频向牛主任敬酒。
崔红英喝得小脸通红,一直陪到深夜。
胡立仁跑到我屋,对杜金彪说:“母猴子这回可出风头了。跟那个什么牛主任坐在一起喝酒,脸喝得像猴屁股。你行吗?”
“跟地缸子喝酒算啥,说不定还陪着睡觉呢。”杜金彪说,“你真他妈的少见多怪,这有啥出奇的?”
“啥出奇?人家这是能耐。”胡立仁眼珠一转说,“能跟农场革委会主任在一起,以后办啥事不痛快?”
第六部分收工后(1)
第二十八章
这天收工后,我顶着西斜的太阳往回走。已过了立秋,天仍很热,火辣辣的太阳不愿下山,再有一个多月又开始挥镰收割了。
黄来宝从后面赶上来,悄悄对我说:“白剑峰,今晚到俺家去吧,昨晚俺照了成是多的螃蟹啦。”
“行啊。有些日子没上你家,正好看看你爹。”我兴奋地一拍他的肩头。他的妹妹黄喜凤在后边跟着,偷偷瞅着我。
黄来宝跟他爹黄树川秉性相近,耿直憨厚。他瓦刀脸,皮肤黑黄,小眼睛黑亮黑亮的。他与我同岁,个头比我稍矮。他们家人都在二连干活。他上工时愿意跟我一起干活,彼此混得熟了。他母亲驼背,身体不好,在家呆着。每次知青来,她都格外热情,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
我简单洗了把脸,甩掉潮湿的水田靴换上布鞋,到小卖部买了一瓶地瓜酒,径直来到黄来宝家。
这是土坯砌成的三间房,低矮昏暗,炕上的破苇席有几处用旧麻袋打着补丁,比青年点条件还差。我头一次进他家时,就感到不解,黄树川好歹是队长,家里咋这样?有人去过黄树山家,三间红砖房,好大一个院落。城里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一应俱全,烟酒不断。两相对比,黄树川家实在寒酸。而黄树川与黄树山两家几乎没什么来往。
我环视这屋问:“黄队长呢?”
黄来宝说:“你问俺爹呀,刚出去,听说三连有个知青病了,他赶马车送医院去了。他一天到晚长在连里,不到半夜不回家。”
“黄队长可真忙啊!”我感慨着,从心底里钦佩黄树川。
黄来宝递过旱烟,我卷了一支。刚抽一口,就呛得受不了。这烟可真冲,原来是吉林的蛟河烟。我说:“抽这烟得抱电线杆子,不然得呛个跟头。”
黄来宝因与兴城迁来的农民住得近,口音上受其影响,他操着兴城与盘锦混杂的口音说:“这烟冲逗(就)是好,一支顶两支。烟卷抽多了咳嗽,这旱烟抽多少也没事。抽习惯就好了。”
“小白呀,快来吃螃蟹。”黄母驼着背,端来满满一盆冒着热气的螃蟹放到炕桌上。
“来,上炕吃。”黄来宝说着上了炕,我随后脱了鞋也盘腿坐在炕上。
黄喜凤进来了,她从盆里挑出一只大螃蟹递给我:“白大哥,你快吃呀。”
黄喜凤几年的工夫已出落成大姑娘。她圆脸,梳着俩小辫,额前留着刘海儿。脸红扑扑,两眼水汪汪。她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常向我打听城里的情况。有一次,我向她讲起了城里的高楼大厦,讲热闹繁华的中街、太原街,讲故宫、北陵、东陵……她听得那样专注,仿佛在听神话故事。她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大城市的向往。
黄喜凤就坐在我的旁边,默默地嚼着螃蟹。我心想,以后我真的能抽回城挣钱了,一定满足这位农村姑娘的心愿。请她全家到沈阳多住几日,让她看看大城市啥样。
“哎,白剑峰,俺听说,过两天,连里男青年都到东风农场修大堤。”黄来宝瞅着我说,“今早,达子征求俺的意见。你说,俺去不去?”
这两天,我也听说要出工修大堤。尽管我没去过,但郑义平讲过,那活累得你趴下就不想起来。看来黄来宝没干过这活,心里没底。我想了想说:“出工修大堤工分肯定高,又是白吃,可我听说那活也真累,恐怕你吃不消。”
黄来宝眼睛眨了眨,寻思了一会儿,说:“可也是。那明儿个俺告诉达子不去了,就在家里干零活吧。”
我说:“对,你跟我们知青不一样,在家干点轻俏活儿,没事摸鱼抓螃蟹多好哇。”
“嗯哪,可也是。”他瞅着我,嘴唇嚅动了一下,想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我诧异地望着他说:“有啥话你就说呗。”他想了想说:“哎,白剑峰,那天俺看见几个兴城老娘们儿议论方怡玫的女儿黄雪芳。”
“她们都说啥?”我放下正要伸到嘴里的螃蟹问道。我知道这些农村妇女凑在一起就爱张家长李家短地嚼舌头。
黄来宝仔细端详着我:“她们说黄雪芳长得像你,黄树田当了王八。”
“这些老娘们儿没事就爱瞎琢磨。”我瞅着他说,“她们有啥根据?”
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天去方怡玫家看雪芳,黄树田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对方怡玫说话也不耐烦。我心里纳闷,这老土咋啦?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些老娘们儿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我看着黄来宝,问:“你信吗?”
“谁知道哇?”黄来宝的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两遍,“别说,俺看雪芳的眉毛、眼睛、嘴角像她妈,可鼻子、下巴还真有点儿像你。”
“哥,你别跟她们瞎猜,”黄喜凤眨着眼说,“俺听说谁常跟小孩在一起小孩长得就像谁。白大哥常看小雪芳,那孩子就长得像,这有啥出奇的。”
我不再言语,低头默默嚼着螃蟹,心里却忐忑不安。这黄树田难道真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顿感心烦意乱,草草地吃了一个大饼子,就走了出来。
翌日,达子告诉我们,明天全营的男青年都到东风农场修辽河大堤,任务相当紧迫。真要出工修堤,我心里倒没了底,难道真像人说的那样累吗?
第二天,全营出动所有的马车、“小蹦蹦”,颠簸好长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当地老农家已经住满修堤的人,我们连只能住到附近的小学校。在一个大教室的地上铺满稻草,我们的行李就铺在上面。尽管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但仍能感觉到地上的潮气浸满了被褥。
小学校距大堤有二里多地。我们来到修堤工地,那场面真是浩大。
大堤上下,成千上万的人往来穿梭着。堤上堤下,插着的红旗被秋风刮得呼啦啦乱舞。
我飞步蹿上大堤,举目观望,堤面可以并排跑两辆汽车,足足有二层楼高。堤下是辽河,宽阔的河面,涌动着浑浊的河水,这大堤绵绵不绝,望不到尽头,像长龙卧在河边,抵御滚滚而来的河水,护卫着成千上万亩稻田。
站在堤上俯瞰,远望穿梭的人群,密密麻麻,像爬动的蚂蚁,人在大堤面前变得如此渺小。可正是这些渺小如蚂蚁的人群,一锹一担一车地用土堆成这壮阔的大堤,展示着人类无穷的威力。
为了大堤的安全,我们要到二百米外的地方取土。达子、郑义平、老黑他们推着装满土的独轮车,飞跑着向堤上冲去。我和谢元庭将一个麻袋的四个角用麻绳系紧,拴在长长的扁担上,然后担起向大堤走去。
这土方死沉死沉,将扁担压成了弓形。肩膀生疼,也得咬着牙挺着。到了大堤上,放下扁担,我俩抓住绳子用力一抖,那麻袋里的土便落下来,只有一小堆。在宽阔的大堤上,这点儿土是那么微不足道。这大堤至少要加厚一米多,多少人就这样将一堆堆的土,像蚂蚁搬家似的从远处移到堤上。
第六部分收工后(2)
何小海、魏实俩人抬着土上来了。何小海眼皮耷拉着,紧咬着嘴唇,魏实瞪着眼睛,龇牙咧嘴。他俩刚刚倒下土,一辆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他俩一闪身,推土机从身边碾过,本来好不容易搬上的土,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堆起来的土已有半尺,经这个铁家伙一压,剩不到二寸。
魏实看傻了眼,嘴里嘟哝着:“人家费半天劲儿整上来的土,让这家伙一压,没了。这得干到啥时才能达到一米多高哇?”
达子推着独轮车上来恰巧听见,冲他说:“这新土不让推土机压实能行吗?那洪水上来不一下子就冲垮了。”
“这……”魏实瞅着达子,欲言又止。
达子手扶车把,向前一拥,地上立刻凸起一大堆新土。我一看,这些土足够我和谢元庭抬三趟,看来还是独轮车效率高啊。
达子抹了一把汗水,对魏实和何小海说:“你们新知青头一次干这活怕吃不消,不行就少装点。”“嗯。”他俩没精打采地应着,拖着扁担朝堤下走。
“看见没,剑峰,”谢元庭对我说,“这新知青就是不行。咱俩抬的比他们多不少呀,也没像他们那样。”
“别说他们,咱们刚来时,干活也不适应。”我说,“这几年锻炼得啥苦都能吃了,你说怪不怪。”
“哎,你累不?”谢元庭瞅着我说,“要不咱俩找个地方歇会儿再干。”
“大家都拼命干,咱们也不能让人看出落后哇。”我说,“鞍山小青年都管咱叫老青年,咱得干出个样子让他们瞧瞧。”
“行了,别说了。”谢元庭不满地瞥了我一眼,“你干得再多能咋样儿?哼,跟你干活就是累。”
“我不知道累呀?”我说,“一会儿,我也推独轮车,你跟别人担去吧。”
“想把我甩了?”他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放下扁担说,“我想试试独轮车,你看他们推得多带劲儿。”
“你?”谢元庭眨眼瞅着我,“那可不是好玩的,没两下子,准得翻车。”
前面正停着一辆独轮车,我过去让人装上了满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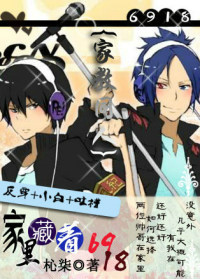
![(仙剑五前传同人)〖五前〗[轩离-红紫]别经年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