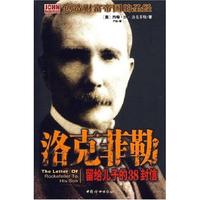3860-罪的还魂术-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睡着。他看了看那个女孩,耸了耸眉。女孩脸上的脂粉经过一夜已经完全褪去,要想辨认出她是谁着实有些困难。而那个男子仍在打着鼾。
金头发男子弯下身去,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夜壶放在身前准备小解,目光落在了他放在地上的那把剑上。他将剑捡起并置于附近的一张圆桌上。接着他走到窗户那里拉开了厚厚的窗帘向外张望。窗外明媚的阳光洒满了整个花园。
这样她便对那些埃隆街的夜间来访者心存细微的宽容。
一天天、一月月的过去,她对这个亚西比德越来越反感。她不仅常瞥见他的身影,而且在某一天或某两天的夜晚还能听见那条著名的猎犬从她丈夫那里发出的吠声。她最后先是取笑苏格拉底的孩子们,然后又只好祝愿苏格拉底能找到一位既深情又忠诚的男伴。但是,对一个牧羊人的女儿来说,一个会向窗外扔那么多钱的男子,那样一个没头脑的家伙不会是一
个和善的人。要知道,那些钱可以买一条犬,买一条值5个斯塔特尔的犬啊!她去找她母亲说知心话。那是一天清晨,她母亲正在缝补一件旧长衣。
“不管怎么样,”赫拉像只乌龟那样皱起眼睛对她说,“我们不会了解男人,更不会了解丈夫。几句话、几个成员、几把剑,这便是男人。”
她将针插在衣物上,然后呆呆地望着粘西比说:“关于亚西比德,我的女儿,你有时应该听听外面的谣传。那个据说俊美异常的男孩曾经跟你的丈夫一起打过仗。”
粘西比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这就是秘密所在啊。她用了点时间消化了一下刚刚得到的信息,然而不同于她丈夫哲学的是,她决定在忽视中寻求幸福。她的父亲,那个牧羊人有时说过:“那些你不能改变的东西,就忽略它们吧。”但人们总认为牧羊人与哲学是沾不上边的。
一天早上,天气不错,她的耳边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她开始不安起来。她跑出去看个究竟。就像以前一样,孩子们在小巷里玩球。突然,他们全跑了回来,哥哥对她说:“妈妈,街上有个死人。”
一个才四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那是个死人呢?她把洗了一半的衣服扔在一边出去看看,没错,是有一具死尸。他的姿势像坐在大衣上,背靠着屋墙,目光紧锁一处。她看了看这是不是哪个死了几天的女人,离得远远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死尸更不洁净的了。那是一个30来岁的男子,很英俊。深色金黄的卷发柔软光滑,像是在早上刮风时应该还活着。当她将他的手臂轻轻抬起并放下时,还依然很柔软,看来他死了并没有多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失去光泽。她大着胆子将它们合上,心却因为希望和恐惧这一对矛盾的感觉怦怦直跳;如果他是亚西比德呢?他的长衣已被乌黑的血弄脏了,不难看出致命的是插在左胸上的一把匕首。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人,不,她并不认识他。她只是有印象曾在哪儿见过他,但也可能是搞错了。
他本应死在战场上的,但现在却死在了街上。这是怎样的差别啊?
前传 辉煌的落日 上埃隆街凶杀案(6)
苏格拉底此时早已去见伯利克里了。她派奴隶去叫他然后去通知邻居们。他们过来争先恐后地重复着同样几句话:“他真英俊!但他是谁呢?”粘西比的心情很沉闷,这一发现似乎是某种不好的先兆。一只死去的鸟已然不是什么好预兆了,何况是一个死人呢……
两个钟头后,士兵们过来把尸体载上独轮车运走了。人们把他放在了宙斯斯托阿广场上,就在迪比隆门旁。这是处理无名尸体的一般风俗,为的是好让他的家人过来认领。事实上,一小时后,死者的父亲和几位近亲辨认出他正是菲利皮季,薛尼亚德的大儿子,是500人议会(本页涉及的雅典的主要民主行政机构:500人议会,500人分别由10个部落选出,每个部落50人——是最高的合法权威组织;10将军会,由每年重新选出的10位议员组成,每个部落1人——由它确定帝国的对内对外以及军事政策并对官员进行监督,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的民主行政机关。阿雷奥帕奇是民主雅典的私人法庭,只断谋杀案及亵渎神灵案)成员之一,与伯利克里同住于肖拉尔戈斯区镇。粘西比刚从集市回来,人们便认出了她,说她正是发现被害者的人,并围过来安慰她。至少有30个妇女还流了泪。不管发生何种情况,人们总是蜂拥而上,粘西比对此异常地反感。
一位金色头发的瘦小男孩注视了她好久,终于走过来拉着她的手问:“这是为什么?”
“这孩子叫菲利普,是菲利皮季的儿子,”一位长舌妇告诉粘西比说,“他的母亲死在了床上,这回他可成了真正的孤儿了。除了爷爷,他的亲人只剩下姨妈和奶奶了。”
粘西比看着孩子的蓝眼睛,眼眶渐渐红了,里头满是泪水。她从他那儿看到了面对不公的痛苦,觉得十分震撼。
“我不知道,菲利普。”她温和地说。
话音刚落她又马上改变了主意:不知道其实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受害。也许自己的丈夫所寻求解决的正是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但苏格拉底,他要解决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在同一时刻,穆塞翁这一富人区一座别墅的二层楼上,熟睡者才刚刚苏醒。其中有一人,一位有着金黄头发和大下巴的年轻男子茫然若失地瞧了一眼绘有阿拉伯花饰的天花板,紧接着又看了看床。上面躺着两个人,一位年轻女孩和一位年轻男子,他们仍在沉睡着。他看了看那个女孩,耸了耸眉。女孩脸上的脂粉经过一夜已经完全褪去,要想辨认出她是谁着实有些困难。而那个男子仍在打着鼾。
金头发男子弯下身去,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夜壶放在身前准备小解,目光落在了他放在地上的那把剑上。他将剑捡起并置于附近的一张圆桌上。接着他走到窗户那里拉开了厚厚的窗帘向外张望。窗外明媚的阳光洒满了整个花园。
前传 辉煌的落日 上清晨一次关于正义的谈话(1)
第二天,粘西比早早地便起了床,从自己的内室观察苏格拉底的房间。
房门吱吱嘎嘎,院子里苍蝇疯狂地嗡嗡作响。粘西比在同一个小木桶里洗着自己最小的孩子和他的外衣。忽然在她面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希腊最强大城邦里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除了肚脐下提了一条宽松的长裤以外几乎赤身裸体。他的肚脐挤在满是赘肉并覆盖着金
黄色汗毛的肚子中间,几乎都快看不见了。
“早上好!”他喊道。
男孩显然被这一声音吓着了,在木桶里不停动弹。粘西比仅仅像是对待长官一样朝他点了点头。
“我想跟你谈谈。”她说。
他向她这儿走近了一步。
“还有葡萄吗?”他问道。
“厨房有。”
他穿过院子,中途拍了拍他儿子挂满水珠的脑袋和下巴,向篮中去寻葡萄。当他回来时,粘西比正把孩子擦干。
“那个死者……”她开始说道。
他在一条腿有长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葡萄架下投射着屋顶长长的影子。他将一颗葡萄粒塞入嘴里开始咀嚼,似乎根本没听懂粘西比所说的话。
“那个死者,”她重新发起了攻势,“是你的朋友吗?”
“我确实认识他,怎么了?”
“因为听人说他曾经住过我们家。”
他开始吃第二颗葡萄,等待着她下头的话。
“这是他为什么会在我们家后面的小巷里被杀的惟一解释。”她说道。
“这是你的假设罢了。”他假装对着葡萄若有所思,只做了这样的回答。
但粘西比此刻的表情使他意识到自己不会这样就蒙混过关。她准备发起攻击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他宁可闪电打雷也不愿听到妻子的尖叫声。此时他的大儿子出现了,他奔向父亲。
苏格拉底拥抱了他并问他是否睡了个好觉。小儿子,什么都没穿,在地上拖着一只脚底装有轮子的木马,嘴里还振振有辞地念着“吁”。母亲将他们带回房间,苏格拉底便又开始从篮中拿他的葡萄。
“苏格拉底,”她坚定地说,“据说菲利皮季在被杀几小时之前还跟亚西比德一块儿吃过饭,而亚西比德又是你的朋友,而且菲利皮季是在我们家后面被人杀害的。我想我的想法不仅仅是一种假设吧。”
见鬼的女人!她很少有那么几天能和他的逻辑推理能力一样好,她嘴里吐出的亚西比德这几个字警告着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太有名了,它属于受伯利克里监护的孤儿,属于一个他放在心底的年轻人。他从未轻率地喊出过这个名字。
“你当时也在跟他们一块儿吃晚饭吗?”她又问道。
“是的。”
“那么你肯定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他揉了揉一只眼睛,接下来又揉了揉另一只,为的是拖延时间。
“我确实知道一件事,”他最后终于说,“那次宴会是在阿尔克罗斯的家里开的,而且亚西比德在第二天清晨前都没有离开过他家。我们谈话直到深夜,在场的还有另几个宾客。那时菲利皮季已离开好一会儿了。”
“他和亚西比德吵架了吗?”粘西比问道。
这个女人的疑心真是重!“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判断的。”粘西比边说着边把桶中的水倒进了排水沟,水便沿着院子一直流到了街上。
一个人是不会无缘无故提早离开宴会的。他们争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她所指的又到底是什么?“我对你的洞察力十分赞赏,亲爱的粘西比。”苏格拉底尽量装作很冷淡地说,“而且我也十分赞赏你竟然对一件跟我们家毫无关系的事如此关心。”
“这件事跟我有关。”她坚定地反驳道。
他扬起了眉毛。
“是吗?”
“是的。菲利皮季儿子的悲伤深深打动了我。当他们把他尸体运走的时候我也在那儿。那个男孩就向我走了过来,因为他听别人说是我发现了尸体。他就简单地问了我一句:‘为什么?’我知道你们在演讲中常说到公正和道德,就是你们,伯利克里的先生们。但我也同样清楚这座城里充满了不公正。想到那个小男孩感觉自己是在雅典不公正的社会基础上长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要知道他可能会失去自尊的,苏格拉底。我想知道菲利皮季为什么被杀,还有是谁杀了他。”
苏格拉底若有所思地考虑着他妻子说的话。他被这些话所震动,几乎是被感动了,同时他觉得再用那些不可捉摸的假话来搪塞或冒失地说漏了嘴都是那么的不合适。
“我敬重你刚才说的话,粘西比。但是如果你知道了杀人者的名字后,你会怎么办呢?”
她愤怒地注视着他。
“我会向议会揭发他!”
苏格拉底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情十分焦急。
“我不知道杀人者的姓名,粘西比。但我不想让你卷进这桩正如你自己所说的会动摇雅典基础的事件中来。你会有危险,也会遭遇到十分厉害的敌人,而且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也有可能被你拖下水。我不想对你隐瞒,那样会令我非常讨厌。”
前传 辉煌的落日 上清晨一次关于正义的谈话(2)
“你的意思是……”她激动地问道。
“听着。在雅典有两个政党,他们水火不容。一个是民主党,他们希望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另一个是寡头政党,他们觉得权力应该掌握在少数有经验的人手里。菲利皮季,就跟他父亲薛尼亚德一样,曾经是寡头政党的拥护者。他强烈反对亚西比德,因为后者虽身为寡头政党却玩弄民主权利。他本是亚西比德的朋友,但自从认为他是个伪君子后便不停地辱骂他。亚西比德的朋友便起来抗议而且用过激的手段进行报复。当时大家都喝了酒,而且周围乱糟糟的。有几个宾客起身去骂坐在不远处的菲利皮季,他就站起身来离开了。后来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有一个亚西比德的朋友去尾随他,后来争吵恶化了……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菲利皮季会来这儿,因为他走时我还在阿尔克罗斯家呢。你瞧吧。”
粘西比认真地听着她丈夫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不知道谁有可能跟踪菲利皮季吗?”她又问道。
“不,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因为如果我知道了,我可能会被迫将他告发出来,那样可能会引起500人议会和十将军会的危机。我们正在打仗,拉栖第梦人已在阿提卡发动了进攻。选择这个时候挑起一件涉及受伯利克里监护的孤儿的丑闻是错误的。这对民主党和整个雅典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打仗,打仗!你们总是在打仗,就是你们这些男人们!所以说,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的意思是应该以民主的名义包庇一个杀人犯。”粘西比边说边向她丈夫投去了严厉的目光。
“如果女人也被允许参政,我会尽我所能把你选入500人议会的,粘西比。”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这么说可是认真的。”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我可接受不了一件不公正的事,而且更糟糕的是,一个杀人犯竟以正义的名义干着坏事。”
从眼角苏格拉底看到奴隶正在厨房生火。油炸大蒜的味道混入了空气中。苏格拉底站起身结束了这场比平时安静但却比他想象中更令人不安的谈话。情况是不可预见的,而且他从中还品出了讽刺的味道:他妻子对于一个孤儿的同情恰恰证实了哲学的道德正义。他总是庆幸于自己的小心谨慎;他没有告诉粘西比受害者是亚西比德的情人,而且争吵的起源既有政治原因同时也有关于两个男人间的私密关系。女人对此总是一无所知。
前传 辉煌的落日 上清晨一次关于正义的谈话(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