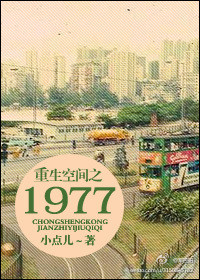802-未婚状态-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告诉我她舍友的事情,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她说她们宿舍有两个女孩,自从进校之后就同睡在一张床上,不管春夏秋冬。我问她女生宿舍的床那么小,怎么能睡得下呢。她说谁知道,夏天即使再热她们也是那个样子。我问那留下的另一张床呢。她说就空着,有时候上面放些东西。我如听天书,惊讶万分,难道她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们吗?我问她那两人是不是同性恋,她摇摇头说不知道。我问她,你们宿舍的人有什么反应。她淡淡地说,习惯了,不管什么东西,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我莫名其妙地把她这句话记得十分清楚:习惯了,不管什么东西,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她说:“我一闭上眼睛就想你。”
我说:“我不闭上眼睛都想你。”
本来还想写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心里满是伤感,只好作罢。
6
我认识她期间读了一本小说,名字忘了,是一位住在北京的作家写的。我喜欢他写的这本小说。好像还看了潘军的《海口日记》。这篇小说的题记好像是昨天的日记都是从今天写起的。而那位北京作家的一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他说:崇拜是恋爱时最要不得的。而对一个女人,你一旦不敢向她调情,不敢搂她或摸她,那几乎就没有什么戏可唱了。我觉得他说得简直是太好了。遗憾的是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男女关系方面总是郁郁不得志。那些女人们会把我当作很好的朋友,但是她们不会做我的女朋友。她们中间的一部分我曾经刻骨铭心地喜欢过,但那个时候我不敢同她们调情,当然更不敢搂或者摸,只会一味地暗恋,远远的偷着望人家。所以没戏。等有一天我敢同她们调情了,她们中的一部分果然喜欢上我了。但这个时候我却纯情不似当年。还是贾平凹说得好,世上的事情是有牙的时候没锅盔,有锅盔的时候却没牙了。
我在和她恋爱的过程中将这本书仔仔细细阅读数遍。有些话当时觉得说得很好,我就抄了下来:
往事像几片落叶,在我们眼前纷纷飘下。
一丝不挂的思想 。
没心没肺地活着。
鲜艳的“麦当劳”餐厅的巨型标志竖在高层建筑上,像是一个冲天撅起的屁股。
“那就是咱们居住的地方?”
“是的”我咬文嚼字地说,“我的青春和我的梦想将断送在那里。”
在这个年代,鲜花比任何时候都要多,而动人的爱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少。
“你狂吠了半天,就不怕吓着姑娘们。”
说了一句丧尽天良的话。
我更喜欢倾听将空啤酒瓶从十五楼扔下发出的声音。
我快乐的就像一只虫子,没有脑袋。
莽莽中原,如今有出息的人不多了。
低头的时候,浓密的黑发一泻而下,怪兮兮的。
那眼神就像井里的月光。
现在看见这些句子,我就会想起那个总是喊疼的姑娘。她的眼神就像井里的月光,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句子来描述,现在终于找到了。
不知道她现在还是否喊疼。
7
都是假的,其实都是假的。我逐渐淹没在文字的琐碎叙述中而不知所措,周围是支离破碎的回忆和为了弥补回忆的缝隙加上去的幻想。我不知道为什么胡编乱造这么一则庸俗的故事来给自己和别人看。我是不是因为逝去的高中生活过于平淡而一直在不经意中耿耿于怀?我可以证明从前度过的短短十多年的生活除了成天到晚捧着书还有别的色彩可言,可以证明在别人心目中像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除了知道做题还有别的诸如找女朋友的本领,虽然这样的本领应该划归于人类的本能之列。我是不是也很希望编造一则美丽动人的故事给谁听?她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她会明白我是多么善良,她会知道我曾经付出了很多,她并不会因为我从前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然而根本没有故事可言,生活只是生活。生活很可能成为小说,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小说。
我现在能想起的只是一些记忆的残片。也许前言不搭后语,也许没有逻辑可言。
她的名字和花有关。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她的名字的。听说追她的男孩有很多。我给她送过情书,但是写得很诚恳,一点都不肉麻。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她给我说的。我还送给她几本书,但是大都物归原主。我是追她没追上,后来峰回路转,追上了。
追上之后其实也没干什么。打打电话,在晚自习期间聊聊天。我没有和她调过情,更不敢对她动手动脚,所以自然没戏。大家不欢而散。
我还给她买过脆皮、口香糖、土豆片。土豆片她没吃,我一时生气,把土豆片给扔了。忘了说,还有一盘《泰坦尼克号》的磁带。后来这盘带在听的时候夹带了。她在我俩分开后买了新的还给我。我开始不准备扔的,但是因为睹物思人,实在过于伤感,就扔了。等考上西安的大学之后,回到家才发现里面的歌词没有扔。无奈地笑了笑,心中仍然隐隐作痛。
她借给我一盘肯尼•;G的萨克斯,还没还给她现在记不起来了。她在一天中午的课间让我的一位朋友交给我一本《中学生数理化》,我曾经幼稚地以为那是我今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但是后来又收到了更加珍贵的。应了广告上的一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一天中午我俩在硕大的饭堂里吃过中午饭,决定找个地方坐一坐。出了门,朝右拐,再朝右拐,一直到没有人的地方。那是学校的围墙。我低着头默默地不说话。我把钥匙串扔到半空中又接住,再扔再接住。路上做饭的师傅朝我俩看了看。我向身后看去,没有人。我问她怎么不说话。她看都没看我一眼,说,说什么呀。我听了就很生气。这话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我使劲把一块石头踢得远远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天气很好,好像是五月份的样子,刮着点风。操场上一群人你推我搡,围着一个球转来转去。我就想,这世界上有些男人真没出息。有的围着皮球转,有的围着女人转,有的围着硬币转,有的围着房子转。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围着自己转。我俩就这么沉默着。她走在前面,我跟着她。不知道是刚吃完饭该睡午觉了还是我这两天心情本身就不好,脑子里木木的,心情沮丧。再过一个小时又他妈的得上课,这种非人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她在墙根下站住,弯下身子吹了吹地上的土,然后坐下去。然后我俩说了什么。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她说别晃来晃去了,要坐就赶快坐过来。我就听她的话,在她身旁坐下来。我们开始聊天,但是我心情越来越不好。
长话短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由于种种众人皆知的原因对她说,我俩还是好好学习吧。然后苦口婆心地发表了一片长篇大论,自然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我最后说,等我考完试我去你们那儿找你玩吧。她说好吧。然后我就起身准备走了。我站起来的时候听见她说,我知道会有今天的,但没想到有这么快。然后就看见她面前青色的水泥地上吧嗒吧嗒滴下几滴泪。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起风了,干燥的操场上扬起沙子。
你可以猜测得到,整整一个下午我什么都没有干,坐在我的桌子上发呆。我同桌见我表现异常,主动给我去楼下买了一盒冰激凌。我吃过之后继续发呆。
下课后回了趟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实在是睡不着,就出去转了转。神不知鬼不觉来到操场上。又突然想起今天中午刚刚发生的事情,心痛万分,逃也似的回到宿舍。跟舍友聊了会儿天,前言不搭后语,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又去睡觉,但是睡不着。大热天的脚却非常冷。快上自习时,我喝了杯水,上了趟厕所。回来后对着镜子梳头,却在镜子里看见她的脸。于是又开始发呆。
赶上课前来到教室。桌子也没擦就坐下来。同桌对我说,你怎么啦,桌子还没擦。我说,忘了。随便抽出一张卷子做起来。上面的题大部分都做过。我没头没脑地往下做。等下自习的时候一对照答案,离及格还很遥远。
自习中间上了趟厕所,回到教室后又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该如何度过。上自习十几分钟了,我还对着桌子发呆。这时门推开了,有人找我。我透过门缝看见是她的朋友,内心极其矛盾,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出去。五分钟之后我飞跑出教室。
出了教室我左看右看,没有人影。再走几步在楼道的拐角看见她。她泪流满面,两只袖口湿了一大片。我的心一下就软了,而实际上在我刚刚说出分手的话时我就已经后悔了。
你一定猜得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两个星期后我俩还是分手了,这次是她提出来的。
第一部分翻起旧时照片
8
我决定不再在这种幼稚的事情上浪费笔墨。所谓的早恋,好比两条还没长大的小狗,你咬我的尾巴,我咬你的尾巴,在原地转圈圈。转了几圈,累了,然后各自分开。
我从前的一篇文章《冷月无声》曾经对此有所涉及,并回顾了在西安上大学前的生活。现在全部抄上,算是有了个了结——
偶尔翻起旧时照片,恍惚中不知身在何处。我站在摆出各种脸色的人群里,双眉紧锁,就有点忧国忧民的意境。当时我还曾刻意地留起了胡子,希望给即将奔赴五湖四海的学子们留下饱经风霜的印象。我在别人的留言本里常用的句子是:十年后街头相逢如何如何。于是有人真的对我说:“你看起来很沧桑。”
看起来很沧桑的我,那时蜷缩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某个角落里,时常抬头对窗外的冷月发几声感慨,但没人注意,他们都忙着做题。我身边几步远处是纸做的垃圾箱。班主任正在上课,就说垃圾箱怎么能放在老师旁边呢,啊?“小人,地地道道的小人。”这话是我对着她说的,她扶着腰远远地走在前面。但那时就有一位女孩叫人想入非非。她远远地坐在第一排,小手里总是捏一团纸蛋蛋来我的领地。有了一些自作多情的想法之后,情况就变得多少有点尴尬。我的习惯总是凝神眼前一处并不存在的虚物发呆。她这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通常显得比较慌乱,原因是不知该将眼光落在何处。于是干脆埋头趴了桌子,听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窗外横着几根电线,电线上常有叫不上名的小鸟嬉戏,紫黑色的羽毛闪耀着神秘的光泽。叽叽喳喳地乱叫,开始时弄得人心烦意乱,但一段时间后发现我竟离不开那种有节奏的叫声。特别是傍晚,血色阳光斜射进来,陈旧的窗棂便铺在地上,听着窗外操场上的喧闹与鸟叫的混音,我莫名地产生一种悲壮感,感觉正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我在各类参考书的包皮上写下诸如“穿过你黑发的我的手”之类的句子,它总叫人感到某种如同空气般无所不在却又无形的力量对青春的压抑。傍晚,红云燃烧,鸟乱窗外,一队队高二女生从后门一闪而过。那扇欲倒的门好比地狱与天堂、现实和理想间的玻璃。我因而寻觅到一种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每天我试图记住一张面孔,等一张张生动鲜活的脸深刻在脑海中时,我也该道别了。如果再次相见,我是准备和她们握手的。
阳光每日在某一固定时刻斜射进来,照在物理老师的小胡子上。“今天我们复习一下‘牛二’定律及其应用。”他的双肩随着语句有节奏地抖动着。我开始在试卷的空白处写下诗句:自由从脚下匍匐而过/我泪流满面,相信/一些抽象的信念/因为,他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时我们的班花开始掏鼻孔,并脱下她右脚上的凉鞋;又有人因为听不懂竟然哭了;两种不同肤色的手悄悄握在一起。他们身后的女生对我深恶痛绝,但我是绅士,不和她吵架了。我说:“你的眼睛真的很美。”周围的兄弟亦随声附和。她从此不再忧郁,然而拒绝和我们一帮凡夫俗子说话了。我发现她一有机会就对英俊潇洒的外文老师下手。“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她嘴里嘟嘟着就把一双因为熬夜显得突出的眼睛咕嘟嘟转起来。
多年之后唯一值得怀念的是楼顶上的一株小树,它在铺满柏油的楼顶上孤独地挺了三年,但总算活过来了。当注意到它的确切位置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时,我几乎要相信我俩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神秘的、无以言传的关系。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也认不请它究竟是何种树木。然而我无端地自信它绝对是松树,如我般孤独地挺立。我便起了“孤独松”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以示纪念;我开始默默祈祷它的强壮,相信它的强壮一定与我的光明前途有某种联系;我开始让老爸看天气预报,因为这有利于它的成长也适合我的复习大业。但它总是老样子,有时候好像要不行了。
我一个人站在泛着青白色光芒的操场上,孤独得如同我的小树。同时,她面带笑容缓缓走进我的视野,并擦肩而过。事后我总结出一条有切肤之痛的真理:一切可有可无的事情都在无聊中诞生。我想那时我是够无聊了。做早操前站在固定位置等她与我擦肩而过逐渐成为一种期待、一种嗜好,如同吸鸦片一样变得无法自控。我看着她从教学楼的木门闪出,又微笑着由远及近;我看着她的服饰一天天变化,从秋天到冬天;我看着她的脸上逐渐爬上青春痘,但仍不失为一种美;最后我看得她再也不敢和我擦肩而过了,开始绕道而行。因此我也相信哲学书里关于量变到质变的理论。我在一张报纸上很有礼貌地写下一些文字,准备打上草稿,再工工整整抄一遍送给她。不料竟然一气呵成,天衣无缝。于是索性把草稿送去。“字写得好有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