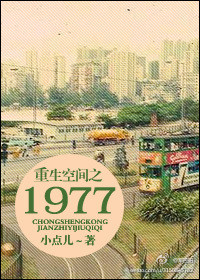802-未婚状态-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竟然一气呵成,天衣无缝。于是索性把草稿送去。“字写得好有个屁用。”这么想来就坦然了。
操场是个叫人伤心至极的地方,几乎所有天真无邪的故事都在这里上演。我双手插着裤兜在泛着白光的土地上晃荡时就亲眼目睹过许许多多聚聚散散离离合合。在黑暗里仰望静卧的教学楼,感觉它扭曲如列车,时时传来阵阵喧嚣,但大家有一天都注定要离开它走自己的路。有月亮的夜晚,操场上的人就多了。凉风拂过,吹动额前发卷,你就突然发现地上有了影子。而柳叶随风摇晃,于是一切都动了起来。这时一声尖叫:“你看,你看,今晚的月亮。”众人便随声附和。我忙走自己的路,然后离他们更远。这时树下的黑影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走近才发现是一对男女。女的声音细细的:“我当时真想扇你一巴掌。”男的就显得有些卑贱:“我错了,再也不了。”真给我们爷们儿丢脸。我心里着实有些气愤,想着就昂起头。又一对迎面过来,还牵着手。我一阵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让路给他们。两人便分开了。我从中间的空隙穿过。女子低下头,可能是害羞了;男子竟然大摇大摆起来,并吹起了口哨。我终于忍无可忍,训斥起他:“有什么可嚣张的?不就是找了个女朋友吗?”这话是我走出二十米后说的。
一块地方我总不愿提及,它总叫人一阵阵心痛。我也忘不了一块叫我用拳头砸碎的玻璃。考上大学后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时仍是老样子,隐隐约约有些凝固的血迹;再去时已经换了新的。一切发生的就有些恍若隔世,只留下记忆的残片如同一堆堆嗡嗡怪叫的绿头苍蝇挥之不去。她与我靠着墙,彼此说一些毫无意义却又急于想说的话。我不知怎的就突然说:“你再这么说我就生气了!”她习惯性地扬扬头:“生气就生气呗。”我就砸了。不料玻璃就破了,手扎出了血,血顺着已有了裂纹的玻璃红蚯蚓一般往下流。那时我俩之间总隔着一块地方,足以夹进另外的人。她哭得伤心,对我说些叫人难忘的话。但后来她又幽幽地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叫你哭的,因为你把我弄哭了。”我便说:“不就是几颗泪吗?我到时候写一部长篇小说送给你。”结果是她实现了承诺,而我没有。
一个人躺在床上。电视里有人唱起忧伤的歌谣:不要问我何时再相逢,不要问我为何言不由衷。于是我对着镜子将蓄了三个月的胡子剃掉。俄罗斯的剃须刀就如同西伯利亚的冷风狂叫起来。我用梳子将头发梳起,根根挺立如刺猬。风越来越大,就听见一种很古怪的声音,如鬼哭,如狼嚎。我便对着镜子大笑起来,有一行泪悄悄流下。这时的窗外,冷月无声。
9
高考结束。我不知道在这四个字后面该用什么标点符号。一个刚刚从黑色七月爬出来的学生最清楚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用N个感叹号也不为过。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句号。因为时间是不带感情的。高中生活就这么过去了,当时的轰轰烈烈平平淡淡现在再想起只是一杯透明的白开水,愿意喝也罢,不愿喝也罢,它只是摆放在那里,悄无声息。
对于高考之后的事情,我在这里还愿意再嗦几句,不愿意看就跳过去吧。
我们那个地方是参加完高考之后才报志愿。一般的程序是先找来标准答案核对,估计自己能考多少分,分数估计出来之后再根据成绩定学校的档次。比方说考得极好就可以报北大清华,考得优秀可以报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之类,以此类推。但是各人估分的误差不同。有的人考了不到六百分却估计自己能考六百三,于是报了北大。结果不上线。这其实说起来没什么,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都有牛脾气。比方说这人分数很高没有被北大录取,他的下场往往是重点大学都不会要他,只能上“二本”。还有的信心不足,考得很高但是报的学校不是很好,当然一报就被录走了。后一种情况较多。
我当时年少,想考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其实我那时对国际关系学院一无所知,只是望文生义,觉得学的东西一定跟外交有关。又加上进这学校要政审,我就猜想将来说不定会干什么情报工作,哈哈,那多刺激。而且它属于提前单独录取,考得上考不上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一本”的录取。
这时候我的父亲出场了。我先对他略作交代。他干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干什么事情都求一个“稳”字。他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在我所有的人生大事上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对我分析利弊:国际关系学院是咱们这种老百姓进的吗?那里面都是那些外交官和党政领导们的子女,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有政审?你看看往年这学校录取的学生的成绩,有超过七百分的吗?没有。但是难道没有像你这样成绩超过七百分又报了这学校的吗?肯定有。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录取上,你想没想过这其中的原因?此其一。即使你报了,你真的能通过政审吗?咱们家你爷爷是党员我是党员,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咱们花费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人力去做这些无用功有什么意思。有这闲工夫我们还不如去南方旅游,我都跟你妈说好了,咱们一把高考志愿交上去,全家去秦皇岛避暑。此其二。退一万步讲,你一切都顺利被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咱们对这学校也不了解,你听说过谁考进这学校了吗?要是真的毕业之后从事情报工作,你让你妈和我还活不活,成天担惊受怕,老害怕你出什么事,此其三……
我斗争不过他,只好妥协。
我第一志愿想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几年外贸专业十分火热,当然分也很高。我如果发挥正常估出来的分数没有多大误差的话,应该没多大问题。这个时候老爸又开始劝我了。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稳稳当当,特别是在人生大事上更来不得半点侥幸。你怎么能保证你估出来的分数就很精确呢?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你高估了你的分数,到时候不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考不上,连个重点大学都进不了。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再退一步讲,即使你估出来的分数很准确,但是谁又能保证今年的录取分数和去年大致相同呢?现在外贸专业这么火暴,我看今年的录取分数肯定比去年的高嘛。我越听越气,真受不了他这种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做法。我说你怎么这么肯定我会那么倒霉?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情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这么倒霉,那他干脆别活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冒一下险呢?老爸本来听我说要报这大学就很不高兴,被我反驳两句脸色更加阴沉。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才对你说这么多话,换了别人他叫我说我还不说呢。这是你的人生大事,最后由你决定。不要到时候说起来又埋怨我和你妈,说我俩把你的前程耽误了。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好,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可没人能帮你,你娃哭都来不及。他嘴上虽是说我的事情由我决定,但是整天不给我好脸色看,好像谁欠了他几万块钱。他在饭桌上和我妈指东道西,说什么去年谁谁谁学习特别好,报了清华,清华没要他,结果连重点大学都没进,上了洛阳一个拖拉机学校。说完哈哈大笑,我总觉他们笑里面满是嘲讽。吃过饭我们家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我们那些远在天边的亲戚打来的。显然是老爸老妈打电话让他们来劝我,他们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甚至都要声泪俱下。几个小时的电话车轮战下来,我筋疲力尽终于抵挡不住。唉,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呀,我他妈要是能生活在真空里就好了。
第一部分面对又一次失败
放弃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接下来就应该选别的。我的意思是要么考北京要么考上海,那两个地方的好学校多了,随便挑一个都行。老爸假装沉思片刻,说你想到这两个离家很远的地方锻炼锻炼是好事,年轻人嘛,在这个年龄多见见世面是应该的,这一点我和你妈绝对支持你。但是我们干什么事情都应该先把利弊得失分析清楚再作决定不迟。先说上海。那里的气候你能不能适应?我可是在那儿出过差,闷热、潮湿,浑身整天都粘粘的,老有喘不过气的感觉。那里的饮食你能不能适应?你不要到时候学业没有搞好反倒先把身体搞垮了。当然你大了,有些困难你是能克服的,这一点我和你妈都清楚。不管怎么说你先考虑考虑吧。最后一点是语言。他们说的上海话你能听得懂吗?你和那些人到时候怎么交流?还有一点我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好随意评论,但是听人说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当然那个地方并不是一无是处了,比方说那个地方人思想解放,机会也多,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上海的利弊得失就这么多,咱们先摆在这里,先考虑考虑再作决定不迟。
关于北京,他没多说什么。但是他把西安和北京作一比较。在西安他有许多大学时的朋友,有的朋友在高校中的官位不小,不管是现在的录取还是四年之后的毕业分配,他们都能帮上忙的。另外我妈有几个亲戚在西安,如果在西安上学他们在生活方面可以照顾得上。而北京离家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要回趟家得坐上一天一夜火车。我气呼呼地说男儿志在四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我就不信你说来说去还能把北京说得比西安好。我当时满肚子理由,但是等我一条一条说出来时又觉得有点苍白无力。
我又一次失败了。我发现从小到大我都是按照别人已经为我设计好的路线和方向在走。有时候我愿意,有时候不愿意。愿意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称赞我是好孩子。不愿意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就说我性格固执,桀骜不驯。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不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就是固执。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办事,那么他们也是性格固执桀骜不驯。推而广之,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理由说别人桀骜不驯。
在这种大的事情上的据理力争每次都以我的惨败告终。即使我的论据充分论证严谨,但每次得出来的论点在他们面前都会魔术般变得苍白无力。他们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或糖衣炮弹威逼利诱,或在我面前以泪洗面,再不行就会回忆生我养我如何如何不易,他们是怎样在艰难困苦之中将我一把屎一把尿抚养成人,然而现在我大了,翅膀硬了,也不听话了云云。
我所做的一切,他们仅仅用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反驳——你不成熟。
于是,不成熟的我极不情愿地来到西安。家里人对我的要求是:锻炼身体,好好学习,不要找女朋友,千万要考研。
10
我从睡梦中惊醒,迷迷糊糊摸出身边的石英表看了看,七点过半。窗外阴沉一片,感觉像是六点多的样子。西安的天气总是这个样子,让人感到无比沉重。空气里弥漫着臭袜子、臭脚丫子和辛辣的体味。我长长地吐了口气,仍然心有余悸。梦见参加高考的情景,开始是钢笔没水了,接着草稿纸用完了,最后一不小心把整张卷子碰到地上,落在淤积的水里。我张了张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穿上衣服后,怎么也找不到袜子。我翻开枕头,然后把被子揭起来,又在床底下找了找。忙碌一阵子,只好穿上拖鞋去厕所。站在那里抖了抖,发了一阵呆,心想尿水发黄,可能是最近火气太旺。回到宿舍往牙刷上挤了点牙膏,之后拿起牙缸、肥皂盒去水房洗刷。水房人太多,得排队。三分钟之后轮到我。旁边小伙把水开得太大,水珠溅了我一身。我嘴张了张,想说他没有说出口。
回到宿舍上铺的阿强说半夜里谁磨牙,他迷迷糊糊的在梦里以为掉进了动物园的虎山。另一位在梳子上蘸了点水,一笔一画仔仔细细地梳头。我想冲杯牛奶,提起暖水壶发现里面的水被谁倒光了。来到对面宿舍借了点水,再回到宿舍人都走光了。我提起拉力器来到阳台上拉了二十下。不远处的高层建筑影影绰绰,处于烟雾笼罩之中。回到宿舍我一口气喝光杯中的牛奶,打了个饱嗝。然后放下杯子,在书架上抽出早上要用的教科书。袜子还是没找到。我从桶里取出准备洗的袜子打算穿上,但是在穿鞋的时候发现原来找不着的袜子躺在鞋里面。穿上鞋,我用抹布擦了擦上面的浮土。刚走到门口,我又折回来打开阳台上的门,好换换空气。之后我看了看表,锁上门,急匆匆走向楼下。
路过食堂时我买三个“东东包”,味道还可以。我平时常吃的有韭菜饼、酸菜饼、包子、晶糕、煎饼果子、油条、豆腐脑、面包。卖煎饼果子的我认识。他在我来这所大学之前就修自行车,我上大二的时候他摇身一变,改卖煎饼果子。还有个卖包子的师傅,从前是理发的。我在他那儿理过一次,质量一般般。理发馆开业一个多月之后,理发馆成了饭馆。我们对此大为惊叹,以为我们身处的这所大学真是不错,连做饭的师傅都是复合型人才。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在这个时候停了。我看了看表,八点整,又迟到了。在这之前高音喇叭播放着英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但原因是高音喇叭的质量太差。这样的话广播的作用是制造噪音而不是传播消息。高音喇叭一般开始的时候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之后是英语。
来到教室时老师已经讲了半个黑板。我在前门口往里张望,坐在前排的一位姑娘冲我笑了笑。她无论上什么课都坐在第一排,几乎每天早上都有机会冲着我笑。我像往常那样朝她咧咧嘴,向后门走去,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坐下来。讲课的老太婆两眼空洞,两眼往上翻盯着天花板,好像没有看见我。我摊开书,问旁边的人今天该讲哪一章了。有俩女生在前排似乎谈论着神秘的话题,一边诡秘地低声笑一边四处张望。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