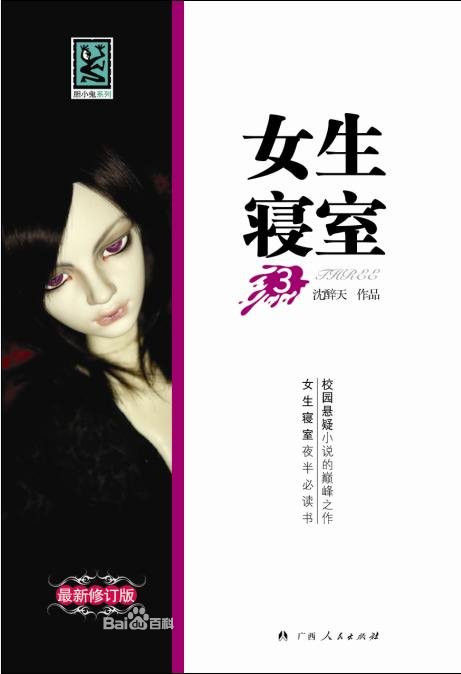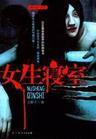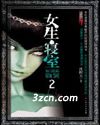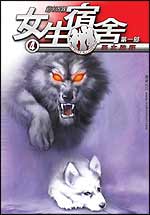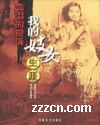耶鲁女生-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据说,二战的时候,德国纳粹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识别美国派出的间谍——观察他是否用“欧洲”方式使用餐具,还是用美国人一贯的方式,坚持用右手持叉。
我还读到过,德国人用另一种办法来识破英国派到德国的间谍——他们观察他过马路时先向哪边看。如果下意识地先向右边看,他们马上断言:此人一定是在英国长大的。
我不由得感叹:一个人在某种文化内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实在太多太多,许多习惯都在无形中形成,恐怕自己都意识不到。像英国交通规则是汽车靠左行驶,因此孩童们从小就形成“过马路时危险首先从右边来”的观念,跨下人行道时首先看右边。久而久之,一过马路自然流露出来,除非有意识地自我训练去控制,否则准会露馅。
这种“下意识”却根深蒂固的知识,现在正是心理与社会学家的热门话题。学者们管这种知识叫做“沉默知识”(tacitknowledge),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大量的这种“沉默知识”。一个新来者如果想融入这种文化,不但要掌握白纸黑字的法令规则条文,也得掌握许许多多的“沉默知识”,才能成为这种文化中的“局内人”,而不总是被人视为“局外人”。
记得我11岁时跟随父亲来美国,在飞机上他对我说:美国人比中国人开朗外向,所以如果跟美国人交往,表情、语气和姿势,都要比原来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的习惯幅度加倍——要笑,嘴咧大一倍,要惊,眼瞪大一倍,要吼,声拉高一倍,这才恰到好处;否则在他们眼中你就是个成天不苟言笑地板着脸的形象,要么觉得你呆头呆脑,要么觉得你深不可测。
当时他也没有来过美国,很少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这些话都是别人的经验之谈而已。但是后来我跟美国老师、同学交往,切身体会到确实如此:在中国人眼里,美国人彼此交流时表情语气未免热烈得过于夸张,甚至带上很强的戏剧性色彩,或许有人还受不了他们那种热腾腾的劲儿;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的交往态度则未免过于冷淡含蓄,缺乏高低起伏,或许他们也有人看不透中国人是内热外冷的“暖瓶”风格呢。
这里我所说的“文化”当然不只是指国度、民族这些大的层面上的文化,也指同一国度、民族中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职业行当、各个地域环境中的文化,例如学术界的文化、商业界的文化、演艺界的文化,大到美国南部这样的地区,小到一个公司企业,甚至一个家族,都具有各自的“沉默知识”。任何团体与组织,除了明文规定(像“上班不得趿拉拖鞋”、“赴晚宴请穿正式服装”之类),也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不停地熏陶着自己成员的行为,从口音、到辞令、到肢体语言、到日常起居时的种种习惯,到与他人交往中的繁文缛节,这些细节使某一个团体与组织的成员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同类,也是社会学家得以研究某人所属的文化、社会阶层、职业。
这种“沉默知识”之所以难学,是因为许多时候,就是“局内人”也很难意识到并且一一列举它们。就从衣着服饰上来说吧,有谁明文规定:在美国,穿黑鞋白袜是服饰上的大忌,或是女士如果穿露趾凉鞋就不应该同时穿丝袜,或是只有青少年才有资格穿那种露肚脐的短上衣?有谁权威发布:一个女性,把衬衫扎到短裤里去,或是在头发上洒太多发胶,都会给人“过时”的感觉,因为这种打扮只在八十年代流行?可是以上这些不成文规定,恰恰美国中产阶级人士都不言自明。
现在中国国内开放搞活,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在加剧。与我们的祖辈父辈相比,这一代人移民、搬迁的机会多了。来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除了要学习新语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大量新文化中的“沉默知识”。当然,“沉默知识”也是深不可测,所谓“掌握”是相对而言,总之是多多益善。我常常听到一些来美年头不少的华人感叹:自己论工作技能、论英语、乃至论业余爱好、论对美国上下古今的了解……都一点不比老美差,怎么他们还是看自己是个“老外”,有意无意地疏远自己?难道这还不说明美国种族歧视吗?我想,有没有可能问题并非出在大的方面,而只是出在若干细枝末节,让人感觉你还不是“自己人”呢——你脱T恤衫“剥皮”而不是“蜕皮”,或者你吃排骨时没有大着胆子直接向盘子“伸出魔爪”?
第四辑 东方西方远方的战火与身边的平静
一切都这样平静,可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真的开始了。在上班的路上,我第一次确切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纽黑文的市政厅离我上班的公司只隔一条街,我每天上班匆匆经过市政厅大停车场的入口。这天早上,停车场的入口处车辆排起了长队,走近了我才看到,原来两个警察正在检查每辆车,甚至把反光镜一一伸到车底,看车下是否安装了炸弹。这种高度警戒的状态,以前我只在驻德国和东欧的美国领事馆外见到过。看来纽黑文政府机构的安全警戒确实提高了一级,不知是不是全康奈迪格州,或者全美国,都是如此?
但到了公司,眼前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我和同事们一如往常各忙各的,并没有议论起任何关于战争的话题。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同事克丽西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打开CNN的网页,察看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到我的上司的办公室里去拿资料,原来他也在看《纽约时报》网页,上面大号黑字:“美国军队炮轰伊拉克”——尽管没有人提起,但战云确实满满当当地弥漫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耶鲁正在放春假,校园里冷清之极,什么人也没有。在电视新闻里得知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如果没放假,绝大多数是左派的耶鲁学生,一定也会举行轰轰烈烈的反战集会游行。星期五早上倒确实见到两个人在我办公室外的街口举着大牌子,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停止伊拉克战争!”“布什下台”之类的标语,后面还有一辆警车护驾。这就是我在纽黑文所见到的全部“反战集会”了!看到他们两人一本正经地站在那儿,向所有过往行人和车辆展示他们的牌子,我简直要失笑:这两人组的“反战集会”简直也太寒酸了吧?可是再一想又不禁肃然起敬:人家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遵循自己的信仰而行动,人数多与少有什么关系呢?
看着这场战争的开始,我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一方面,战争既然已经是既成事实,我当然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尽早把萨达姆赶下台,好在巴格达建立一个符合人民心愿的新政权,让伊拉克有一个新开始。我对萨达姆一向没什么好感,也相信这个独裁者下台对于伊拉克人民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可是看到全世界各地反战与反美人潮,我又不由得怀疑这场战争的明智。至少,它严重地加深了美国在世界眼里的负面形象。民意调查表明,除了美国的民众普遍支持这场战争之外,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公众几乎不约而同地反对这场战争,就连与美国站在一条战壕里的英国政府,也是得顶着几乎一边倒的民间反战声浪逆道而行。美国在世界上这种日渐孤立的角色不能不让人焦虑与担心。而且,这么强大的反战声音,让人不由得不发问:究竟是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错了,还是美国自己错了?
更何况,小布什一再强调美国之所以不需要联合国同意就出兵伊拉克,是因为美国是在“自卫”,美国不得不出兵伊拉克,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再一次策划“九一一”这样大规模的袭击。可是就连我的同事克丽西,这个对“九一一”事件痛心疾首、坚决支持美国和盟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女孩,也说不清楚“九一一”与伊拉克战争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
星期五,当我们终于在办公室里谈起打仗的事时,克丽西忍不住对我抱怨说。“可是,如果美国出兵是为了防止再一次恐怖行动的话,我不懂美国为什么在联合国报告上对于伊拉克的违法武器那么大作文章,可是并没有怎么提伊拉克与恐怖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到现在都不清楚,打伊拉克与‘九一一’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无言以对。仔细想来,这里面的联系的确十分令人费解。按常理推测,伊拉克与恐怖组织之间一定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可是这并不是美国在过去几个星期内论证战争之必要时所阐述的要点。相反,鲍威尔在联合国的报告中用大量物证和照片一再强调的是伊拉克非法拥有不被联合国决议所允许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毫无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合作的诚意。至于伊拉克与恐怖组织的关系嘛,鲍威尔说“盖达”一个高级成员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了恐怖组织,可是他也并没有解释萨达姆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究竟有什么勾结——这正像说盖达的成员在印尼、在德国、甚至在美国或者可能在中国建立了恐怖组织,并不能就此推论这些国家的当局与他们有联系一样。
不管布什和他的手下怎样解释美国对伊拉克政府宣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显然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公众与政府并没有被这套说辞说服。这场战争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星期四和星期五,大规模的反战集会和游行的浪潮,从地球这一边拍打到另一边,各个国家的反美浪潮,大概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为高涨。我注意到,人们还特意举着英语的反战标语,好让那些一向不懂、也不学其他外语的美国人能一目了然。
不管怎样,导弹炸响后整整两天,战争对于我来说只存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图片和与同事零星交谈之中。直到周末,和成千上万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我整天一刻不停地开着电视,放在CNN、FOX或MSNBC的新闻频道上,随时收看战争的最新动态。他们这些新闻从业人员也真敬业,一个个马不停蹄一连几个小时不插广告地直播从前线传来的各种消息,还穿插与各色人物——从军人到政客,从各路专家到各种知情人——的采访与对话。要说这些新闻机构的敏捷身手和超级效率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星期六早上,刚刚披露有几名战士阵亡,一个多小时以后,FOX已经把其中一名士兵的家属拉到摄像机前,听他们对着镜头回忆这位阵亡者的生平。
可是,望着屏幕上他们麻木的神色与机械的叙述(他们一定还处在刚刚得知噩耗的震惊之中),我又深深地意识了这场战争对于观众的非真实性。他们一个个好像是电视脱口秀中的来宾,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对于他们来说一定刻骨铭心,却与观众的生活毫不相干的故事。就连屏幕中一再出现的战争画面——巴格达模糊的夜景、远方不时响起的爆炸声以及城市上空隐约可见缭绕的浓烟,不知为什么也让我想起某些电影中很不高明的特技镜头。
和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我难以把镜头中的画面与身边现实挂上钩,难以深切地体会这场战争对于远方民众、身边民众的命运会有什么真实的冲击。伊拉克战争不是被夜以继日地现场直播着么?不是有那么多记者出生入死地冒着战火采访么?这些镜头却不知为什么更像是一届电影节、一场电视秀、一出舞台剧。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如此轻易地表态支持美国打响战争吧:媒体确实把天下都拉到了每个人眼前,然而它的方式是通过把天下都收纳在媒体这方天地之中。媒体充当了观众读者与大千世界的连接中介,却同时又阻断了人通过自己的感官,来实实在在地把握大千世界。更不用说奥斯卡颁奖的衣香鬓影、言笑晏晏,与伊拉克的刀光血影、轰鸣隆隆,居然穿插播出,让人哪里分得清究竟哪个是虚幻,哪个是真实?
战火已经燃起,对伊拉克以外的世界来说,战火只是燃烧在在报纸版面那么大的电视屏幕,电视屏幕那么大的报纸版面之中。我自己的生活,我周围人们的生活,仍然是如此令人震惊的平静。
第四辑 东方西方如果你是美国总统
前几天与朋友一起吃饭,他若有所思地问我:“如果你是美国总统,而你从中央情报局得到确凿情报,北韩准备把它的核武器卖给一个恐怖组织——你会怎么做?”
我没有料到他会问这个,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想,我会想办法阻挠这场交易,不过具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的朋友说:“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向北韩发起核攻击,把它的首都平壤炸平,彻底根除那些在高层作出这种邪恶可怕决策的官员——这才是彻底干掉这场交易的最好办法。”
这位朋友一向是个挺温和低调的人,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时,真把我吓了一跳。张口结舌一会儿,我说:“这种办法到底有没有效姑且不论,你用这么极端的手段,不就沦为与那些你想消灭的恐怖分子一样了吗?”
朋友耸耸肩:“这是自卫。我们都很清楚恐怖分子想要得到核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大规模地杀伤我们的同胞。阻止他们的办法只有抢先一步把他们消灭。我当然知道这样会杀死大量的平民,就像在二战结束之前在日本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一样。但也就像那时一样,现在我们也是不得已。”
见我沉默不语,他又说:“既然不是他们的平民死,就是我们的平民亡,我们当然更有责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动用核武器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如果真到这种地步,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说:“我真庆幸我不是那个作决定的人。”
在这之后整整一天,我都在思考这位朋友一番话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我猜想,这个周末,在北韩宣布它“已经”拥有核武器之后,一定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进行我与朋友这样的谈话。面对着一个不择手段的恐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