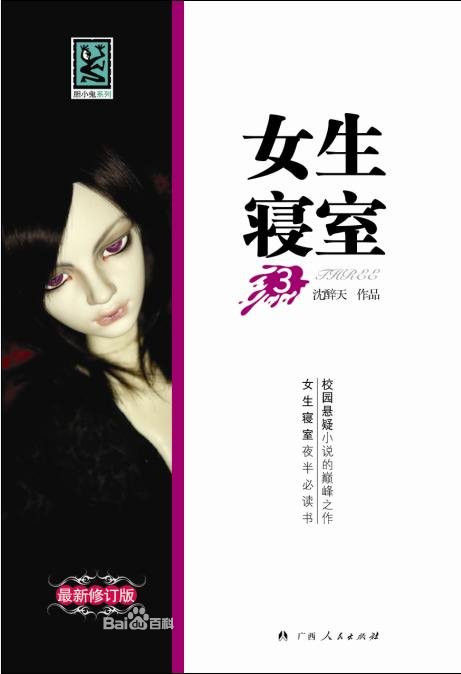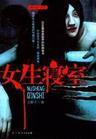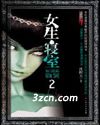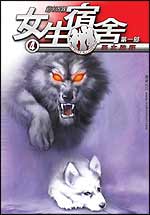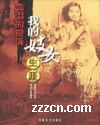耶鲁女生-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看似不重要的小烦恼点点滴滴、积少成多吗?
尽管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接受心理治疗的耶鲁学生并无“大病”,在我上耶鲁之后,校园里确实出过两三起学生自杀的恶性事件,我也亲身遇到了一个曾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女孩。
她叫莫纳丽,从斯里兰卡来。在我大四的时候,她还是个新生,可是因为开学两个星期前才决定要来,宿舍调配不开,我们学院的院长十万火急地问我能不能接受她来一起住一段时间。那段日子我正一个人住单间宿舍,我自然更愿意自己“独往独来”,可又不好拒绝我的院长。于是,她搬了进来,成了我的临时“室友”。
莫纳丽让人一见惊艳:深褐皮肤,浓密卷发,身材娇小,纤细的腰,秀丽的脸。住在我屋里的那一段时间,不时有男生吞吞吐吐地问我:“莫纳丽是不是跟你住在一块儿?有空让她出来一起玩。”
没想到,这样得天独厚的美女,却曾经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相处熟了,莫纳丽告诉我,她三年前就考进耶鲁,比我只低一年,可是在这里只上了一个学期就不得不辍学回斯里兰卡。原因是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那时刚从斯里兰卡来美国,感觉举目无亲,非常孤独。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我一天到晚去跳舞、开派对、喝酒,玩得天昏地暗,几乎没把任何精力用在学习上。期中考试,我五门课里有三门不及格。我的教授们汇报给院长,警告说如果我期末再不及格的话就得从耶鲁辍学。
“正巧那个时候,我的男友跟我分手了,我的生活就像一列脱了轨的火车,越来越失去控制。我晚上拼命寻欢作乐,想减轻心灵上的空虚,与许多男生发生关系,经常在清晨醒在陌生的床上,有时甚至是衣冠不整地躺在陌生的地板上。白天我不去上课,只是在自己寝室里呼呼大睡,根本不想起床面对现实。
“终于有一天,我精神崩溃,在床上一连躺了三天,不吃不喝,万念俱灰。我的室友们害怕了,打电话给我的院长。他安排把我送进了医院,就是‘心理卫生’科。给我检查的心理医生问我愿不愿意在医院里住一晚上。我说‘不愿意’。没想到他这句话并不是征求我的同意,而只是为了看拘留我需不需要动用强迫手段。我因为说‘不愿意’,就成了非自愿,需要强行留院治疗的病人。他们把我的四肢绑在床上,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监护。学校通知我了的父母,说我出事了。我妈妈从斯里兰卡飞来,最后决定:从耶鲁辍学,把我带回斯里兰卡在家里疗养。”
“你那时,到底有没有想过自杀呢?”我忍不住问。
她愣了一下,脸微微地红了起来:“确实想过。后来我想,在医院里住的那天晚上,也许救了我的命。”
回到斯里兰卡的家里,莫纳丽静养了好几个月,情绪渐渐恢复。之后两年,她当了一名教师,给当地小学生们补习数学和科学。“在这两年中,我长大了很多,平静了不少,在心智上成熟了一大截。后来我决定,现在是回来继续念书的时候了,再一次申请耶鲁,又被录取了。”
看着眼前这个微笑着的女孩,真不敢相信曾经有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发生在她的身上。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你现在快乐吗?”
“我现在很平静。快乐嘛,还是需要努力来得到的。”
第一辑 课内课外诗歌在今天有什么力量?
我猜,没有几个中国人会知道“波灵格”(Bollinger)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吧——我也猜,美国人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波灵格”是一个美国诗歌奖——准确地说,“波灵格”诗歌奖是颁给美国诗人的最高奖项之一,每两年颁发一次,颁给一名美国诗人,奖励他或她为美国诗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得主包括著名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埃兹拉·庞德,以及玛丽安·摩尔;最近几届得主全是在美国诗坛上举足轻重的泰斗,有的曾担任美国桂冠诗人,有的据说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名单上。
记得2002年秋天,耶鲁大学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主办者一定兴奋欲狂:邀请了所有在世的波灵格诗歌奖得主,一共九人,有八人欣然同意光临!这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同时在一张节目单上出现,同一天晚上在纽黑文聚齐,朗读他们的诗歌!据说,这是波灵格奖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颁发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说是“百年一遇”并不过分吧?
我是诗歌爱好者,遇到诗坛的百年一遇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早早地就和朋友跑到朗诵会的举办地点去占位子。不过,“波灵格”以及诗歌,对于诗坛以外的人,究竟有多大的号召力呢?在美国与在中国一样,喜欢诗的人总是少数啊,许多在诗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诗坛外简直鲜为人知。但是,举办朗诵会的教堂内外的景象让我吃了一惊:几乎半个耶鲁都拥来了,晚到的人们进不去,只好被请到附近另一所教堂里去看闭路电视转播。环视四周,耶鲁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们全番出动,就连历史系和政治系的教授们也几乎全到齐了。
八名波灵格奖得主被好几名耶鲁教授簇拥着来到会场。八人中有七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只有一人是名女性——露易丝·格鲁克,是2002年那年的获奖者。其中一名老头看上去格外老态龙钟,他佝偻着背,身材干瘪瘦小,走路颤颤巍巍,看上去好像虚弱得随时可能当场……
看他这模样,我真有些担心他能不能支撑到朗诵会结束。看看节目单上的介绍,呵,他一定就是老诗人斯坦利·库尼兹(Stanley Kunitz)了,1908年出生,已经94岁,是所有还在世的波灵格奖得主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怪不得。
朗诵按照诗人们姓氏的字母顺序进行。他们每人各显神通,有的诙谐有的深沉,有的朗诵使自己成名的经典,有的则选了自己从未公开过的新作。有的人朗诵得非常成功,有的则显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诗虽然十分出色,但念得语气呆板,音色沉闷,听得全场观众几乎昏昏欲睡。
轮到94岁的库尼兹时,只见他极缓慢、极缓慢地走到讲台前面,仿佛随时都会摔倒。我暗暗地为他捏了把汗,希望他不要出什么三长两短才好。他比别的诗人矮了一大截,几乎够不着讲台。旁边的人忙活了好一阵才尽量调低扩音器,对准了他的嘴。全场这时已经响起了一片嗡嗡的声音。
可是老诗人一开口,就马上使全场安静下来。
“我今天要朗诵的这首诗,与耶鲁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的声音有老者特有的嘶哑,却仍十分洪亮,甚至可以算是中气十足。他说得很慢,几乎是一字一顿地,给他的话一种特有的戏剧性效果。
“那是1968年,我来耶鲁访问,住在卡尔洪住宿学院里。那时,我的好友W。 B。 路易斯,是卡尔洪学院的院长。”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卡尔洪学院就是我在耶鲁的住宿学院,而这名W。 B。 路易斯,是学院最著名的院长之一,现在学院里还有一间以他命名的教室。
“我到达耶鲁的那天正在写一首诗,一首关于我童年的诗。我写这首诗已经写了一段时间,可是不知为什么,突然文思枯竭,写不下去了。
“来到卡尔洪学院后,我和路易斯院长寒暄了几句,就上楼去我的客房,想继续写这首诗。可是,我在桌前坐了好半天,仍然什么也写不出来。没办法,我只好把诗搁在一边,下楼去与路易斯院长共进晚餐。
“饭间,我们打开电视,突然,得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马丁·路德·金博士竟然被人刺杀了!
“我们都心情沉重,无心再吃饭,也无心交谈,匆匆互相道了晚安就各自回了房间。
“我走进我的房间,坐在桌前的灯下,看到被我搁在一边的诗,不由得拿起笔来,在后面添上一行字:‘在一个杀气腾腾的年代里……’
“在这之后,我用两分钟的时间,飞快地写下了这首诗的最后九行。”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试验树》(The Testing Tree)。”
停顿了一下,他清了清喉咙,开始读这首诗。
我从来没有对哪首诗如此好奇过。全场的听众们与我一样,屏息静气地捕捉着他的每一个字,等待着那最后九句的到来。
诗开始得平淡无奇:“我”在放学回家的小径上,一边眺望着学校的操场,一边在寻找石子;“我”找到了一条藏在树丛里的小径,沿着若隐若现的小路走下去;口袋里揣着石子,“我”站在一棵“无穷无尽的”橡树阴影下,走开五十步外,试图用石子投准橡树上刻着的目标。
“父亲不管你在哪儿/我只有三次投掷/祝福我的右臂完好。……”
诗的句式越来越复杂,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抽象,必须用心听才能理解每句话、每个词的意思。突然,老诗人提高了声音:
“……在一个杀气腾腾的年代里,
这颗心一碎再碎
并在破碎中生存。
我们必须走过
黑暗和更深的黑暗
而不能回转。
我在寻找那条小路。
我的实验树在哪儿?
把我的石子还给我!”
最后的一句话几乎是喊着出来的。真没想到,在这样瘦小干枯的身躯里,竟有这么大的能量。看得出来,在这么多年后,这位老诗人仍被这首诗的力量所感动着,仍能深深体会到二十多年前时写这首诗最后九句时,童年希望破灭似的彷徨、困惑、悲伤。
一片寂静,全场鸦雀无声,似乎一时无法从最后一句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的眼睛湿淋淋的,好像许多听众的眼睛都是湿淋淋的……
接着,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
第二辑 校内校外校园里什么饭碗最抢手?
九月初的“劳工节”宣告假期到此结束,美国各大学顿时又热闹得像集市,洋溢出一派兴奋的开学气氛。但是近年,这种兴奋总是夹杂着越来越强的忧心忡忡:学费逐年上涨,越来越成为大家议论纷纷的头痛难题。
回想起来,我的教育投资当年在我们家就确实是个大话题。
美国大学学费之昂贵是众所周知的。私立大学学费与食宿费加起来,每年总在三、四万美元之谱。而且大多数大学都要求学生们至少在头两年必须住在校方提供的校舍、在学校餐厅开伙,家长们只好乖乖地任学校的餐厅、公寓痛宰了。这还不说,更头疼的是,每年学费都会增长百分之三到四。也就是说,每年家长们得比前一年再多交学校一千多美元。像耶鲁,我当“新鲜人”进校那一年(1997年)学杂费共是32;505元,到我进入毕业班的第四年(2000年)升到35;685元,这几年更是加速上涨,现在已经上升到四万出头。
公立大学对于本州的学生,看在是本州纳税人的份上,学费标准要相对便宜,像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本州的学生一年学费才八九千美元,比私立大学要便宜三分之二还不止。上本州公立大学还有一个好处是学校离家近,回家的路费等开销较少,甚至可以就在家住、在家吃(在中国,这就算是“走读”吧),除了学费外,还能省出一大笔食宿费来。可是许多人觉得这样会失去许多在校园中与同学朝夕相处的宝贵体验,有人甚至认为,大学四年,从课堂上学知识只是受教育的一小部分,更丰富的知识、技能是从与同伴相处得来的。这种看法,也正是有的大学要求新生必须住校的理由。
中国人谁不希望子女上顶尖大学?但是一年三四万美元,四年十好几万美元,对于一般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来说,确实是笔巨款。幸好,美国大多数大学都有奖学金(颁发给学业或体育、艺术等方面的优秀学生)或助学金(financialaid,颁发给有经济需要的学生),奖学金与助学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通过竞争而获得,而后者不是。
不过,长春藤大学以及类似档次的名校,是不对学生们提供任何奖学金的,用哈佛招生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被我们学校录取本身,就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了。这里需要说明:过去,许多人对此有误解,像我父母看见耶鲁学生资助办公室第一年给我寄来的通知,上面有一项列着金额为11;612美元的“耶鲁奖学金”(YaleScholarship),以为这意味着校方对我的成绩的肯定和褒奖,当时有亲友来问我父母,耶鲁学费这么昂贵,怎么支付?父母便回答,学校给了“Scholarship”。后来才清楚:在长春藤大学这里,尽管用了“Scholarship”这样的词汇,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奖学金”,而是根据学生的经济需要而颁发的。周围不少亲友对中文与英文之间这个“概念差”体会不深,以为我得了多少多少“奖学金”,我也无法一一解释清楚:这里的“Scholarship”实际上是中文中“助学金”含义的一种资助,这里我借此机会一并解释一下。
长春藤大学以及类似档次的名校在助学金上十分慷慨。像耶鲁、哈佛这样财力雄厚的大学,录取学生都是不看学生家庭的经济情况,是否能负担得起学费的,这就是所谓“needblind”录取规定:只要认为你够格,录取了你,就决不会让你因为没钱而跨不进校门,你缺多少,学校就给你补齐。
通常,想向长春藤大学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在填入学申请表的同时要填一份联邦学生财政资助申请表(FAFSA),写明家庭经济状况,再附上家长头一年的报税表给大学寄去。大学通知学生是否被录取,也会告诉被录取的学生校方打算给他们多少助学金——金额多少是按照学生的家庭状况来定的。同时被好几所名校录取的学生,不妨跟资助办公室讨价还价。我的一位朋友,同时被斯坦福大学与纽约大学录取,纽约大学除了给她一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