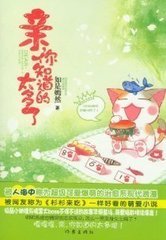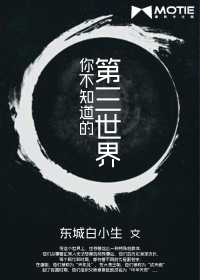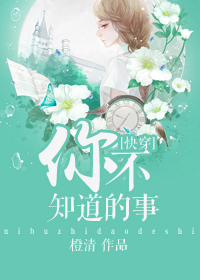知道点中国文学-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的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应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第五部分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冯友兰
《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惠能具有相似之处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传习录》上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满由政府任命官员代替世袭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广西平乱。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认为乱事的起因乃是两广官员“因循怠弛,军政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当反思其咎”,“自责自励”;又认为“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建议宜抚不宜剿。当年年底,王守仁来到南宁,两广、江西、湖广四省数万大军也云集南宁。王守仁按照他宜抚不宜剿的既定方针,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谈判,一面下令前方军队全部后撤以示诚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头目卢苏、王受来到南宁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这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并未妄杀一人。这一事件表现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是今天我们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资料。
《传习录》中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俩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统的代表王守仁哲学观点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关于“良知”,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第五部分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袁宏道《叙小修诗》
万历年间,明代诗文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其为首的是袁氏兄弟,即宗道,宏道和中道,尤其是袁宏道。他们的诗文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突破了儒学传统,文学上突破了复古的传统。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源起追溯到三袁,将他们的文学倡导与胡适的白话运动作了类比,指出他们实一脉相承。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三袁在文学史上的先导作用。没有三袁,也不会有后来的竟陵派和张岱等人的出现,而汤显祖等人也曾颇受三袁影响。到了清代袁枚的文学主张也与三袁遥相呼应。显然公安三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他们的文学本身的价值。
袁宏道(公元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与他的兄弟并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生在世间读书人崇古已到惟古是从却不知变的阶段,稍稍敏感度强些主题意识多些的文人都会觉得被古人的遗产压得呼吸不畅。但因“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便不知如何改变。等到与李贽相遇,恰如揭开了一块天窗,“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看袁宏道《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心集》诸篇,倚势筑屋,趁机传道,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反复宣扬,造成一股不小的话语势力,这也是一个新流派形成的必须之举。
袁宏道的文章按着自己的主张,不拾他人残唾,只要自己真实货色。但要为某一方向摇旗呐喊,总不免丧失分寸。对于他与他的兄弟们来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没有可以借鉴的榜样。任何值得参考的例子都有可能重新与复古派同流合污。“只要法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们读书不少,却不屑也不敢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任何经验都成为虚空。于是,他们在自己所倡导的文学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处于幼稚而伟大的童年。
袁宏道等人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书中的文言显然是不合“童心”的古人遗物,只有自己日常的话语才真算是自己的语言。于是三袁的文字浅白,近似于当时的白话了。但如此一来就很容易落入“过流”的陷阱,叫人如喝白开水一般,顺畅得很,又品而无味。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日常使用的书牍记序,他们开创的是被后人称为小品文的文体。朱光潜先生曾这样描述小品文的特点:“就大体说,随感录这一类文章是属于‘悟’的。它们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笔止,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各各自放光彩。”三袁都喜尚的禅宗的“顿悟”精神必然影响了他们的行文意念,由点带出,随意而至,无需刻意整饬造成结构之力。
随意之文,需有丰富多样的内容,厚积薄发的思想与激荡委曲的情感做后盾,方可造成叫人停顿的“涩”处,让读者也尝到“悟”的妙趣。如上所说,他们在文坛很早就形成的前驱地位与官场的得意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与体验。再者他们虽欲流自性灵,抒发自我,但他们缺乏造成委曲激荡的绝立孤独境界。他们虽与复古派文见相左,然而他们内部一直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体。兄弟间的亲情加上文学上的同道将他们的情感牵系得愈发紧密无间。手与足的交流何必遮遮掩掩,虚虚实实,又哪有除了亲切体贴之外的更复杂多变的情感?将心整个地交出,尚嫌笔不能随心,文字不够真切。在他们动笔之时,除了那些有关论文学主张的文字,面对他们的假象读者是至亲与密友,而不是需要说服与感化的对手。而这层关系又影响着他们的为文处人,扩散进整个文风。等二袁逝去,袁中道孤身一人,也是更多的将孤独感转为对二位兄长的怀念与对参禅的深入。对禅宗的喜好,又抑制了各自的自我张扬,最多是寄情山水了。《袁中郎尺牍·徐汉明》里,袁宏道在玩世、出世、谐世、适世这四种人中也只愿做适世者。“虽于世无所忤逆,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就是一种不明不暗的中庸状态了。袁宏道的后期文章更趋于平淡,看来也理所应当,就是多活几年,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第五部分闲情偶寄———李渔
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
———《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
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设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
———《闲情偶寄·戏曲部·审虚实》
不知有多少人看过林兆华导演的话剧《风月无边》,这部优秀的现代话剧就是讲述明清之际的戏曲大师———李渔的生平故事。
李渔(公元1610年—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人,别号湖上笠翁。他的前半生,正遇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原来家境优裕,亭台楼阁,因屡遭烽火,荡然无存。年轻时期的享乐生活,成为昨日幻梦:“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此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成霜。”其乐可知。这种生活养成他豪放舒展的性格。但生活的巨变,使他备尝忧患穷愁。为了生活,必须改变“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南京别业芥子园,开“芥子园”书铺卖书,卖诗文。组织家庭戏班,几十口人流动演戏,走了大半个中国,李渔当班主,自编自导,流动于达官贵人中,觅钱口。这使他在一定范围内跳出了文人的圈子,戏剧成了谋生的手段,专心一意地搞编导。生活的不幸却成就了他,让他为戏剧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说:“作文之事,贵在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一切生路全绝,便专在戏剧上了,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专”是李渔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晚年64岁(公元1678年)时,全家定居杭州西子湖畔,5年后贫困而死。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编辑了杂著集子《一家言》,死后50年(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有人编其诗文、杂著全集名《笠翁一家言全集》,其中包括《闲情偶寄》。《偶寄》又包括词曲、演习、居室、器物、饮馔、种植、颐养等部分。他还著有《窥词管见》,是论词的,22则,见解精彩。还写过传奇18种或曰16或15种,流行的是《笠翁十种曲》。其中只有《蜃中楼》、《比目鱼》较好;其中的《风筝误》即京剧《凤还巢》的底本。写过平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另名《连城璧》或曰《肉蒲团》。《闲情偶寄》内容博杂, 其中的“词曲部”是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中的里程碑。《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闲情偶寄》提供了中国古代较早较有系统的戏剧理论格局,标志着中国古代对戏剧特性的新的、甚至是归结性的认识。
在这位一身并兼剧作家、演员、导演、戏班主人的全能戏剧活动家的心目中,戏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李渔的戏剧理论首先强调“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