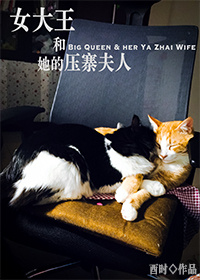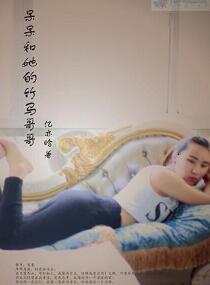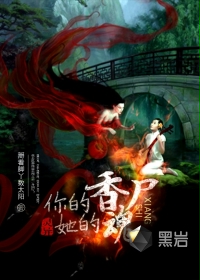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层!我希望他们十一月份能搬到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货,但是两口子用已经足够了。”
相对来说,宋庆龄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下一代所注入的热情与爱护,要比一般人浓厚得多。1977年春天,宋庆龄因病回到上海治疗。年轻的靳利平遵照父亲去江西前的关照,不时写信给宋奶奶,代表他们全家表达对宋庆龄的思念之情。这次宋奶奶回上海后的身体情况究竟怎样了?今天已是大年初一了,应该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宋奶奶。所以,1977年2月7日一清早,靳利平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宋奶奶。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7)
因身体的原因,宋庆龄于3月14日病情稍微好一些后才动笔回信:
靳利平:
二月七日写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春节祝贺。
我现在在上海治病。希望回到北京后看到你们。此致好意并祝你们新春好!
林泰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1978年,刚粉碎了“四人帮”的神州大地,万物复苏、万象更新。
就在这年,靳山旺结束了在江西进贤县农村长达六年之久的劳动改造。但是,极左思潮的阴影,仍笼罩在他的头上。这年5月,当他从中央警卫团转业时,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在他的转业证明上明白无误地写上了“不准分配到党政机关,只能分配到工厂”的字样。于是,靳山旺只得怀着一肚子的冤枉与辛酸,携全家告别北京城,回到了家乡陕西。陕西省政府把他安排在西安新华印刷厂,任命为该厂的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靳山旺从此已退出了政界,“四人帮”反党集团蒙在他身上的污垢仍没彻底洗清。
1979年3月14日,宋庆龄致靳利平的亲笔复信
但时年只有四十五岁的靳山旺从没放弃过他心底那种尽力为宋庆龄工作的愿望,哪怕是到了远离政坛的基层。所以,他一到新华印刷厂工作,就及时地写信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并寄去了当时厂里正印刷着的一些政治书籍。他知道,宋庆龄对这些信息最关注。
因为这次从江西调回北京、又从北京返回家乡陕西,一切都是上级安排的,所以,行程紧迫、行色匆匆。回到家乡后,他对宋庆龄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多么想把自己的一切情况再次向老太太一吐为快呀!
此时此刻,靳山旺越发怀念自己当年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了,那五年不到的时间里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幸福与高兴,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这种幸运了。为此,他甚至有点羡慕那个现在工作在宋庆龄身边的杜述周了。
那么,杜述周在宋庆龄身边又工作得怎么样呢?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1)
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人间天堂”,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
对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花的顾金凤进行暗中考察
杜述周受命顶替了S警秘的职务,调任宋庆龄身边担任警卫秘书时,正是江青集团登峰造极的时候,极左思潮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正常工作秩序与生活轨迹。在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究竟是迎合江青集团之流落井下石、向江青集团邀功讨好、飞黄腾达呢,还是顶住邪恶逆流,凭着自己的善良与正义感忠实地执行自己的使命、有效地保卫宋庆龄、维护宋庆龄家中的安宁与平静?对于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杜述周根本没有多想,当即以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作出了决定。
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既要不得罪江青集团,又要巧妙地实现自己的初衷,难哪!在那个全国一面倒的狂热的形势面前,自己左一点、右一点都不行,都可能得罪江青集团,自己由此遭到打击报复、打回山西老家还是小事,不能有效保卫宋庆龄才是大事呢!万一自己真的因此而离开宋庆龄、人家卷土重来的话,宋庆龄岂不要再吃二遍苦?
已年逾不惑的杜述周,竟然在这个问题上被难住了,陷入了苦苦思索之中。就在这时,邓颖超一个直接打给他的电话,使他豁然开朗:邓颖超在电话线那端明白无误地阐明了他此行肩头所担负的特别重任,还帮助他分析了当时他所处的大环境与特殊地位,解释了S警秘之所以被强行撤离宋庆龄身边的原因,接着,邓颖超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与重托,
宋庆龄为马海德祝寿于北京家中,后站立者为杜述周
她相信杜述周这个心地善良、人品高尚的国家干部,自会很好团结家中的所有同志,圆满地完成周总理交办的这个任务,准确而又巧妙地对付一切外来的不正常的干扰。最后,邓颖超给杜述周交了底,她希望杜述周有事多向宋副委员长汇报,碰到问题多与周边的同志们沟通,在遇到实在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宋庆龄直接找她与周总理。
邓颖超的这个及时打来的电话,顿时使杜述周一颗悬在半空的心落回了原处,胸中有了主心骨,紧皱了多天的眉心舒展了。他只是保留了S警秘当时的政治学习制度,除了每天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与政治时事外,其他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概予以摈弃。同时,他不管大会小会,都一再强调“团结”二字,强调“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弦外有音地督促与警示全体人员心无旁骛地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一如既往地尊重宋庆龄,服从警卫办公室的命令与指挥,不得有任何越轨的言行。
1972年,紧张的政治气氛有了较大的缓和,这也与中央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少有合适的人选担任外事接待工作有关,所以,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这时,索尔兹伯里发现宋庆龄虽年近八旬,但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那样健康”。
这应该与杜述周替换了那个S警秘之后的宽松和谐的环境大有关系。
但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宋庆龄,从没有为此盲目乐观,她在1975年11月7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就直率地表达了她对江青的认识:
“至于××,她是个自私的人,只是想利用我,但又企图不断地用谎言来使我相信她是我‘真正的朋友’。”
果不出宋庆龄与邓颖超所料,当时,江青集团阴损宋庆龄之心依然阴魂未散,1972年冬与1973年春,因患肠粘连与高血压长期卧床不起的保姆钟兴宝,终于成为了上海的江青党羽“排除异己”的借口。本来与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毫无关系的钟兴宝,成为了他们第一个驱赶的对象,他们竟多次派人来到淮海中路1843号,指令杜述周驱赶钟兴宝,接收他们另外派来的女佣。为息事宁人,也为了更好地保护宋庆龄,杜述周无奈接受了他们的指令,并经与宋庆龄私下密商,采取将计就计之策,暂时请兴宝回老家苏州木渎休养一段时间,同时,试用新女佣。
望着卧床不起的钟兴宝,为了能让她回到老家后,在木渎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尤顺孚的直接医治与照顾下尽快康复,宋庆龄只好忍痛割爱,接受了杜述周的建议。
1979年,杜述周与李燕娥合影于上海宋宅楼下
1973年3月8日,钟兴宝在从木渎专程赶来的儿子顺孚的陪同下,掩面辞别了宋庆龄。临行前,宋庆龄塞给她一千元钱,说道:“兴宝,侬回苏州去住一程吧,这点钱,给侬看病用。唉,伊拉要侬走,我也没办法呀。”说到这里,宋庆龄的声音哽咽了。
钟兴宝前脚刚走,由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那个新保姆就上班了。因她毕竟是上级机关派来的,再加上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替钟兴宝照顾宋庆龄,所以,杜述周尽管心里不踏实,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完全陌生的文盲大嫂上了二楼。
然而,真应了那句有比较才有鉴别的话,这个文盲大嫂与钟兴宝阿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她破例一下子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干起活来毛毛糙糙、粗手粗脚,不是昨天刚打碎了宋庆龄专门托安娜从国外带来的小镜子,就是今天“哗”的一声把一盆水全打翻在卧室中,硬是把地毯浸了个透湿。幸亏当时李燕娥因患了静脉曲张症,走路很困难,不在眼前,要不,她不被李燕娥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呢!
使宋庆龄忍无可忍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一阵,宋庆龄忍着病痛忙碌了几天刚写好一篇文章,就放在书房里。当晚临睡前,她提醒那新保姆:不要整理书桌。然而,第二天当她因病晚起了一个钟头、来到书房准备继续她昨天没完成的那篇文稿时,却发现其中最后一页怎么也找不到了。书桌就那么大,文稿也就放在那里,怎么会不翼而飞呢?肯定是那个新保姆不知把它弄哪里去了!因为能上她二楼的除了张钰外,只有这惟一的一个女性了。然而,昨晚临睡前,宋庆龄还再次关照新保姆不要整理书桌的呢!
“阿妈,阿妈!”宋庆龄又气又急,用上海话招呼那个同样是上海人的新保姆。
连叫了几声没人应,宋庆龄不得不蹒跚地走向书房门,打算再把声音放大些,然而,她还没走几步,书房门口就无声地出现了那个新保姆,硬是把宋庆龄吓了一大跳!这个不懂规矩的新保姆,竟连应都没有应一声,就踩着地毯无声地上了楼。
“啥事体?”她居然还如此没有礼貌,连“首长”两字也省略了。
“我放在书桌上的一页纸头到哪里去了?”宋庆龄压住心头的不快,皱着眉头问道。
“啥纸头?勿是都放在那里吗?”新保姆指了指书桌以反问作回答。
“可是,我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我要的那张纸头,就是写了字的压在最底下的那张纸头。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宋庆龄还是忍着气,尽量平心静气地询问对方。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2)
“早上,我理了理台子的,顺手拿这点纸头放一放好的。我可一张也没弄掉呀。怎么会没有的呢?”新保姆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开始上前弯腰俯身地寻找了起来。可是,她找了一会儿也没从桌底下找到一点纸屑。
“昨天,我叫侬不要动我的书桌的,可是侬……”眼见最后一页文稿当真不翼而飞,被那新保姆弄丢了,宋庆龄气得连话都说不囫囵了。
“我是好心,见侬的台子上堆得一塌糊涂,所以就整理了一下……”新保姆明知错了,还犟嘴。
这样的人还能用?幸亏是一页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稿,如果是国家机密呢?这还不闯了大祸吗?宋庆龄又气又急,当天就通知杜述周,请那位新保姆走了人。
这时,多种疾病缠身、年逾八旬的宋庆龄,日常生活已很难自理,身边已几乎一天都不能没人了。张钰再勤奋,她毕竟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顶替兴宝的家庭杂务。于是,杜述周连忙向上海市机关管理局重新要人。
没几天,又一个新保姆来报到了。竟是一个满口鲁中方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吞吞如蜗牛似的、长着一双粽子样的小脚(想必是小时候缠过小脚的)山东大娘!这种连自己恐怕也难以伺候的人,还能为宋庆龄服务吗?
宋庆龄哭笑不得,所有见到她的人也都忍不住掩嘴窃笑。
可是,杜述周却一脸难色,悄声地向宋庆龄汇报说:“首长,管理局说了,她是一个警卫员的妻子,政治上可靠,家务活干得不错的。我想,既然这样,我们也就再试试吧。”
为不得罪管理局革委会的领导,宋庆龄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那位小脚山东大娘。但愿她当真能干好家务活,接过兴宝留下的那摊子工作。
管理局革委会领导的介绍倒没有假,这位小脚山东大娘虽说行动不便,但干起家务活来却不含糊,洗衣扫地都能胜任,尽管她不会烫衣做饭干细活,但为宋庆龄梳头更衣也在行—因为她自己也从小到大就梳“芭芭头”的。
在这个极左的年代里,宋庆龄只好将就一些了,决不敢让自己的“小资情调”太浓了。
然而,没过两个月,那小脚山东大娘就开始不安分了,她先是偷懒使乖少干活,宋庆龄吩咐她干的活,她不是磨磨蹭蹭干上老半天,就是推三托四、不分轻重缓急,到了晚上,她更是赖在宋庆龄的卧室里,盯着那台黑白电视的屏幕不挪窝。更使宋庆龄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小脚山东大娘还特嘴馋,宋庆龄搁在那里的一些话梅、牛肉干什么的,她趁宋庆龄不在眼前,就毫不客气地拿着往嘴里塞……
这段时间里,杜述周与宋庆龄一样提心吊胆,惟恐这个小脚山东大娘接下来再闹出什么笑话,也怕她自己不慎从楼梯上滚下来。
使杜述周比宋庆龄还要着急的是,当时宋庆龄身上的荨麻疹严重发作,身上长满了无数樱桃那么大的红疱,头顶上也因此而大量脱发,尤其是当他知道这位小脚山东大娘的种种不规矩后,他还不能随时往楼上去,不能对她进行突击检查与教育,因为宋庆龄早有规定在先,任何男性不经她同意均不得擅自上二楼,除非警卫室里那代表着宋庆龄的专用紧急电铃骤然响起来。
当然,面对这窘迫境地,宋庆龄自也不会听之任之,她在日益思念钟兴宝的情况下,与张钰多次商量,保持着与远在苏州的钟兴宝的联系,她们期望着兴宝尽快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呢!
一番鸿雁传书后,1973年5月5日,宋庆龄终于向钟兴宝发出了召唤令:“有可能来上海一个礼拜吗?”于是,钟兴宝不待病体痊愈,在接到宋庆龄的这封来信后,一人来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