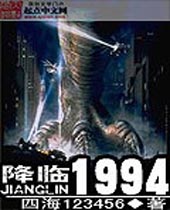3694-�й�����������ʮ��-��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ɽ��������ɽ��̽����ɲ������̨�سǺ����Dz���̨�����۶����У�������̨��Χ��������������ɽ���ڶ�����·�ϣ��ػ����ߣ������Ű��ߣ����Σ�գ�������Ը����¤����¤��ɽ����ת����ľ��粣���ɽ��������ǰ��Զ����ɽ�ͻ�������ʽ����׳ΰ����;ʮ��Ƨ�����羰�����������˻ƻ�ʱ�֣����ǵ��ﶹ�帽���ķ���������£�հ������ൾ�ϲ������һ�������ŵĹ��ڵ�������ƹ������һ���ڴ˵õ�һ��ʵ֤�ˡ���������µ������ΰ�����������ƴ�������ԭ����˽������Ƶ��ص����������⣬���仹���ƴ�ī�����������ʿ�֤������ʩ����һ���ˣ���������д�����£��ּ��ڽ�ǰ��ʯ���ϣ����Ǵ���ʮһ�꣨��Ԫ857�꣩�����ġ������д��ƴ�������ʮ�����Ʊڻ�һС������αڻ��������ⲻ�������Ƕ�����ʵ��̤�����õ�Ωһ�ƴ�ľ����������ǹ��ڹŽ���֮��һ�屦��Ҳ���ҹ��⽨�Ļ��Ų����������һ�����������ڻ�����ʯ�̾�����������שĹ��������κ�����ש��һ��������Ҷ�Ĵ��һ������������Ľṹ��Ȼ������쳣�����ǿ�ʼ����Ω������©���ʧ�������ǹ�����ʼ��ʱ����Ϊľ��������Ϳ�����죬û�п������������֣����Խ��Ƶ���֪������ȷʵ���������ͨ������Ľ������£���д�ڼ����ϡ���������Ϊ�С�ƽ�������壬�����ϲ��ṹ�����������أ�б�µ�����棬����ոڰ��⣬ֻ���������¿�϶��������ȥ���������ij����м������ȥ����һ�����������ֵ�̽�ӣ����������ѱ������̾ᣬǧ�ٳ�Ⱥ�ؾۼ������棬���������������������֣�������֪��������ʧ���������ּ���̽�ӣ���Ȼ���������϶��йŷ��ġ����֡����������ǹ���ľ���еĹ��������������⣬��ʹ���Ǿ�ϲ��������������������ǡ������ʱ�����ɣ��������ͣ���ľ��������ǧǧ����ij��棨����dz�����Ѫ�ģ����������ࡣ���������ʵǹ����������붥�ڣ����������Ϊ�飬���������й����ϣ�����ϸ����̽��Ω�ֲ��ܵ�����Ϊ��ʱ�������»�Ե�ѵã����β������ģ����ͼ¼�����꾡�����»Ṽ�����˵Ľ��ĵġ��������ǹ����˼��죬�ſ�������������Լ��ī���������ֵ����ҹ����������ּ����������ڸǡ�����������ɶ�ߣ������ֲ��㣬���������֣�����ȷ�档���������ã�����ƾ�Լ���Ŀ�����������������ϳ���ְһ���������ܱ����������������Զ�ӣ�������Ů������������֮����������������ϸ����ǰ�����ϵ����������ϳ��й�ְ���⣬��ȻҲ�С�Ů�������������ߣ���Ϊ���������������������֮ǰ�����������֮����Ȼд�����ϣ��ֿ��ڴ��ϣ���֮����Ӧ�������ͬʱ�ġ���ʹ����ͬ���˹�����֮����Ҫ���ڵ��깤��ʱ��������˾Ϳ����Ƴ��ˡ�����Ϊ������ֵ�ȫ�ģ����ǵ�ʱ������ɮ���ȥļ����ܣ��뽫���µ�����ϴ�ѣ�����������ϴ�Ƨ��ϡ������ȥ��һ���죬������ũ���ˣ������ֹ�����ȫû�о��飬�ﻮ��һ�죬��֧��һ�ܡ������Ѽ����ܴ��ذѲ���˺����ˮ���ഫ�ݣ�����Ҳ���˰����ϴ��������������һ����ˮ��ī������Ȼ�Գ�������ˮ��֮��īɫ�ֵ���ȥ������Լ���ɼ��ˡ���������ʱ�䣬�ŵö�������ԭ�ġ���ϲ����������Ȼ�Ʒ磬�����ɡ������������Ҿ���ξ������Ȼ���Ƴ��Ļ¹٣����ǵ�ʱ���ǻ���֪����������˭������������Ӱ������˺����Ǽ���̽�������Ľṹ��������������ʦ���ȡ���ʦ�������أ���Ȼ��κ�����������Ǵ���ı����ַ����������ܶ��أ�������ǰ��δ����ǰ����֮����ڶ�����࣬�䳤�Ⱦ��ˣ���ɮ����ľ��Ϊ���������������Ƿ��������ѱ澿����һ��С������һƬ����Ҷ��ʾ�����������ǵǺ�ɽ�����У�Ҳ����ľ��Ǻ�ɽ����ľ�����ǽ������в���ľ���������룬���ǻ�δ��ȷ������ʲôľ�ġ���������������Һ�ɽ����̽��Ĺ�����������䣬�����ļţ���Ȼ�����ӱ���ب��ʤ�أ���������������į���硣��̵ļ������µ��Ѳ����ˡ������ƴ���ʱ��ʢ����ͬ����һ���ܲ���ͬ��������ϣ�����д�ż�̫ԭ����������ϸ������֮�亱���شټƻ����ñ����취����������̨�����º�Խ����̨��ɳ�����������Ӿ����������أ����������죬������¬���ſ�ս����Ϣ��ս�±������Ѿ������ˡ���ʱ������ʤ�����ģ��������յп���������̤�ĵط������Ǵӱ��Ͻ�֪��ƽ����Σ�������֡�ƽ����·�Ѳ�ͨ������·Ω�б������ţ�����ͬ������ƽ�磬�ط���ƽ�������ֿ���ƽ��ô��ƽ���ָ���������������������Яͼ¼������ݷ�̫ԭ��Ѷ����Ӵ��س�����ͽ����ͬ��·��;�����������ʹҴҷ��֣������ϱ�������ͼ��ص���ƽ���Ǿ���������۵ġ�Ȼ�����������������ȫ����Ŀ�ʼ���˺�������ͼ����ƽ�����ɽ��ƽ�������糤���ݷ����������Ա�س����д����Ϻ��������Ϻ��ʼ��ڵأ�շת�������Ƕ��������������š�����ɽ������֮�����꣬������д��������ʱ�������ǵпܽ���̨���ľݵ㡣��ʱ���Ƕ�����ɲ֮�����������ƴ�ľ������������֮㷾��ạ̊́�����ʮ�ֳ��ء�����Ժ�����֪������²�Ω�Ծɴ��ڣ�������˵ë��ϯ�����ﻹס�����졣����������µ���ʷ��������������ˡ������Ļ����Ѳ��������⺱������ィ����ͬʱ������һ��������ģ�͡������������������飬��ԭ������Щ����������Ϊ�����ģ���Ϊһ��������ο����ϡ����������ĸ��������������������ף������������в�̵ȡ����ڷ��������ij��ȣ�һ������ȵ�λ���ϣ���һ����74���Ĵ��̳��̳�����������𣬸�����в���������ȡ����ļ�������ǽ�ħ���ȣ�̻���Ҽ磬���ִ�������ϥ�ϣ���������ӡ���������������ڸ�ǰ�������ڳ����������ϡ���μ�����������շ𣬴���˫�����ţ����ҽ��¸�������һ�䡣˫ϥ���������ƴ�������ʢ�е����ƣ������Ժ����ټ��ģ�������ֵ��ע�⡣�Ҵμ�������ǰ����ӷ�˫�����硰��οӡ��״�������������������ϣ��������ϴ����������ȵ����ң�����Ҷ�����������ߺ���������������ǰ�����������������������ϣ�������Ʒ�����պͰ����ӵ���в�̣��������������������⣬һ��������ͬ���������ն����ݷ�������������ֱ����������ʽ֮���ݡ������������գ����������üë�������Ŀڴ������Ǽ��������Ʒ硣���ռ������ӷ��ظ��������������������밢���Ӵ��ڸ����ϲ������ޣ������ƴ��Ĺ̶���ʽ������������ǰ��࣬����������������������Ҷ�Ժ����������������ػ�����ͬ��һ����������������һ�����һ����ţ��ڸߵٵ������ϡ�����������������ͬ��������ʽ�Ĺ����������ڹ����Ѳ���������ػ�ʯ���⣬����ɽ����ͬ�����±��Ƚ̲ػ��С���Щ�����������䣬�ܵ���ױ�Ķ��ˡ���Ȼ�����巽�棬ԭ״�еñ��棬�����ŵ�ɫ��ȴ��ʧȥ�������������������ʱ̼�����۰���ɫ�����մֲڣ�ɫ��������ͻ�ʻ���
���й�����������ʮ�����������ֵ�14�����¡�������̨ɽ����µĽ�����2��
�������ң����Ҽ����������������Ҽ�����������ͺ������������������������Ҽ䣬����������в�̣��������ǣ����������ǰ��Τ�Ӽ�һͯ�������Ҽ������ǹ�����������ʨ�ӣ�������ǣ��ʨ�ӣ�������в�̣����Ҽ�̳�ļ���ǰ�ǣ������Ż������������гֽ��������ΰ��ң�����š�̳����������Ҳ�����������С���ǹ����ߡ����������������������ŷ�̳���ڵ�����Ҽ䴰�£����������ĵ�������ɳ��Ը�ϵ�����ͨ�������ã���������������Գơ��������������������ҡ������ȴ��������������Ҳ�������������������Ϊ��ʨ����Ļ������а����ӻ����ǹ����������ı�־��Ҳ����Ϊ��̨������ĵ��������Բ�ʹ�����ڴ�Ҫ�ĵ�λ���������������������������磬�����������´������´���紹�£��ô���ϵ������ǰ���������£��ô�������ȹ�����������´�ɽᡣ�������������⣬����ǰ������ͷ���������������ƣ���ͷ���ڼ��ϣ����䷭���������Σ�������������ͬ��������ɭ���۾�����Ϊ������������ִ��������Ŀŭ�ӡ����ǵļ�����������Ĺ�г�������ٸ�����ƴ���Ҳ���ټ���ʵ������ϧ�ֱۺ��´����н�����װ֮��������̳�ϵ��������������ͨ��Լ5��3�ס�����������������Լ4��8�ס�в����������Լ3��7�ס����������ϵĹ���������ͬ������Լ1��95�ף�Լ��Ϊ����������λ���������ǰ�棬���ڸ������ĵ�λ�������������Լ4��1�ף�ȫ������ɭΰ��Ω����������Ը����������������������Сǫ��֮״�����ŷ����ɽ�ͺ���ǽ�Ĵ֣�������ǽ֮�������š������������ʵ����Ŀ�����پ�ʮ�����ǵ��ܹ�ӹ�ף���Ȼ���������ܵġ�������������������������һ������������һ����Լ��ʮ��֮���긾������ò����������������һ����֪��ʵд��Ф�����Ǵ����£����µ����Ӵ������Ϸ���������������������ͷ�ε����硣���������Ĵ������ɶ���������εķ����ɵġ�����������ػͱڻ��й������ͳɶ������ǰ�����꣨����Ĺ��������������Ů�ֵ������������֮�㣬��Ϊ��ʱѰ����װ�����Զػ���Ů��������������������Ƚϣ���ǰ����һ�������ñ���������ɫ���ţ�������Ů��ͣ���࣬�������ˣ������������ڷ�̳����Ϊ��С��ǫ���϶��������ԡ�����̬������ػͻ�����Ů�������ƣ�����̳��λ��������Ů���ڻ�֮��������ơ������������ܹ�����¡ɱ���ˣ�����������״ò��ȫ��������������������ƴ�����ϴ�����ŵ㣬�����������϶��ɵü�һ�ߡ�������ɳ��Ը���������Ҽ䴰�£������̳������������������ױ֮����dz��һ����ı��������࣬ǰ��¡��ȧ�Ǹ�ͻ�������ʴ��ݾ���ʵΪдʵ������֮������Ʒ��Ӣ�����е߲���Ժ������ŦԼ�в���Ժ����ʡ����Ϧ�����ǣ���ѧ����������������ɳ�����س�Ϊ�����ģ������ͬһ�������ʮ����֮��Ϊ����������ģ����δ��ų��������������֮ʮ��Ӧ�棬������fֱ��ʥ�¡���������������������ǰ������������������Ҷ������Ϊ����֮в�̶��ѣ�������֮����������������������νʮ���������С�ʮ���������ڷ�䣬���ж���Ϊ�����������ӣ��������ò����ӡ��Ȥ�����Ʊ��������Ϸ���ԣ����⼸������������������������ò���࣬���Ƴ������ǵ��͵��й�ɮ�ˣ���Ը��������ơ��ഫ�����������Ժӱ����أ�����Ҳ�����ع�ɲ�еĸ�ɮ���ڹ����ߵ�λ�������Ŷ���������������ġ�������Ը������ϣ��������仳��ʩ��ɳ�ţ����������ڵ��磬�ǵ�ʱ�ķ��С�����ƾ��һ����������δ���������ۡ��������������⣬���ڻ�����ʯ��������һ���챦ʮһ�أ���Ԫ752�꣩������ɽ�������������ʯ����������Լ1�ס������˶�������������������ϣ�������������ʽ�������ѻ٣����ָ�����ϥ�ϣ����������������£���ǰ�Ĵ��Ӵ��һ���ᡣɮ�µ��²����������������£���Ȼ�������з紵����֮�С�������Ե�����Դ�ֱ���ƣ���������Ȱ�����������ͬ�����ڽ��⾳���ۣ�����ò�طʣ����������У�����������֮�С������������ۣ�������������дʵ�Ե����࣬�Ƹ��и��Եĸ��ˣ����ҹ���������У��Ǻ��ټ��ġ������������ձ��Ķ���ij���ϵ����������������ַ����������ȫ��ͬ�����dz���ͬһ��ʦ���֡������������������������ơ������������ߣ����߾��Ƿ��ϵ���ʦ�������²���������û������ʯ��������ܱ������еı��𣬲�֪��ʱ�������й����ġ����������ڴ���ɽ�ϣ�1973�����������Է�������ı��������������ע�������ڻ������������ּ�¼���硶���������ǡ�������������¼������ͼ������־�����鿴�����ƴ��ķ����ٲ��ñڻ���װ�εġ��������������������۱��ϣ����бڻ����ڣ���ԭ�бڻ�֮�ý���ġ�������Щ�ڻ�����ŵ����Ҵμ�ǰ�ڶ���ϱߡ����۱ڳ�Լ450���ף���Լ66���ס��乹ͼ��Ϊ���飬����һ�飬�Է���Ϊ�����ӣ�Ϊ���ģ�������в�̣������һλ�ǹ�������ɱ档��ɫ���ʯ��ɫ���⣬������ɫ�����������������Σ���һ�ɳ�����������ɫ���������鶼������Ϊ���ģ���С����Ϊ����������������Ҫ����֮�ԣ��ָ����������������������ӡ���������ƺ���̬��������Բ����Ʈ�������ƣ����主���Ʒ硣��֮�����˸���ɮ����������һ����ɮ���������ģ��϶�һ���Ǵ����Ĺ��۷���ڵ��ˡ�����֮һ��Ȩ��̴٣�������Գ����룬��ػͱڻ��������ģ�ͬһ��ʽ�������ͺ���ıʷ��������к����ŷ磬��Ӫ����Ĺ������������������ͼ���ʷ����ۣ�����ڻ���ػ��ƴ��ڻ����������ƣ���Ϊ�ƴ�ԭ��֮�����ԣ�ʵ�ں��ٿ���֮�㡣�ػ����⣬�ƴ��ڻ�֮���ڡ�������ԭ���ģ�����������֪�����е�һ����1964�����ڴ������������������ƴ�ԭ���ıڻ���������������ע����ʹ����д��ڵ�Ҳ��Ȼ�Ǹ����������ƴ�ԭ���Ҵ�Ľ������ϵģ������տ��ܴ����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