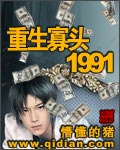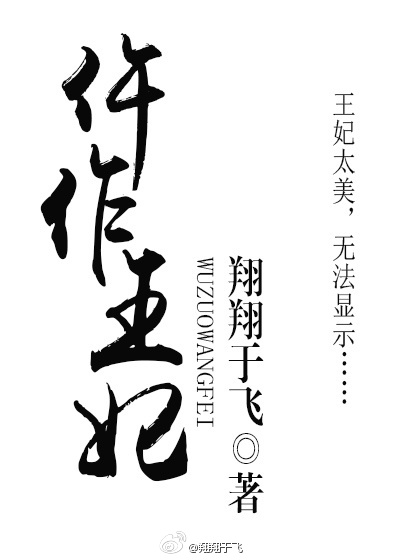5491-美元硬过人民币-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章将要结束之际,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小夏在昨天证明了一些什么?器官的健康。前途的无量(我忘了提及一次健康之外的有趣的身高和体重测量。小夏一米八一,比去年增长了一点五公分。体重净增八点七公斤。而东平和刘松的有关数据,因不能给他们增添任何荣耀,所以就此省略了。)。反应的灵敏(对射中击毙了所有的对手)。
现在东平和小夏走向刘松乘坐的那辆的士,带上车门。他们向三许巷驶去。
三人行三人行 六
刘松几乎每年都来N市和东平一起过年,就像他没有自己的家一样。不然,他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家。刘松从来就不缺什么,尤其是人人都十分需要的家庭。主要是家庭的概念起了变化,这事的确不能怨刘松。读书的时侯他有家庭,正确的解释就是他父母牢不可破的家。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够成了这家里并非就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后来住校,在单位住集体宿舍,他有了一伙朝夕相处的朋友。那时家的意义对刘松而言就是这么一伙哥们。他和东平的友谊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结下的。到后来,像人人都要经历的那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男人的家。当时他们喜欢使用的词是归宿。在精神上的归宿之外还得有一个具体的屋顶,他们结盟为住房而奋斗。女人、房子加孩子,三者够成了经得起任何推敲的家的概念,可时间轻轻的一击就把它彻底地推翻了。我是说时尚,在今天那最有诱惑力的家的概念是什么呢?对于刘松,对于东平,或小夏这样的间接经验的获得者,对他们而言最理想的家就是一所空房子,空得让人心慌,空得让人发■,那该有多么地令人神往呀?
刘松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他有一所房子在南方的某市。东平的情况正如大家知道的,他有房子,但需要照顾母亲。小夏呢?虽暂时没有拖累,但也没有房子。从感觉上说,还是刘松的家最正宗,最像家,除了一处房子什么也没有,甚至包括他自己。他的家空得厉害,令人恐怖,因此才引发了小夏某种类似于崇拜的感情。就是历经坎坷的东平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刘松有一个到了上学年龄的儿子,他不能把他作为家庭的一员来照顾──为了保持家的纯洁性。儿子跟他妈过,而他妈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妈,也就是儿子的外婆。既然刘松能把儿子从家的结构中划出去,其他的任何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我指的是那些女人。她们相继想在他的空房子里占有一席之地,一两个小时还可以,顶多饶上上半夜。上半夜一过他就思念起儿子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在这里呆上整整一夜,这些水性杨花的女人又有什么权利呢?让她们留下就是对儿子的犯罪。于是他毅然决绝然地把她们从热被窝里拖出来,赶到寒冷黑暗的街上去。他也只有在那时才会想到儿子。
也许因此那些能讨他欢心的女人一般都带有孩子气。她们让他更多地想起儿子,或许,还能部分地代表儿子出现在他的面前呢。她们比较容易从这个角度进入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又是什么?一所空房子,里面有一张特大的床。她们的进入使他记起了自己的儿子,随即又由于她们的存在他把儿子遗忘了。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从来不缺,永远是二十岁不到的年龄,平均为十七岁零九个月。总有一天儿子要长大成为她们的同龄人,他也得变成她们的父辈、祖父,可她们依然固我地停留在十七岁,的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
东平和刘松认识时,他(刘松)初恋的情人是五十年代出生的,比刘松要大,教会了他许多。后来他的情人们就变成六十年代出生的了,刘松儿子的母亲就属于这个年龄段。而目前刘松已进入了七十年代的领地,正手持镰刀准备到八十年代的稻田里去收获(她们暂时还没有成熟)。东平预言,总有一天刘松会和他的儿子因此打破脑袋的,他侵犯了他的领域,他们(父与子)的时代交错混合在一起,那还不乱了套?所以东平为他的朋友考虑,一向主张刘松把他的爱情定位在七十年代,这已不算苛求,七九年出生的女孩到现在满打满算,怀胎十月算在内也不过十五虚岁啊?当然,这是东平为刘松着想的极限,为他不远的未来所做的计划。刘松呢?对于这一前景竟十分恐慌。他说:“再过二十年,他们不都三十多了吗?这怎么得了!”
不过,刘松还是理智地接受了东平的建议,他的现任女友七五年出生,今年正好十八岁。他和她已经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长得就像一辈子。对于他的过去她从不过问,这恐怕是她能够呆下去的秘密。一天刘松告诉她自己离过婚,并有一个六岁多的儿子。对方说:“如果你没有这些事哪才不正常呢。”刘松喜欢听到她这么说。
当然他不会因此而放弃到东平这里来过年的习惯,就像动物的迁徙一样,每年北上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他准备带着这个叫小丽的姑娘一道走。通知了东平,临时刘松又变了卦。他一个人松松垮垮地来了,不见有人像尾巴那样地跟着。“发生了什么事?”东平按常规理解道。“什么也没有发生”,刘松说。东平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刘松故作姿态。“票都买好了,饭也吃了,最后还是没让她跟着来。”刘松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接下来的几天里东平一直督促刘松给小丽去电话,最起码得让她知道,他没有从天上掉下来。刘松一如既往地并不反对,听筒拿起来了,号码也拨了好几个,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东平问:“为什么?”“不知道。”“你既然能给那些毫不相干仅仅认识的人打电话,为什么不能给她打一个?”“不知道。”“我认为这种与众不同的对待说明你对她很在乎。”“也许是的。”“就给她打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啊,又不是别的什么,打了又能怎么样?”于是刘松又拿起听筒,拨号。他将听筒递到东平的耳朵上:“打不进去,占线,不能怪我啦。”
“你和小丽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还行。”
于是一次轮到刘松跟东平回西村时,东平特意谈起了这个问题。他不顾刘松的干扰、怠懈和大而化之,执意要谈,且主题鲜明。不得已,在香烟、咖啡和东平意志力的作用下刘松的谈论比较感性和具体一些了。他说到他怎样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她走的时侯没有站起来送她。她说走了走了,还是没走,实际上她是想让他送她。她这样要求他所以他决定不送。当然,如果不要求他他也不会送的。只不过不要求送她就没有送她这回事了。一刻钟后她给他打来电话(她是自己打的回去的,把自己关在父母以外的闺房里),说她多么多么地想他能够送他。她已经把自己灌醉了,在他够不着的那头泣不成声。她告诉他她喝了整整一瓶人头马VSOP,他在心里为她计算了一下时间,刨去下楼行车用的她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大约在四分钟内她灌下去一瓶匍萄酒,真够勇猛的。然后他就听见了她的呕吐声,这引起了他的反胃。但总的来说他还是有所感动,不然这样的小事也不大可能记住。
另一件叫人感动的事也与小丽有关,但主角已经不是她了。那是一条叫叶利钦的小狗,本来是刘松喂的,后来因为后半夜绝对寂静的需要他把它送给了她,以示自己对任何人(或狗)都不特别偏袒。而她也正好对此作另一番理解。既然她不能随时随地和他在一起,那就把那条来自他的狗当做他吧。至少她是和它呆在一起的,它是他的代表、信使和兄弟。后来他故意疏远她,以及她知道了他并非特别地专一,还有他那免不了的过去,在孤苦无告中她是靠叶利钦才支撑过来的。后来她打电话给他,告诉他那狗死了。当时他们隔绝已有三个月,他再次听见了电话另一端她的哭声。那是为一条小狗而非她自己的高尚的眼泪。她啜泣着告诉他:她把它放下楼去到草地上小便,用一只篮子从窗口徐徐下降。它坐在里面,稳当得很,以前她就是这样干的,可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她把它放下去,还没有到底它就纵身一跃,或者是篮子自己翻了。然后它就摔死了。她把它埋了也已经半个月了。她问他是否会因为当时没有告诉他,而会感到不快?它就这么死了。也许是出于和它最后在一起的人见一面的愿望,他才建议他们一块吃一顿便饭的吧?于是分裂的状态就这么结束了,至今。
在东平的影响下小夏也关心起刘松的爱情问题。有一天东平特意没有去西村,而是安排他俩去了。小夏缠着刘松谈了一夜,自以为很有收获。第二天晚上又是东平和小夏去西村了,两人经核对,发现刘松一连两个晚上的叙述竟完全一样,都是讲了两件事:人头马和叶利钦。小夏坦率地说他并未受到感动,倾听中注意到的只是人头马,那得多少钱一瓶啊?小丽一仰头就灌了下去,肯定流了一身一地,那该有多浪费!当时小夏就这么问了刘松。刘松淡淡地说:“一时找不到别的酒。”东平实在弄不清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更虚无一点。刘松虽然是在背台词,至少声音是令人感动的。小夏不受迷惑,他只专注那些更实际的事物,比如自己的身体,身体中的体力,那些纯粹的属肉体的成分。
三人行三人行 七
小夏是个身体狂。中学时代就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于三伏天最热的时辰──中午一点钟在家门口的公路上练跑步,为的只是身体好。然后是大学、到电厂工作,在各类各种级别的运动竞技中小夏虽然长于罗致奖状,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他的想法和原则。在小夏那里,好身体的概念总是和实际应用分不开的,它不应是单纯的比赛而应有利于生活。所以小夏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牌技、速度和命中率。他一向强调和自鸣得意的是他的臂力、记性、勃起时间,也许还有预感。他很会神话自己,问起来人五年前见面时他所戴的一条围巾,它的颜色以及那人围系的方式。对小夏而言,这些都历历在目,如在目前。他以帮助别人修复历史的方式取得信任,再以这种信任去加固他在历史方面的权威。当然对于女人他的口味未免单调,只要身体好,体壮如牛就足以引起他的兴奋。只要年纪轻、经得起他的折腾就是好女人。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和任何不健康的女人睡觉,她们由于内部的腐烂而散发出阵阵口臭。他怕诸如此类的女人玷污了他的纯洁之体,带走他的活力和精华。而与此对抗的意志说到底也来自于无坚不摧的身体。小夏一整套的哲学都是由身体发源的,以至最后抵达他的灵魂和神秘的领域。比如他对自己文学上天份的确认就是从超常的视力和敏感的嗅觉开始的,由此达到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的可能,达到意志力所具有的专注,达到精神上的通神。他的贡高我慢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十分实际和清晰的路线。
谈完刘松的爱情问题之后,话题自然由爱情而到女人,由女人而及性。东平问小夏:性的开放局面到底是释放了某种本来固有的本能,还是夸大和刺激了它?讲白了就是,一部黄色录像给人的到底是欲望的满足,还是挑逗了欲望本身?如果是前者,黄色性感倒是社会安定的一剂良药。相反,它就是不应该倡导并要加以限制的。小夏对政策问题不感兴趣,但他聪明地认为:今天人们的性欲是越来越强烈了,强烈到已脱离本能的地步。牛马还有发情期,人唯独没有,他一年四季三百六十天随时随地都能干,都想干,真是绝了!即使是人老力衰、硬不起来,他仍然还是想。人已完全晋升或堕落为一种心理动物了。每当他渴望和异性结合时,你能判断这是一种生理要求,抑或是一次心理上的下流?“分不清,实在分不清”,小夏说,“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真正本能意义上的性交吗?”他问。“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及牛马,还有猪。我们太可悲了!”作为小夏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自我崇拜者,也许就是奇耻大辱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告诉东平)他一直想找回那种不带任何心理感受的纯粹的本能。他的方法在别人看来就是典型的性压抑,小夏拒绝和任何想和他有一腿的厂里的姑娘们睡觉,甚至包括他正式的女朋友。他在夜深人静中等待着自己真实的本能发动,等待着他那像牲口一样的明白无误的春季。他听见体内血液流动的声音,夜半高空传来的神秘话语。至少,他可以为他的自制力而感到骄傲了。同一时刻在我们的星球上城市中在同一栋宿舍楼里有多少男女在苟合?甚至在小夏的隔壁就是有那么一对。他们互相撕咬着、舔噬着,翻来覆去,呻吟不已。独立于这些堕落的男女之外,仅凭这一点小夏就被自己感动了。
奇怪的是,越是在他洁身自好的斋戒期,和姑娘们无条件性交的机会就特别多。有一天小夏自觉他的季节到了,跑去找主动献身的她们,不是正来月经就是有了正式的男朋友或已经结了婚了。要不就是无缘无故地拒绝,作为对他上次拒绝的报复。小夏的来势凶猛、不能自已,他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本能,那就是:不来则已。
“后来呢?”东平着急地问。
后来小夏就想到了小时侯。小的时侯,直到上大学离开家以前,小夏都不知道什么是饿的滋味儿。因为他妈那时在家专职做饭,喂养小夏的兄弟姊妹还有他们的爸爸。小夏随饿随吃,一吃就饱了,所以他不很知道什么是饿,虽然理解字面意思。上了大学,对于运动量超常和身体特好长个子的他来说,饿就成了家常便饭,饿了食堂还没有开饭,那种感觉就被固定下来了。最后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基本的感觉,随时伴随着他。小夏就是从这时知道的:饿并不等于吃,不等于饱,它和吃饱是两个概念。饿了有时得忍着,经常得忍着,慢慢地,你就习惯了,也好受多了。这就是小夏得出的结论。后来他把这个结论运用到性欲方面,也还算比较成功。他明白:性欲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