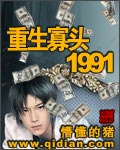4699-大厝·钟宅-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 路上,金花一个劲儿地絮叨着,“到了那里,一定不要乱跑乱动,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做错了什么会被长辈们骂的。” 我应允着,可满脑子却在想着那奇怪的问题—祖墓怎么能吃呢?
《大厝·钟宅》 旧事谁晓香火中的家族盛宴(2)(图)
整个闽南地区,对清明是很重视的。外出的人都要尽可能地赶回来祭拜,旅居海外的人也都要汇寄家费回来,在家中备办丰盛的五味筵碗孝敬厅中祖先的神位、厝主和地基主等。不知道钟宅的“吃祖墓”是不是指这个…… 等我回过神来,三房的祖墓已经到了。令我惊讶的是,钟宅人的祖墓竟然不在山上,而在村里楼宇间的空地上。金花说,这儿原来是很荒凉的,可这几年房子越建越多,祖宗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小了。不过这是五个“房”里修得最好的墓。长房和五房的墓找都找不到了,所以扫墓就到祖厝里去;二房的祖墓比较特殊,原来是墓的那块地方现在盖了房子;四房的祖墓离三房的不远,是钟宅五个房里修得最新的墓地。三房的祖墓是典型的闽南墓室结构。墓地很大,前前后后该有百来平方。左右两侧各蹲着一只活灵活现的守墓狮雕。墓地中心是隆起如龟甲的墓冢,又称墓龟,前面是墓庭与墓埕。外围顺坡筑着一道矮墙,边缘留设着一弯小水沟,做排水之用。 整座祖墓处在楼房的包围中,惟独墓的正前方无遮无拦。金花说,在钟宅,祖上流下来的习俗,祖坟的正前方是不许盖房子的。所以,在如今钟宅争先恐后见缝插针盖楼的时候,祖墓前才能难得地留下这一片空地。 我们到时,祖墓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男丁们抽着烟,三三两两,或立或蹲。一个老阿伯蹲在正中的墓碑前,拿着笔描着什么。我走上前一看,老人正在一笔一画地给墓碑上的旧字描红,面前的小盏里盛着朱红的汁液。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解释:“每年都要重描一遍的。风吹日晒,褪色太快了。” 墓碑上刻着“明皇祖妣钟门孔氏儒人墓”的楷体字,两边是两幅凤凰祥云图,前面的供品桌前则刻着龙头鱼身的麒麟。我纳闷地转头问金花:“这里葬的是女祖先?” 金花点点头说:“好像是吧。因为男祖先的墓找不到了,所以就拜女祖先喽。”她的解释甚是可爱,她说:“反正祖宗夫妻在阴间也是在一起的,拜的时候也一起受礼就是了。”这种“怪论”估计也只有这些能干的钟宅媳妇才想得出来。 墓的左边祀着一碑,刻“福德”二字,据说这是土地公的别名之一。闽南一带皆以土地公为守墓之神,所以连祖厝内也常供奉着土地公。民间相信,人死后是由土地公带路去阴府的,土地公是阴神,城煌爷是他的直属上司,墓旁或宗祠内祀有土地公,以做守墓或带路之神。 忽然间,一阵女人们的笑声传来。我这才发现,祖墓后面的空地上搭建着好几座灶台,各种各样的食物零乱地堆放着,大脸盆、大桶、大锅,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碗筷一箩箩地排开。几个女人家正围着灶台七手八脚地忙活着。有的拉了根水管在洗菜、杀鱼,有的则靠着灶沿切肉、剁骨头,灶台上的锅已经架好,火苗“哧哧”地冒着,灶台上一阵水雾蒸腾。一个媳妇过来,掀起锅盖,转头对着旁边喊:“水开啦。你那鱼杀好了没有?”“差不多啦。你把那筐给我递过来。” …… 媳妇们的喊笑声打破了男丁们的沉寂,那慢慢溢出的菜香使这个安静的清明早晨声色俱全。>;>; >;>;男人的祭祀 不一会儿,男丁们来的渐渐多了起来。大家像是都分工好了,来了也不多说话,彼此仅点个头,问声“来了”,就开始分头忙活。有些人扛着锄头、带着铁锹和扫帚,先用锄头把墓地周围的杂草锄净,清理墓埕。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似乎生怕用力过猛会破坏了祖宗的“房子”。 还有几个男丁挑着一担担的箩筐过来,打开盖,是满满的牲礼和供品。几个长辈围上前,帮忙把东西一样样从筐里端出来,再一样一样地在坟前的供台上摆开—一块猪肉、一个大发糕、一只鸡、一条鱼、十二个红、十二个红面桃、一条牡丹烟,一瓶高粱酒。供品的摆放也似乎颇具门道:鸡和肉并排摆着,两边放鱼和鱿鱼干做牲礼脚,鸡头和鱼尾朝里,意寓做事有头有尾;放着的三个酒杯各斟满酒;还有冥钱,分寿金和插金两种,一捆有一千张,数量不一。 清完坟,摆好供品,祭祀仪式才正式开始。长辈先点燃两支白烛,立在碑前。他们认为,阴阳两界的时差是相反的,点了蜡烛,祖先才能看见来时和回去的路。接着,把香点燃,再令祭拜的男丁每人也各燃三炷香。金花告诉我,按常理,只有拜神时才能点三炷香,而拜家族祖先是只能点两炷的。也许,在钟宅人眼里,能传下六百年子嗣的祖先也该是成仙了的吧,所以他们选择了以对待神仙的礼遇来伺奉祖先。看来,光这上香就有不少的学问。 长辈们说,土地公是守墓之神,上香时得先给土地公上,得到了土地公的允许,祖先才能被牵引出来;祭拜时,是不分长幼前后的,不过男丁们要先拜。男丁们拜时,墓地里一片安静,一群人站在一起,正对着墓碑,手心对着手心紧贴,执着香,闭着眼,若有所思,连灶台边的女人们也噤住了声。不过,男丁们终究是比较随意,拜完了,鞠了三个躬,就把香插到香炉里,然后就“哗”地散开,各自找个地儿一边站着去了。 接着才是女人们过来祭拜。金花说:“早些年,因为觉得女人晦气,钟宅的清明祭祀是只许男丁参加,女人是不能来的。不过这些年好多了,风气开化,再加上男丁们越来越多,过来吃饭的人也多了,只好叫女人们过来帮忙。慢慢地,原来那些规矩也就松了。” 女人进不了祠堂的故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一个。那个在鲁四老爷的斥呵中萎缩下去的生命,就因为她是女人,就因为她死过丈夫和儿子,她便永远失去了祭祀的权力……多少年前,在钟宅,这儿的女人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因为是女人,她们不能入族谱,不能进祖厝,等到她们的身份被认可的时候,也是她们成为“祖先”的时候了。 就像此时长眠在这方墓穴之下的那个灵魂,当她活着的时候,或许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会有这样一群人对着自己三跪九叩。可即便如此,又能证明什么呢?此刻的她也不过是自己丈夫的替身而已,墓碑上只有一个“钟门孔氏”,她连自己是谁都没有权利留下。 此时,几个女人家放下手里的活,擦干手,有点羞涩地穿过男人群,围拢过来,弯腰,鞠躬,跪拜,嘴里念念有词。女人显然比男人认真,也细致,那匍匐在地的执着,唇翕蠕动时的严肃,都让人感到她们对这一场祭拜的在乎。那一瞬间我很想知道,此刻,在女祖先面前,她们求的是什么—是为自己?还是为丈夫、为儿子、为女儿?抑或是为整个家族?—或许,这场家族的祭祀是母系社会沉淀下来的源髓。
《大厝·钟宅》 旧事谁晓香火中的家族盛宴(3)
拜完了祖先,就该为祖先修房子了。人们总是喜欢用现世的生活去构筑那未知的世界。钟宅人说,人间的房子旧了就要自己想办法翻修,祖先的房子旧了却只有靠子孙们来修,不然就是不肖子孙。所以每年清明子孙们一定要帮祖先修好房子,祖先才不会怪罪。
而所谓的“修房子”,就是在墓冢上“压纸”,闽南一带又叫“挂纸”。如果说,坟墓是祖先死后居住的场所,那么挂纸就象征子孙一年一度为他们的居处添新瓦。
“修房子”自然也是男丁们才能做的事。眼见着四五个男丁将薄薄的彩色油光纸裁成宽约四寸、长约六寸的纸页;然后用波纹状的钢錾在中间錾出三四行波纹状的曲线,这些“墓纸”呈长方形,颜色有黄、白、绿、红、蓝五种颜色,如此两三张一叠;然后用小石块分别压在墓头、墓碑及墓旁的“后土”(土地神)上。
小孩子们最喜欢“压纸”了,几个小男孩在男丁群里蹿来蹿去,从旁边的地里捡来一大堆的小石子,另外几个孩子则争着去抢叠好的墓纸。
听见有男丁嗔斥着:“去去去,小孩子家一边玩去。”
小男孩们可不管这些,依旧在那里左蹦右跳。
“让他们压好了。”人群中有长辈说,“小孩子轻,这样才不会压坏了祖先的屋顶。”
人群中一阵哄笑。闽南的习俗是只要将墓纸沿墓龟四周间隔压住就行,可钟宅有些不同,他们要把整个墓龟全部压满。
男孩们得到了老人指示,在众人的注目下显得特别的兴奋和得意,比赛看谁压得多。一个小女孩也兴奋得想跑过去,却被母亲一把拉住。小女孩一脸委屈地看着母亲。
“你不能去的。你不是男孩。”
“为什么?”
母亲沉默了半天,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向女儿解释,好久,说:“长大了就知道了。”
于是,她们和许多女人一样,默默地站着,看着男孩子们在墓龟上跳来跳去。很快地,一张张五色斑斓的冥钱密密地盖住了整个墓龟,远远看去宛如野地里盛开的花,使这片原本灰暗、荒凉的坟山,凸显红绿纷披。
这时,墓地里开始热闹起来。男丁们互相分着烟,寒暄着彼此的近况;女人家则又回到灶台边,哧哧的油炸声和哄哄的煤气炉响,都暗示着午餐时间的临近。这时候,有一些晚到的族人陆陆续续地过来,点香、行礼,似乎一切都已十分熟悉,简单地行完礼后,或独自蹲到墓边,或者站到旁边跟人说话。只有一个四十开外、有点腆着肚子的男丁有些例外。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硬币,双手合掌,闭上眼,对着墓碑若有所思。好半天,他略弯下腰,松开手,硬币掉下了。
“他在求什么吗?”我不解地问金花。
金花告诉我,他这是把硬币当圣杯使呢。她曾听她公公说过,一般人清明祭拜就是求个平安,只有要干某件大事的人才会在清明这天来这里求问,希望能在祖先的坟前得到一个明确的指示。至于他所求的事是好亦或坏,就不得而知了。
果然,他掷完硬币回过身,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旁边的人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加入大家的话题。》》
》》纸片里的迢迢心愿
天色渐渐亮堂,似乎临近中午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声:“烧纸吧。”大伙又都“嘤嘤嗡嗡”地从四周聚拢到墓碑前,每人拿着一叠冥钱在手里,站着围成一个圆圈。有人在中央点起了火,人们各自把冥钱一张张往火里扔。据说,这样齐整地烧,一来钱的数目比较清楚;二来祖先带回去时也比较方便。大伙像是排好了节奏,你一张我一张,中间的火苗燃得越来越旺,升起的烟雾缭绕在整个墓地,一切都变得有点恍惚起来。
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叫一声:“那不是志仔么?”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正由两个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向祖墓走来。一时,很多人迎上去。近了,才发现老先生的腿脚有些颤抖,气色也不太好。一位叔公牵着他的手,不停地说:“真的是志仔啊!真的是你啊!”那位老先生也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嘴里却念叨着:“总算赶上了。总算赶上了。”
“这人是谁?”金花跑到前边向一位长辈打听。
“这是志仔啊,咱们钟宅早年的大学生呀,后来就一直住在上海,好多年没见他了。”
一个阿伯为志仔点了香,老先生有些吃力地走到墓碑前,握着香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想弯腰,对着搀他的人说着什么,可是还是有些吃力,只好放弃了。但他还是固执地亲自把香插到香炉里,然后,回过身,对烧银纸的族人们说:“我跟你们一起来烧吧。”有人从别处搬来了把凳子,老先生坐下,接过旁边的人递过来的冥纸。一边烧一边说着话。
我们这才知道,志仔已经十八年没回钟宅了。志仔说:“一直就想着回来,回来上炷香,再看看钟宅……本来前年就要回来的,可是腿脚不好。今年稍稍好些了,这不就让儿子开车送我回来了。”“十八年了,咱们钟宅的变化可真大呀。”他用手笔画着,“以前这南边、还有这东北角,哪有这么多房子呀,全是种菜的旱地,现在真是不一样了,热闹多啦。”
有个同样满头白发的老人走过来,志仔一眼就认出了他,握着他的手直说:“昶哥,咱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还记得吧,咱们年轻时清明也拜拜的,喏,也是在那边,临时搭了个灶台,就蹲在那边上吃饭。那时哪有这么多人呀。咱们钟宅好哇,人丁越来越旺啦。”老先生像打开了记忆的匣子,一直说个不停,脸上泛着一股喜气和兴奋,一串串的惊讶和感叹仿佛要把人拉回到那个遥远的过去,也使这里的空气一下变得轻松和热闹。
忽然间,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老了,再远,也要回来一趟,谁知道明年还看不看得到呢……”
“哪会呢。你身子好着哩。”大家听出了老先生的伤感,纷纷安慰他。族人们围在一块,你一句我一句,更显得热气腾腾。
风吹来,冥纸灰扬起,细细碎碎地在墓地四周漫天飞舞。身旁的女人说:我们现在烧的是给祖先的钱,烧完了停几分钟,再烧给土地公。这样,土地公才不会卷了钱,扔下我们的祖先自己先回去。而且,烧冥钱的时候,不能搅动,要让冥钱慢慢地烧,要不会把冥钱弄破,钱破了祖先就用不了了。
这时,金花在我旁边小声地说:“上次听人说,有过世的人托梦,让阳间的亲人以后不要再烧那种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额的冥钱了,因为冥间的银行找不开那么大的票子,所以钱是多,可是花不出去呀。”
“呵,原来阴间钱也有花不出去的时候呀。”我自语着,有些想笑出声来。
眼见着族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