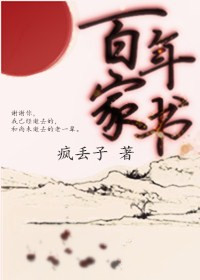百年记忆-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脱胎换骨,象海市蜃楼一样,你只看到远方的一片仙境,但你永远也走不到地方,它是一个永远的诱惑,一种永远鞭策你在劳动中安于改造的动力。
最高境界的脱胎换骨虽然是抽象的,但每一天的脱胎换骨却是具体的,经过一段时间劳动,我对体力劳动已经适应了,我不再把劳动看做是一种惩处,而看做是一种有希望的脱胎换骨,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在农场几年,我是最安心于脱胎换骨典型人物中的一个。无论分配我做什么活,从来不讨价还价,劳动中不偷懒,不和任何人交头接耳,不听到哨声不休息,也不象吸烟的人那样,动不动地就站在地头吸一支烟。就是为了偷这一点点懒,许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人也学会吸烟了。因为劳动中你不能把农活停下来,但是你可以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吸烟是允许的,不会吸烟的人则还要干活。我不吸烟,就是低头干活。
农场劳动绝对超过8小时,早晨6点起床,草草吃过早饭,人们就争先恐后地下地了,也不是农场有什么要求,就是一个“表现”,劳动态度好,是脱胎换骨重要标志,我自然不能落后,也就跟着积极改造的人下地了。
初来农场时,队长说先要过劳动关,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劳动关是用不着过的,每天劳动有定额,干不完定额,回到班里要受“帮助”,大家一起干活,任何人也不得偷懒,谁不出力气,大家都看得出来,不等回到班里,就在地头上骂你了。我有自觉,在劳动上总是最卖力气的一个。
其实在农场里,最难过的既不是劳动关,也不是生活关,农场里最难过的大关,是争取摘帽关。为了争取摘帽,每一个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这样,没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着别人表现了。
第一年国庆节,突然宣布给两、三个右派摘帽子,右派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摘帽之后,右派们看到了希望,立即农场里的气氛就变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成为明年国庆节摘帽的右派。其实我对这几个摘帽的人做过分析,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们的摘帽,可能是把他们整错了,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背景,赶个机会,就说是摘帽了。这种机会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别人只是右派,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就是全农场的人都摘了帽子,也还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远休想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
右派们的种种表现是很精彩的,有人劳动时拚命地干,烈日下光着大半个身子,突然一声喊叫,晕倒了,大家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拾起锄头又接着耪地,情况汇报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扬,做为表现,就记在队长的印象中了,来年摘帽子,就是一个条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动不动地就往队部交思想材料。还有人检举他人反动言行,于是农场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一些反映劳改农场生活的小说,把右派们一个一个写得那样美好,以我几年农场生活感受,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们是被美化了,一个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时候,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农场里只能比社会更露骨,也更残酷。
就是在右派们争先改造立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农场已经任命右派做班长了。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本来只有属于内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长,譬如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就是京剧团的小武把子。这类人坏得很,许多班长在地里总是向学员们要这要那,他们出工时自己不带烟,想吸烟的时候,就向右派学员要,有的右派学员投其所好,就“喂”他们烟吸,他们得了这些人的好处,就对这些人格外关照,而不肯给他们烟吸的人,就总被他们汇报。更有的班长向学员们借饭票,借钱,反正就是占右派学员的便宜。这种事,农场渐渐知道了,于是农场开始挑选可靠的右派做班长。这些右派班长,把当班长看得非常神圣,不像那些小坏蛋,把班里搞得一塌胡涂,右派班长对于各项要求都非常认真,学习,劳动,头头是道,把班里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规,队部也很满意。
右派班长比那些小坏蛋班长厉害多了,他们有文化,他们能够看得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还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对抗改造,随便一点小事,他们都能分析出立场观点来,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农场改善生活,早晨炸油条,每人发一个小纸,拿小纸去买一两粮票的油条。油条买回之后,我们新上任的班长给大家做工作,班长对大家说,今天早晨农场为了改善生活,浪费了几百斤油。我这个人就是爱多嘴,这时我就在一旁说:“吃到人肚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如果这句话被小武把子班长听见,他可能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但右派班长的嗅觉灵敏,他一下就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我才免了一场大祸。
小武把子当班长,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此外谁爱做什么,他一概不管;右派班长却什么都管。我从外面带进来了几本书,全都是我最离不开的那些书。小武把子班长看见我看书,还颇有点敬重,右派班长上任之后,他不允许我看书了。他说读那些书对我的改造不利,他规定学员们只能读马列的书。这一下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选拔右派当班长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长全换成了右派,这一来连那些小坏蛋们也老实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内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们交给右派班长管理,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老实了。右派班长也不和他们发威,右派班长会找他们谈话,会对他们做工作,会对他们的一行一动做阶级分析,这一下,他们再不敢捣乱了。他们知道只要右派班长到队部一汇报,他们就休想出去了,因为他们和右派不一样,右派送进农场,没有出去的希望,他们表现好,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长时时盯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听话了。
过了些日子又开了一个大会,几个摘掉帽子的右派,被召回市区重新安置工作,在大会上摘掉帽子的右派,扬眉吐气,似是就要回家做大官去了,农场更要以这件事教育全体学员,让大家看到只有老老实实改造才有前途。大会开过之后,一辆汽车拉着几个摘掉帽子的右派回市里去了,许多右派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心里也热热乎乎地颇为激动,但我知道,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市里去了,我也还是要留在这里的。
几年农场生活,使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我变得无忧无虑,农场里许多右派都愁眉苦脸地生活着,只有少数几个人,活得极是轻松。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自尊,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觉不到失望了。他不再尊重自己,他也不再尊重他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他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
我从小受的教育,极有礼貌,苟于小节,但到农场之后,我光着膀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一点也不觉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还是穿着它上工下工,城里的乞丐都比我穿得体面。我的一顶草帽,连帽顶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每天顶在头上,好歹也能遮些阳光。
我喝生水,吃才从地里拔下来的青菜,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而且我还学会了骂街,骂最难听的粗话。
第四部分 脱胎换骨十三、脱胎换骨(2)
还是那些小坏蛋,他们看我好欺侮,就总是和我过不去,动不动地就向我耍威风。最先我总是躲着他们,由他们骂我。有时候他们故意拿我寻开心,无意中打一下、踢一脚,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乐儿”。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在他们和我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农田地里,放下工具,我向他们骂了起来。骂人的话,不外就是那几句罢了,他能骂出口,为什么我就骂不出口?妈妈姐姐地,我就骂起来了,这一骂,真把他们骂傻了,他们没想到我也会开口骂人,今天我真地骂起来了,他们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这样,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就是后来干起活来的时候,我也是一面干活一面骂街,骂得那些小坏蛋们没有一个敢出来答言。
这一骂,骂出了一个朋友,大家叫他大刘。这位朋友40多岁,自幼参加革命,抗日时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建国后没有来得及休整,一个命令下来,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说,他是一个革命功臣,但不幸却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样,被送到农场来了。
大刘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对我说过。反右斗争开始,他是积极分子,在单位里领导运动,让他主持斗争会,批斗他们单位里的右派。一天,又是开批斗会,大会休息的时候,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看没有外人,就对一个人说:“鸣放时不是让人家说话吗?怎么又说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呀……”说着,他就从厕所出来了。回到会场一看,会场里的标语改成“右派分子刘××必须低头认罪”了,原来他在厕所说话的时候,被人偷听去了,立即汇报到最高领导,他因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降级降职降薪,送到农场改造。但他对于自己的当右派满不在乎,到了农场也是胡不讲理,稍一不高兴,破口就骂,连土皇帝马场长都不敢惹他,更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东西。就是平时走在农场大院里,他也是骂不绝口,他没有文化,也没有多少词汇,他骂街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了,枪毙不了我,我就操你妈妈!”农场对他很感头疼,就分配他赶大车,尽量少让他在农场里呆。赶大车可以天天到市里去,他可以中午在市里吃馆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他不参加学习。
在农场里,从马场长,各队队长,到每一个学员,人人心里都有一本细帐,谁最厉害,谁不好惹,谁天不怕,地不怕,谁破罐破摔,谁又最胆小怕事,谁最好欺侮……那是人人心里都清清楚楚的。队长们开会点名批评什么人,都是找好欺侮的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谁也不敢惹,象大刘这样的人很有几个,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砂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路上大刘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他们狗操的们。”大刘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点来,逮捕证没法签,这才交给公安局代管,收在了这个农场里。只要你不杀人放火,这个农场也没法送你去监狱。懂吗?这叫隔离,什么叫隔离?你们有学问的人叫软禁。中国没有软禁,就叫隔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软禁,就不是硬禁,顶天也不能给你戴铐子,你只管把心放在肚里,你越孙子,他们越欺侮你。上次开会,那个王八蛋队长问你是什么东西,你真不理他,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看他冲着你挥拳头,他不敢打你,他打了人,他犯错误。他们为什么叫你?他们早研究好了,你年纪小,胆小,读书的孩子,没经过世面,拿你开刀,有震动力。从今之后,你就天不怕,地不怕,让他们看出你是豁出去了,破罐破摔了,你也不想好了,你也不想出去了,他们也就不打你的算盘了。”
感谢大刘,他向我交了底,原来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能是看着这些人,他们不能任意处置这些人,他们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送进去,他们也没有权利想给谁摘帽子就给谁摘帽子,他们就是奉命在这里看管右派,不能把他们留在城里,也不能治他们的罪,还得吓唬着他们老老实实。因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们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们送回公安局去受点罪,却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毕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渐渐地大刘和我关系越来越近了,跟车出去干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对我说,“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要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怀疑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军心。其实上级也没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如今总算把知识分子划出来了,送到农场来,也不怕扎堆儿了,留在外边的知识分子也老实了。可是也不想想,没有知识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胜利吗?”大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干部,他对革命有自己直觉的看法。
“别以为脱胎换骨这4个字是什么人发明的。”大刘也有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我才肯听他讲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得脱胎换骨。都是参加革命,我们就不问什么动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先要说明是什么动机。为什么?农民就知道二亩地,革命胜利分二亩地回家种地去了,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他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了,革命胜利只给他二亩地,他不干。所以得先说清楚,你是奔着什么来的,是不是想捞一把。再说,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革到半路上,一个不顺心,走了,农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