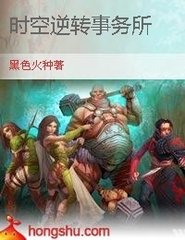逆转死局-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全是谎言,”莫瑞尔半起身,咄咄逼人地冲着法官的脸说话。
“谎言?”艾顿法官重复了他的话,戴上眼镜。“那个女孩不是无罪开释?”
“你知道我的意思!”
“恐怕我不明白。”
“我并不想要那个女人,是她穷追不舍。我没法子。我对她没有意思,那个小笨蛋就想杀了我,她的家人捏造了这个故事好博取别人对她的同情。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从没威胁过人,也从没有过这种念头,”他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顺便跟你说,这一切康丝坦思都晓得。”
“我想也是。所以你不承认那场审判提出的证据是真实的?”
“不,我不承认,那都是间接证据。那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看我?”
“没事,麻烦你继续讲。我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没关系,你继续讲。”
莫瑞尔把背往后靠,呼吸沉重缓慢。他用手顺了顺头发。先前摆在嘴里一角的口香糖,现在又嚼了起来。没胡碴的方正下巴以规律的节奏挪动着,让口香糖在嘴里吹泡出声。
“你以为你把我调查得一清二楚,是吧?”他质问。
“是的。”
“假如你弄错了呢?”
“我愿意冒这个险。莫瑞尔先生,这场会面已经进行得够久了,不用我明讲,我从来没这么吃瘪过。我只剩下一个问题,多少?”
“哦?”
“多少钱?”法官耐心地解释。“才能让你放我女儿一马,从此消失不见?”
房里的阴影越来越深,空气也转凉了起来。莫瑞尔脸上掠过一抹奇异的笑容,白健的牙齿露了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脱下不舒适的衣服,摆脱掉一个难演的角色。他往后坐回椅子,抖了抖肩膀。
“毕竟,”他笑着说,“生意归生意,对吧?”
艾顿法官闭上眼睛。
“是的。”
“可是我非常喜欢康丝坦思。所以你得给我个好价钱,非常好的价钱,”他让口香糖在嘴里吹泡出声。“你准备付多少?”
“这么说吧,”法官不动感情地说,“提出你的条件。你不能要求我估量你值多少,我想你也不是两先令半克朗就打发得走。”
“哎呀,你这么想就不对了。”莫瑞尔愉快地说。“幸好,问题不在我值多少,而是康丝坦思值多少。她是个好女孩,你知道的,如果父亲大人,您,低估康丝坦思的价值、贬低康丝坦思,那就太不应该了。是的,你必须准备为康丝坦思付出合理的价钱,加上一点利息补偿我受伤的心。那就——”他思考着,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游走,然后抬起了头——“5000镑?”
“别傻了。”
“她不值那么多?”
“问题不在康丝坦思对我值多少。问题在于我能筹到多少钱。”
“是这样吗?”莫瑞尔起了兴头地问道,侧着头看法官。脸上又闪过笑容。“这个,我已经出价了。如果你要继续讨论,你得提个价码。”
“1000镑。”
莫瑞尔揶揄他。“别傻了,亲爱的先生。康丝坦思自己一年就有500镑。”
“2000镑。”
“不成,太低了。如果你说3000镑的现金,我还可能考虑。我说我‘可能’考虑,不是‘会’考虑。”
“3000镑。这是我的底线了。”
两人一阵沉默。
“那么,”莫瑞尔耸了耸肩。“好吧。如果你认为康丝坦思就只值这些,那就实在太糟了,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很清楚客户什么时候到了底线。”
(艾顿法官的身子稍微动了一下。)
“3000成交,”莫瑞尔提出结论,嚼口香糖的模样显得心意已决。“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我要提出条件。”
“条件?”
“我要确定你不会再骚扰我的女儿。”
莫瑞尔这么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却不在意这个条件,似乎有点奇怪。
“随你怎么说,”他让了步,“我只要看到钞票就好。现金哦,那么——什么时候?”
“我现在户头里没那么多。我需要24小时的时间筹钱。还有一件小事,莫瑞尔先生。康丝坦思现在在海滩,如果我把她叫来,告诉她这桩交易,会发生什么事?”
“她不会相信你的,”莫瑞尔马上答道。“你也知道。事实上,康丝坦思料想你会玩什么把戏。我亲爱的先生,别冒这个险,否则我明天就跟她结婚,打翻你的如意算盘。等我拿到钱,你大可跟她说我的——嗯——恶行。等到那个时候吧。”
“这个,”法官声音透着古怪,“对我倒是方便。”
“什么?交钱吗?”
法官思考着。“我听说你会参加在陶顿的派对,是吧?”
“是的。”
“你可以明天晚上8点到这里来吗?”
“乐意之至。”
“你有车吗?”
“哎呀,没有!”
“没关系。往返陶顿市和通尼许镇的车每小时有一班。你搭7点的车,8点就会到通尼许镇的市集广场。只要走出通尼许镇中心,沿着海滨路一路走来就会到。”
“我晓得,康丝坦思和我今天走过一次。”
“不要早到,因为我可能还没从伦敦回来。而且——你也得想个借口,向康丝坦思解释你为何离开派对。”
“编借口我拿手得很,别担心。那么……”
他站了起来,拍了拍外套。房间里光线昏暗,只能假设两人都没注意到彼此脸上的表情。两人似乎都在倾听潮水拍岸轻柔的隆隆声。
莫瑞尔从背心口袋拿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心。光线太暗,法官看不清是什么。那是莫瑞尔习惯放在口袋里的小口径左轮手枪子弹。他把玩着子弹,仿佛是子弹为他带来好运。
“现在是你的表演秀,”他有点恶毒地说,“希望你演得开心。可是——康丝坦思现在在下面。我们该口径一致。你要怎么跟她说?”
“我会说我同意婚事。”
“哦?”莫瑞尔紧张了起来。“为什么?”
“你还给了我什么选择吗?如果我不同意,她会要求解释。如果我给了理由……”
“好吧,那就如此,”莫瑞尔思考着。“她会喜出望外——我可以想像——24小时内,她的心情都会很愉快。可是,笑容很快就会被抹掉。你觉不觉得这有点残忍?”
“‘你’跟我讲残忍?”
“不管怎么说,”莫瑞尔满不在乎地冷静说道,“听你祝福我们、看你跟我握手,会让我心情舒坦些。你一定得跟我握手,并保证支付婚礼的庞大费用。太糟了,你得让康丝坦思承受这一切。就看你表演了。那么,我现在去叫她喽?”
“去吧。”
“好戏开锣了,”莫瑞尔把子弹放回口袋,戴上他那顶时髦的帽子。他的身影衬着从窗外透进来的朦胧夜色,身上那套浅灰色西装的腰身显然收得太紧了。“下次你见到我时,请叫我‘我亲爱的孩子’。”
“等一下,”法官一动也不动,“假设我筹不到钱,会怎么样?”
“那么,”莫瑞尔指出,“那就太糟了。再见。”
他再次把口香糖在嘴里吹了个响泡,走了出去。
艾顿法官仿佛在思考般呆坐不动。他伸长了手,拿起那杯没动过的双份威士忌,一口气把它喝光。先前放在桌边的雪茄受了冷落,已经熄灭了。他使劲站了起来,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靠墙的桌子边。他把电话推到一旁,打开上层抽屉,取出一封折起来的信。
光线太暗,他没法儿读信,可是信里的每个字他都记得。这是“首都与外地银行”当地分行的经理给他的信。虽然语气极为客气,但摆明了银行不愿再让艾顿法官预支现金,因为他透支得太厉害了。还提到他在南奥德利街及柏克夏郡菲尔市两处房子的贷款——
他先把信摊平放在桌上,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把信扔回抽屉,然后关上。
海浪窣窣一路把夜晚的呢喃传了过来。远处,一辆汽车的引擎震动着。任何人看到艾顿法官的样子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没有人看到)。他结实的身体像洗衣袋似的没了筋骨,咚地一声在旋转椅上坐下,两只手肘靠在桌上。他摘下眼镜,双手盖住了眼睛。他一度举起两个拳头,像是要大吼,却只是默默地放下了手。
外面传来脚步声、低语声,还有康丝坦思有点牵强的笑声,提醒莫瑞尔他们已经到了门口。
他慢慢地戴上眼镜,在椅子上转过身来。
以上是4月27日,星期五傍晚发牛的事。隔天晚上,安东尼·莫瑞尔先生没搭公车,从伦敦搭了8点的火车前往通尼许镇。在市集广场,他向人问了要怎么去海滨路。另一位证人的证词指出,他在8点25分到达法官的小屋。8点半(电信局的记录)有人开了一枪。一颗穿过脑袋的子弹让莫瑞尔先生命丧小屋。等凶手发现什么东西在受害人的口袋时,已经太迟了。
第五章
电话交换所的女孩正在读《真实爱情故事》杂志。
佛萝伦丝有时好奇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如果是假的,这份杂志才不敢刊出,而且这些故事听起来都像确有其事。佛萝伦丝想到故事里的那些女孩,羡慕地叹了口气,不管她们再怎么堕落,总是能让自己得到些乐子。从来没人要用这些有趣的方式让“她”堕落。虽然这些欢场女子的生活最终一定很悲惨,可是……
总机唧唧作响,红灯也亮了。
佛萝伦丝把电话接上线,又叹了口气。希望不是像几分钟前的那通电话,一个女人从公共电话亭打来,想打长途电话却连一毛钱都没有。反正只要打电话来的是女人,佛萝伦丝都不喜欢。故事中的那些女孩虽然后来都悔不当初,但她们可真正“体验”了生活。她们出入豪华赌场,与不良分子往来,还卷入谋杀案……
“请告诉我号码?”佛萝伦丝说。
对方没回答。
小房间里,滴答声响亮的钟敲了8点半的报时声。佛萝伦丝觉得滴答声给人一股安慰。寂静中就只有钟的滴答声,佛萝伦丝沉醉在白日梦中,而电话线仍是接通的。
“请告诉我号码?”佛萝伦丝回过神,再问一次。
然后,事情发生了。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口气非常急迫地低语着:“沙丘之屋。艾顿的小屋。救命!”他急促含糊地说了这些话后,接着传来一声枪响。
佛萝伦丝当时不晓得那是枪声,只知道耳机里的碳粒在她耳边噼啪作响得令人难受,感觉像钢针刺入大脑。她在总机前跳了起来,接着听到呻吟声、扭打声和巨大的重击声。
尔后一片安静,只听见时钟滴答响。
佛萝伦丝非常惊慌,但头脑还是很冷静。有一会儿,她扶着桌子,看着钟,仿佛祈求指引到来。她向自己点了点头,赶紧接上另一个号码。
“通尼许警察局,”一个年轻但自尊心极强的声音回答,“我是文斯警官。”
“艾伯特——”
音调变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急促低声的抱怨,“别在我当班的时候打电话来——”
“可是,艾伯特,不是这样的!有一件可怕的事!”佛萝伦丝说明了她刚听到的事。“我以为我最好——”
“非常好,小姐,谢谢您。我们会处理的。”
在电话的另一头,文斯挂上电话,惊愕中带着怀疑。他把这个情形告知警局的小队长,小队长搔了搔厚实的下巴,面带犹豫之色。
“法官,”他说,“搞不好没什么事。可是,要是真有人想杀了那个老家伙——天哪!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艾伯特,赶快骑脚踏车到那里,快点!”
文斯警官跳上脚踏车。从通尼许警察局到法官的小屋大约有四分之三哩。若不是中途发生状况,文斯4分钟就可以骑到。
当时天色已黑。傍晚下了一阵雨,雨虽然停了,这个温暖的春夜没有月亮且带着湿气。在车灯照射下,沿着海岸的这条柏油路闪着微光。每隔两百码就一盏的街灯让黑夜显得更加幽暗与难以名状。与海边的树一样,街灯一副孤寂凄凉的模样,空气中充满浓烈的海水味道。文斯听到这个涨潮期碎浪击岸的断续隆隆声。
就在他看见右前方法官小屋的灯光时,突然发现眼前有辆汽车,刺眼的车灯让他几乎睁不开眼睛。这辆车停错边了。
“警察先生!”一个男人的声音,“嘿,警察先生!”
出于本能,文斯停下车来,一脚踏在地上。
“我正要找你,”这个人继续说,“有个流浪汉——喝醉了——菲罗斯医师和我……”
文斯认出了这个声音,是巴洛先生。巴洛在这里也有一栋小屋,靠近侯修湾另一头的海岸。说不上来为什么,年轻的文斯非常尊敬巴洛先生,仅次于对艾顿法官的敬意。
“先生,我不能停下来,”他又兴奋又急切地喘着气说。文斯自觉身负重任,因而把这件不该公开的事告诉他信得过的巴洛先生。“艾顿法官那边出了状况。”
文斯的声音划破黑暗。
“状况?”
“发生枪击事件,”文斯说,“电话接线生这么认为。有人遭枪击了。”
文斯蹬上脚踏车快速离去,看见在车边走动的巴洛先生渐渐没入街灯的光团中。文斯后来想起巴洛先生瘦削脸上的表情,车灯照着他半张脸,嘴半开着,双眉紧蹙。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脏污的法兰绒裤,没戴帽子。
“快去!”巴洛严肃地说,“火速赶去!我随后就到。”
文斯奋力地踩着踏板,发现这个人紧跟着他,踏着大步跑得飞快。文斯觉得有点丢脸,竟然有人可以用跑的追上执法人员,文斯相当震惊。他踩得更猛,可是这个人还是跟上了。文斯在艾顿法官的门前跳下脚踏车,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出现了另一个人。
黑暗中看来模糊苍白的康丝坦思,就站在大门边。木栅栏挡住了她一部分的身体,风吹乱了她的发丝,连身裙紧贴着她的身子。就着脚踏车的车灯,文斯可以看见她泣不成声的模样。
巴洛呆站着望着她。打破沉默的是警官。
“小姐,”他说,“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康丝坦思回答,“我不知道!你最好进去看看。不,不要进去!”
文斯打开门时,她想伸手制止

![星光逆转[重生]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1/2196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