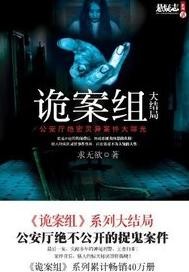狄公案_湖滨案-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彩币。批了八字,换过庚帖,那边只等选吉期迎娶了。
(妁:读‘硕’,媒人。——华生工作室注)
“一日,一个朋友叫万一帆的告我道,这江文璋虽是读书识字的人,却是个衣冠禽兽,登徒子一类人物。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听说还是黉门的败类,诽薄周礼,被逐出庠校。我闻此言,心知上当,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允,整日哭得泪人儿模样,茶饭不思,恹恹成病,一连几日米汤都未沾牙。贱荆又哭又闹,阖家鸡犬不宁。我没计奈何,肠子一软,也只得任他们去了。前夜江家轿马迎娶,倒也十分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得认了。酒席上只喝了一二杯,聊为搪塞,便告辞回家。
(黉:读‘洪’,古代的学校。庠:读‘祥’,古代地方学校。——华生工作室注)
“今日一早,江文璋气急败坏跑来宅下报凶信,道是新婚之夜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急问端底。这老狗支支吾吾,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如花似玉、灵生活动的一个人儿如何一夜工夫便死了哩?内里岂能无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报,推过一日。他道是江幼璧也潜匿失踪,他们须得寻着儿子问明端底,好来报信。江幼璧至今还未寻着,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藏匿起来。等混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一我当即要去江家看看小女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云昨日已草草入殓,灵枢都移后到了城外石佛寺。”
狄公双眉紧攒,禁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又未肯打断刘飞波话头。
“狄老爷,天下哪有不让尸亲见尸便偷行闭殓的?王法昭彰,这其中的鬼域伎俩,伏望老爷明镜断勘。好替小女伸冤,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此刻王玉珏、万一帆两证人俱跪堂下,听侯老爷垂问。”
狄公捻须沉吟,半晌无话。
江文璋抬头正想要张口说什么,狄公摇手止住。又问:“依刘先生意思,可是江幼璧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
刘飞波忙道:“这个……这个江秀才本是木雕泥胎,无用之物。我此刻推想来,凶犯应是他老子江文璋。江文璋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老奴狂态,早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婚筵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止,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烈志轻身。这江幼璧自然怀恚抱恨,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待要徵声发色,又怕坏了门风清声,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竟自合忍,婚妻已死,日后苟且有何生趣?究竟不是吕布之勇,手刃董卓这老贼奴消恨,故只得半夜一走了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江文璋畏罪,乃匆匆厝殓了月娥,意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作主,间断案情本末,由我亲手剐他二十四刀;才解我心头之恨。”言罢扑簌簌掉下泪来。
(恚:读‘会’,怨恨,愤怒。——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听其情词可悯,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为转脸问江文璋。
“江文璋,本县问你,适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属实?”
江文璋颤兢兢抬起头,叹道:“回老爷话。贫儒平日不理家政,犬子迎亲也是贱内一手张罗。月娥的事来得突兀,家吓懵了,一时都没了主张,仓促收厝,也是实情。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并未入土。棺盖草草加了几颗钉。倘王法不容,愿当罪咎。乃若亲家翁诬贫儒有不齿行经,实属谤渎之词,一无依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贫儒究竟是读书之人,礼义传家,诗书延泽,焉会去行那等猪狗不如没廉耻之事?惟求老爷明鉴。”
狄公频频颔首,问道:“令郎迎娶,这新婚之夜究竟什么一回事”
江文璋抬头见狄公威而不猛,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肠子渐宽。乃详述道:“昨日宅下都用过早膳,见已巳时初刻,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环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且等些时辰。转眼巳时交尾,时近午牌,新房内仍无动静。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日,里面只不答应,也无声响。老朽这才觉识有些异样,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及进去一看,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帐衾簟席全都染红。犬子幼璧竟没了踪影。贱内上前摸了脉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冷了。
(簟:读‘变’,竹席。——华生工作室注)
“老朽赶紧去对西街访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孔掌柜作中人见证。华大夫来验过身道,月娥系新婚初合出血不止,竟乃血山崩,终于死亡。华大夫又道如此入伏天气血污尸身,千万不可停留,须及早收殓殡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稳婆,替月娥抹洗了,便草草收盾于一具薄木棺内,暂移城外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厚殓了送坟址。
“这是新娘的事。新郎没了去向更令老朽焦虑。半夜出事后,他定是情急慌张,丢魄落魂。又羞于唤众人呼救,以至蹉跎延误。待见月娥已气绝,他更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情知也说辨不情,说清白了又怎样?不如一走了之,必是自寻轻身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直令老朽疑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闩的,窗槅木栅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了?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我乃命众人四处寻找,直至昨日半夜尚不见影迹。
“今日绝早,家人手拿犬子系身的黑丝绦来报,道是南门湖上一渔父在湖中拾得,情知是投湖了。果然祸不单行,江门合当断后。老朽哭得昏死过去几回,忽又想到此事尚未报信于亲家,便又跌跌撞撞、巅巅巍巍赶到刘府宅院。谁知被他一把攥住,完不松手,一直拽到这衙门里老爷堂上。老爷亦可怜我这个孤苦老人,一日之内连丧爱子新媳,乐极生悲,红事办作了白事。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头人送黑头人。”说罢喟然长吁,禁不住老泪纵横。
狄公听罢江文璋如此一通言语,不露情色,转口又传万一帆问话。
万一帆跪上前一步向狄公叩了头。——狄公见他约四十上下年纪,面皮自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已出露老之将至之气候。他猛想起昨夜筵席上康氏昆仲正是为他这个牙人的一笔款贷致生争执。今日却看他是如何为刘飞波作证的。
万一帆证言道:“两年前江文璋发妻亡故,没出月便径自来宅下找小人,道是欲娶我女儿三官为续弦。小人一听冒火三丈,天下恁的有如此鲜廉寡耻、老不正经的,竟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哩。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设,小人自然一口回绝。
“江文璋碰了壁后,居然怀恨于心,恶意中伤小人。几次低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读小人名声。故当小人听说刘先生要嫁女江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知了刘先生,劝他三思。”
万一帆语未落音,江文津已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竟青天白日大堂上血口污人。那年老朽发妻弃世心里正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女儿许与犬子。老朽素知他人品卑下,行为苟且。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甚药,当时便婉言谢绝。”
狄公恼怒,万、江两人必有一个是当面扯谎,这近戏弄。为此藐视官衙,一旦问破,定不轻饶。此时暂且含忍,选问王玉珏取证。
王玉珏称,刘飞波所叙大抵属实,故他愿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江文璋垂涎月娥一节,似系猜测,恐无实据,他不敢贸然作证。再者,洞房花烛夜的究竟,一时也判断不清。
孔掌柜则证言江文璋一向循礼守仁,人格端正,操行纯洁,决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系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形迹蹊跷,必不至是劫凶杀人,望老爷迅即查明,替江文璋开脱。
狄公首肯,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须臾华大夫传到。狄公问了当时断诊验尸本末,嘱与衙门仵作质对。又斥其催尸主私殓,于律法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炎夏,故从宽处断,该罚白银十两充公库,严禁后来。
衙门仵作称:“月娥小姐死例实属罕见,然名家医案确有记载。只是昏寐不醒者居多,一旦命象险弱,差近死亡。失血过量,偶有不救者。”
狄公一拍惊堂木:“本县原拟鞫审昨夜花艇谋害舞姬杏花一案,不料有民事诉讼至署,竟也是人命关天官司,且较早一日发事,论理先行断治。——本县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察。”
第六章
退堂后狄公踱步转入内衙,饮了一盅茶。吩咐马荣差遣番役先去石佛寺布置禁戒,他自己则去江文璋宅院看了现场即赴石佛寺开棺验尸。
狄公对洪参军道:“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刘飞波倘若真信万一帆的话,必不肯答允这头亲事。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甚深,腹中似可撑得船去。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得如此凄凄惶惶、累累如丧家之犬。再看江文璋嘴上固然这般诉说,举止神态仍不失泰然。少间我们去江宅时还须留意看觑则个。”
狄公、洪亮分坐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四名番役来到江文璋宅院。
江宅满院喜庆灯彩未撤,随处披红挂绿。但阖府的人个个失魂落魄一般,好似白日的耗子,见了官府来人都依壁躲路而行,不敢高声言语。
江文璋迎狄公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敬茶。狄公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乐图》,写的是孔子率门徒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情景。两边各四个暗红柜厨,并不封锁,内里尽是书帙。心里油然生起一种亲近之感。
(雩:读‘鱼’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华生工作室注)
“江先生昔时讲学庠序,阐发圣道,本是孔门夙儒的正事,如何却要辞了?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似无病疾。”——狄公这时忽的对江文璋发生了兴味。
江文璋叹了口气道:“狄县令有所未知。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到老来方知郑、马传疏很觉可疑。且孔子时本无六经之称,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说始于戴圣,一个异端,一个赃吏,岂可信从?偏偏县学只许规范郑、马,不能半点差池,老朽心中便不乐。一日讲授《春秋》,我道《春秋》本鲁国之史,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作《春秋》,一不可信。《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益不可信。《左氏传》载桓公、隐去被弑,而《春秋》只书‘薨’之一字,灭匿臣之迹,隐二公之冤,如此史笔,差董狐万万,乱臣贼子岂能生俱?——哈哈。
(弑:读‘士’,古代统治阶级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薨:读‘轰’,古代称诸侯之死。后世有封爵的大官之死也称薨。——华生工作室注)
“那一日老朽多喝了几盅,竟吐出如此一通妖论。果然当时县令闻报,将老朽传去重重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忿忿,一气之下便学起着时五柳先生赋归去来。——今日老爷问及,仍以这段旧话作答,真是拗性无改了。狄老爷明经出身,老朽弄斧班门,亦知羞了。如此絮叨,幸乞宥谅。”
狄公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出一身冷汗。方知这江文璋有十二分眼孔胆门,端的是个异才,不可轻觑。遂又问:“江先生如今教课生徒,讲的是哪部书?”
“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书,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南。老朽自己得闲,只读《易》,余皆不看。虽不至韦编三绝,也庶几看破些无人际遇。”
狄公一头听话一头吃茶,不觉两盅吃过,乃依稀记得这茶幽香无比。
“这好茶再乞另烹一壶来吃。”狄公笑道,“今日听江先生说经,十分领佩,这茶也觉有异香。”
小童答应,下去烹茶。
狄公又笑:“江先生岂忘了本县来宅上应是何事?这茶水烹了,临行再吃。此刻我们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江文璋顿悟,又生沮丧。口中应了,遂站起前头引路。
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行过几处房栊,便是一个小小亭阁。亭阁右边有一垂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竿修竹,轻微摇摆。几本花木正开得妖娆。只觉香气馥郁,十分醉人。
江文璋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道:“那片房舍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在二进内院。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庭院。江幼璧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斋,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觉高敞。里间乃是卧房,也即是新婚出事的洞房。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一花藤小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塌。壁上悬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纤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未打开。
江文璋道:“这书斋夏日尤觉凉爽宜人,犬子附会风雅,取了个名儿叫‘绿筠楼’,那上面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馏金匾哩。”
狄公听得“绿筠楼”三字,心中一震,与洪参军交会了一下眼色,遂不动声色看起桌上的书帙和抽屉里的笔札杂物来。江文璋知趣,退过半边,只在门槛上站立。
狄公略一转肠,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筠楼主的一些浅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里的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又是另一个绿筠楼主了。”
江文璋作色道:“绿筠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刻诗,更不会传人杨柳坞那个风月渊薮。——犬子一向立身端正,侃侃直道,不是三瓦两舍上行走的人物,岂会与那里的女子有瓜连。”
(薮:读‘叟’湖泽的通称。——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听了并不介意:“想来又是一个绿筠楼主了。令郎邑勉好学,锐意进取,不知可有得意之笔,正经文章?”
(黾勉:勉力,努力。黾:读‘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