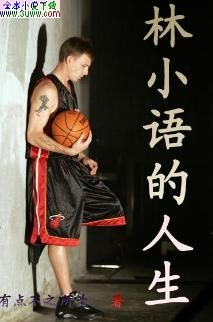相继死去的人-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学过什么外语?
法语和英语。
别忘了黄金人的故事。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大声说,语气中带着懊恼和气愤。
“今天你是怎么了,娜达莉娅?简直不像是你自己,连简单的作业都完成不好。你的病历卡拿来了,你完全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几道题你应当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什么地方不舒服,那就叫娜佳。”
“我的心疼,”姑娘发愁地回答,“马上就到巴甫利克的生日了,可是我却不能祝贺他。”
“蠢话,”米隆断然说,“太孩子气了。你就这一次不能祝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巴甫利克照样过。”
“不,他会过不好的,”她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大概没有小弟弟,所以你不理解。我和奥列奇卡好歹总算在家里过过一段时间的正常生活,可是巴甫利克进医院的时候只有半岁,除了医院的病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什么乐趣可言?伊尔卡一星期来探视两次,带点好吃的,这就是全部乐趣。而他一年过一次生日。一年只有一次,这你能理解吗?因此我们总是尽力给他意外的欣喜,伊尔卡把刚挣到的钱全掏出来给他买礼物,给全病房的小朋友买食品,我写滑稽诗,奥列奇卡朗诵我写的诗,给他画漂亮的明信片。我们集合在一起向他赠送礼物,奥列奇卡读诗。而且他们整个病房都跟他一道兴高采烈共同庆贺。怎么可以剥夺小孩子的这个节日呢?”
“你冲着我大叫大嚷干什么?”米隆突然粗暴地打断她说,“是我剥夺了他的这点乐趣吗?依我说,你要是觉得非祝贺不可,你就祝贺好了,只是这里不是我说了算,这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她稍稍小声说,“请你原谅我的失态。的确不是你的错。只是我的情绪太坏了,我一想到巴甫申卡过生日的时候得不到我的任何东西,心都要碎了。要知道没法跟他解释,他还太小,才只有6岁。他肯定在等着我的祝福,一旦等不到,一定会嚎啕大哭,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好吧,”米隆突然温和地说,“我去对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说说看。也许,他会允许你给弟弟发电报。你先编好诗句,以备万一。”
“谢谢你。”娜塔莎欣喜地回答。
“别谢得太早。暂时还什么都不清楚。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也可能不允许。”
但是瓦西里同意了。而且甚至没有费什么口舌,这让米隆吃惊不小。要么是他确实害怕娜塔莎紧张激动,心绪不佳,不能好好表现自己;要么是他另有打算。反正他轻易地甚至还有几分满意地同意她向小弟弟祝福。“当然,”米隆突然想到,“如果娜塔莎没有忘记弟弟的生日,甚至还跟往常一样给他写了诗,就是说,她的确一切正常,也就没有理由担心了。完全正确,瓦西里应该上这个钩。”
第二天,给娜塔莎拿来了一张空白传真电报纸。她在上面认真地用小字写了一首长诗,在一旁画上一只脖子上扎着大蝴蝶结的滑稽小狗。电报拿走时,她明显地快活起来,而且甚至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次让她写的完全是另一个发报地址。这份电报将不是发自摩尔曼斯克,而是发自奥伦堡。
然而,晚上等着米隆的是一个令人气短的意外。他给娜塔莎上完课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父亲坐在里面。
“你好,阿斯兰别克。”他冷冷地说。
“晚上好,父亲。”米隆小心翼翼地向父亲问好,料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果。
“你看见我好像不高兴。”
“你说什么,父亲,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有点措手不及。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来办事。决定同时看看,我的儿子怎么样履行自己父亲的请求。”
“怎么样?”米隆尽可能冷漠地问,“瓦西里说我的坏话了?”
“是的。这让我极为痛心。”
“我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意了?我听话顺从,执行他所有的要求,甚至遵守他强加给我的一切荒谬的规定。父亲,你把我送进了什么地方啊?是度假期还是服苦役?在这个地方不经允许连路都不能走一步。去镇子上不行,出大门不行,晚上散步不行,在楼里面走一走也不行。除了那个姑娘,不允许同任何人说话。我为什么要受这种惩罚?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要把我送进这座监狱?”
“你让我痛心,儿子。我原本以为瓦西里不完全对,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他并非夸大其辞。你桀骜不驯,执拗任性,你并不把父亲的话当做法律。这不好,这违反了常理。当一个不孝之子是一大罪过,大错而特错。但是更大的罪过,更违反常理的是怜悯女人。你陷进了罪恶的深渊,错上加错。”
“父亲,但是这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姑娘,而且患有不治之症。难道我连向她表示最起码的同情的权力都没有吗?”
“没有,”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绝,“你应该做瓦西里命令你做的事情。你应该为我所效力的事业效力。你不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这就是我的意愿。如果在你有罪孽的心灵中还有所怀疑的话,你记住,你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我的血,而不是这个姑娘的血。对我们而言,她是个异族人。而这意味着,她对于你来说也是外人。你的母亲得知你违背常理不听父亲的话,她会极为伤心。这一点你也应该记住。你是印古什人,是穆斯林,阿斯兰别克。如果我长期装作没有发现你的非穆斯林行为的样子,如果我停止了反对你不用你出生时我给你取的名字,这不等于我容忍或者准备把你投入斯拉夫文明的怀抱。你生为穆斯林,至死还是穆斯林。这也是我的意愿。”
说完这番话,父亲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米隆听见外面传来父亲同瓦西里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他的心里腾起一股突如其来的对瓦西里的仇恨,这个人比米隆所能想象的还要精明得多。真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发现了米隆只是假装无动于衷,实际上怜悯娜塔莎。这个眼力厉害的恶棍、卑鄙的告密者,先给父亲递了小报告。
不过父亲的权力毕竟是非常大的。二十二年来,他是阿斯兰别克——米隆惟一的主宰者。二十二年来,他要求儿子对他言听计从,绝不争辩,并且让儿子相信,儿子对父亲不顺从不尊敬是一大罪过。米隆也相信了他,至今仍然相信,尽管父亲显然干着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瓦西里对他说了那些话,诸如倘若你不听话,即使为了名誉父亲也会第一个打死你。父亲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点连讨论都不用。
这一天躺下睡觉时,米隆感到自己是一个违犯了教规的人,罪大恶极。如果他注定要为了父亲的意志而牺牲,他一定会接受,就像接受命运的恩赐一样,绝不敢反抗,也不会寻求解脱的途径。如果父亲叫他去死,他就应该去死。这再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他应该服从父亲的意志,这就是常理。
米隆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装的还是昨天睡下时装的那些念头。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了娜塔莎。好,他应该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接受死亡,如果这是父亲的意愿的话。父亲有权力自行决定自己儿子的命运,但是谁给他权力决定一位俄罗斯姑娘的死活呢?娜塔莎信任他,米隆,她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等着他拯救她。难道仅仅因为父亲要他意识到自己有错或者有罪,他就丢开她不管不顾吗?好吧,他可以去死,如果必须这样,但是他也得想办法把这姑娘救出去。他无权退缩。父亲认为怜悯一个俄罗斯姑娘、一个非穆斯林、一个异教徒的女儿,这是罪过。好吧,就让他,阿斯兰别克,做一个违反教规的罪人。况且,毕竟他还是一个男人!他有责任保护小孩子,即使是异教徒的孩子也罢。
既然如此,就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问题是莫斯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娜塔莎的电报?奥伦堡距喀尔巴阡山可不近,如果送电报的人从里沃夫坐飞机走,那不会早于明天。还有从这里到里沃夫的一段路程呢。首先得坐汽车到当地的飞机场,接着坐四十分钟的老式“玉米机”,而且到奥伦堡还不是每天都有航班。假定莫斯科收到电报是后天,那么就可以开始逐步实施下一阶段的计划。莫斯科方面收到电报之后,应当过几天,寻找娜塔莎的人才能理清头绪,如果还有人寻找她的话。如果他们能猜透米隆的用意,如果……如果……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
上一页 下一页
17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均非常健康的人。他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对令人不快和忧心忡忡的心情有特别强的排除能力。他善于不去想他不喜欢或是不愿意的事情,他也善于让自己不去牵挂他不想操心的事情。二十年坚持不懈地拿女人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做实验,他竟然能够做到从来不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极不道德和伤天害理而心虚胆怯。他有自己的目标,也只有这个目标令他心驰神往。他永远不能忘怀,当他提出的理论受到嘲笑讥讽,被一起共事的同行们斥为没有前途、违反科学而予以否决时,他所体验到的刻骨铭心的怨愤。沃洛霍夫想向自己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这一点今后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知道,这对他就足够了。二十年来他的头脑中连想都没有想过,一旦他的理论被证实,会带来滚滚财源。他的钱够多的了,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杰出的诊断医师和放射性应用治疗血液病的学术带头人,这使他名利双收。通过自己不合法的科学实验牟取暴利,他根本没有想过,这在他而言,是纯粹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思想。
5月中旬碰到阿尼斯科维茨老太婆,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不愉快。更令人不快的是,这次相遇照她所说并非偶然邂逅。原来,老太婆跟踪他好几个月了。这一次她有意相遇,是要给他上一堂道德课。他平静地对待同叶卡捷琳娜的那次谈话,他并不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认为,阿尼斯科维茨不会再打扰他,不会再在路上截住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太婆不过是要吓唬他一下,教训几句,然后就忘了,依旧忙她的事情。但是,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见面之后不久,沃洛霍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听说了您的实验。我们对实验很感兴趣。考虑一下您的条件,开个价。我们还会给您打电话的。”
沃洛霍夫当即大惊失色,因为事出意外而六神无主,甚至连答话都顾不上了。而打电话的那个人不待他回答,自顾说完就放下了话筒。他一再回想这个电话,力图事先想好几句话,以备他再来电话时好妥为应对。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我没有进行任何实验……”
随即他就明白,这些话都不合适。他们既然打电话,就是说他们知道底细。不承认有什么用?
“我的科学实验尚无结果……”
“我不需要你们的钱……”
“我不拿科学做交易……”
所有这些话在他看来都显得笨拙无力而且不得体,没有说服力,透着做作的小家子气。他明白,他们会以张扬相威胁,不过他对此倒不是特别害怕。他就以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相回敬。女人?不错,有过。那有什么,难道犯禁?孩子?不错,他的女人们生有孩子。难道这是犯罪?在孕妇身上做实验?你们说什么?我是个诊断医生,我运用放射学方法检查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这些方法取得了专利权,是得到承认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哪位妇女需要用我的专长进行治疗,我就给予她治疗,还能怎么样。对了,我曾经用研究所的化验室为自己的情人们做过检查。这不对。你们处罚好了。但是,一不偷,二不砸,并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经常生病?有什么办法。第一,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生态环境极差;第二,这与我本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唉,身体留下很多良好的愿望,可是暂时没有人能够废止遗传规律。毕竟这都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
总而言之,他不怕揭发。归根结底,没有谁能指认出他所有的女人和孩子。仅仅除了一个声称对他跟踪盯梢列出了名单的叶卡捷琳娜。平心而论,根据她说的数字,她列出的名单确实齐全。但是叶卡捷琳娜死了,死得恰逢其时。然而沃洛霍夫博士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方法交到别人的手里。他全都了然于胸,什么人为了什么需要这种方法。现在,实验臻于完善,只需等着卓娅和薇拉的孩子出生了。他相信他就要大功告成了。他学会了挑选智力优越、身体耐力与韧性超群,同时又绝对顺从听指挥的人做实验。理想的执行者在居心叵测的人手中,既可能成为超可靠的警卫和不屈不挠、不知失败的士兵,也可能变成狡猾的罪犯和雇佣杀手。
沃洛霍夫不想把自己的方法教给任何人,因为他清楚地看见了其大规模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当陌生人终于第二次打来电话时,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也不打算向你们出卖什么。”
“好吧,”电话那头说,“您是舍不得。我们自己来向您讨教您的方法。”
这次通话之后的几天中,沃洛霍夫坐立不安,提心吊胆,等着随时有人来抓他捆他,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刑讯拷问;或者到他家破门而入,偷走所有的笔记;或者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暴行等等。
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既没有攻击他,也没有偷他的文件。于是他渐渐平静下来,终于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情了,就像同阿尼斯科维茨谈话时他对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见我不怕他们,也就缩回去了。”这样一想,人也轻松舒服了许多。沃洛霍夫博士排除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