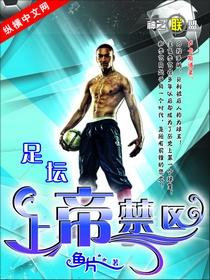上帝之灯-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威廉斯先生。”汉克连忙说道,歉然地鞠个躬后就匆匆离去。他的情人则哭着跑向牧场房舍去。
奎因先生和芭莉小姐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奎因先生说道:“我有了一个构想,不过不是很好。”
“可怜的孩子,”宝拉叹道,“好吧,去找惠特尼·威廉斯谈一谈,看会不会激发什么灵感。”
接下来的几天里,奎因先生漫步在史考特的牧场中,与他谈话的包括骑师威廉斯,戴眼镜的郝勒迪先生——他发现他也对赛马一无所知且更不关心,总是泪眼盈盈的凯萨琳,名叫比尔的警卫——他睡在马房里“危险”的旁边且一只手还搁在猎枪上——以及老约翰本人。他学到了许多关于骑术、刺探情报、比赛程序、马具、障碍赛、奖金、罚金、向导、下注的方式、著名的比赛、马匹、马主及比赛跑道的知识,但是灵感还是拒绝出现。
所以到星期五傍晚的时候,他发现不知怎地史考特牧场里没人理他了,他就开车到好莱坞去。
他发现宝拉在她的花园里安抚两个苦恼的年轻人。凯萨琳·史考特还在哭,那个自称为懦夫的郝勒迪先生头一遭穿了没有异味的衣服,正笨拙地抚弄着她的金发。
“更多的悲剧!”奎因先生说道,“我应该知道的。我刚刚才由你父亲的牧场过来,那里乏味得很。”
“哼,活该!”凯萨琳叫道,“我叫我父亲滚蛋。那样对待汉克!只要我活着我都不会再跟他说话!他——他不正常!”
“等一下,凯萨琳,”郝勒迪先生责备似地说,“不可以那样说自己的父亲。”
“汉克·郝勒迪,如果你还有一丁点儿的男子气概——”
郝勒迪先生挺直身子,好似他的情人刚刚用电线电了他一下。
“我不是有意的,汉克,”凯萨琳哭着扑到他的怀里去,“我知道你禁不住会胆怯,可是他打倒你的时候你甚至没有——”
郝勒迪先生若有所思地摸着他的左颊:“你知道,奎因先生,当史考特先生打我时某种感觉发生在我身上。在那一瞬间我有一个奇怪的——呃——渴望。我真的相信如果我有一把手枪——而且我知道如何使用的话——我当时很可能会犯下谋杀罪。我看到——我相信是这样说的——血光。”
“汉克!”凯萨琳恐惧地喊道。
汉克叹口气,杀戮的眼神从他的蓝眼睛中褪去。
“老约翰,”宝拉凝望着埃勒里解释道,“发现他们俩又在马房中拥抱,我猜想他是认为如此会给‘危险’一个坏榜样,因为它的思绪应该在明天的比赛上,所以他开除了汉克。凯萨琳气炸了,叫约翰滚蛋,然后她就永远地离开家了。”
“开除我是他的特权,”郝勒迪先生冷静地说,“不过现在我不亏欠他任何忠诚,我不会赌‘危险’在障碍赛中获胜!”
“我希望那只畜牲输。”凯萨琳哭着说。
“好了凯萨琳,”宝拉坚定地说,“我听够了这些胡言乱语。现在我得好好跟你说说。”
凯萨琳还在哭。
“郝勒迪先生,”奎因先生正言道,“我相信这是暗示我们可以去小酌一番。”
“凯萨琳!”
“汉克!”
奎因先生和芭莉小姐把这对恋人拆散。
十点过了没多久,史考特小姐由芭莉小姐的白色小屋出来,钻进她的车里,她已经停止哭泣了,但依然满脸泪痕。
当她把钥匙插进点火位置并脚踏起动器时,由后座的阴影中传来一阵沙哑低沉的声音:“不要叫。不要出声。开车直到我叫你停为止。”
“啊!”史考特小姐叫道。
一个巨掌蒙上她颤抖的嘴巴。
过了一会儿车子开走了。
第二天奎因先生来找芭莉小姐,他们慢慢地朝东边的山谷走去,附近就是优美的圣塔安妮塔赛马场。
“昨天晚上悲伤的凯萨琳怎么了?”奎因先生问道。
“喔,我要她回牧场了。她是十点多一点走的,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女孩。你跟汉克说了什么?”
“我把他彻底洗脑后就带他回家。他在好莱坞住宿之家租了一个房间,他一路上都靠在我的肩膀上哭泣。似乎老约翰还踢了他的屁股,他因此萌生杀意。”
“可怜的汉克,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老实的男人。”
“我也怕马。”奎因先生连忙说道。
“喔,你呀!你可恶,你今天一次都还没吻过我。”
沿着第六十六号公路,只有芭莉小姐清凉的双唇才能令奎因先生免于发火。这条路的车速缓慢,在小路上更糟,仿佛南加州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圣塔安妮塔来,利用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从农夫的污秽T型车到电影明星的现代汽车。看台上挤满了嘈杂的人群,像一幅蠕动的彩色马赛克。天空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微风轻轻吹,跑道上是急速的跑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在晴朗的天空下,这些闪着亮光的动物,显得小巧、快速,而且线条清晰分明。
“真是障碍赛的好天气!”宝拉叹道,抓着埃勒里一起走,“喔,那是宾恩,还有艾尔·琼森,还有鲍伯·柏恩斯!……哈罗!……还有琼和克拉克,还有卡萝……”
不管芭莉小姐的过度兴奋,奎因先生终于全身安抵马房。他们看到约翰·史考特心无二用地看着一个马房助手帮“危险”按摩柔软的前腿。史考特的面无表情使得宝拉不禁叫道:“约翰,‘危险’有问题吗?”
“‘危险’没事,”老人简短地说,“是凯萨琳。我们昨天为了郝勒迪那小子吵了一架,她跑掉了。”
“胡说,约翰,我昨晚亲自把她送回家的。”
“她在你那里?她没有回家。”
“她没有?”宝拉的小鼻子皱起来。
“我猜想,”史考特怒道,“她是跟郝勒迪那懦夫跑掉了。他不是男人,胆小的——”
“我们不能都做英雄,约翰。他是个好孩子,而且他爱凯萨琳。”
老人固执地看着他的种马,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开,朝向他们的包厢而去。
“真奇怪,”宝拉用害怕的声音说道,“她不可能跟汉克跑掉,汉克跟你在一起,而且我发誓她昨晚说要回牧场去。”
“别急,宝拉,”奎因先生温柔地说,“她没事的。”不过他的眼神若有所思而且有一点不安。
他们的包厢离马房不远。在初赛过程中,宝拉不停地用她的望远镜在人海中搜寻。
“噢,噢,”奎因先生突然开口,宝拉这才感到周围发出如雷般的响声。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扫帚棍子’,最爱欢迎的马,被删掉了。”奎因先生冷冷地说。
“‘扫帚棍子’?山迪尼的马?”宝拉瞪着他,脸色苍白,“但为什么呢?埃勒里,这里面有些——”
“好像是它抽了筋所以不能跑。”
“你认为,”宝拉低语,“山迪尼是否涉及凯萨琳的……没……回家?”
“有可能,”埃勒里说道,“不过我不能适应闪光的东西——”
“它们出来了!”
叫喊声动摇了看台,一列气派的动物从马房中出来。宝拉和埃勒里随着焦躁不安的群众站起来,引颈张望。障碍赛的参赛者列队走到标杆处!
来的是“高岗”,它在两年前的马术比赛中,最后冲刺时成了跛脚,之后就没有参加过比赛。这将是它的复出之战;消息灵通人士对它颇为轻蔑,公众似乎也都同意,因此它的赌注是五十比一。还有“战斗比利”,还有“赤道”,还有“危险”,黑得发亮、高大、气派。“危险”很紧张,惠特尼·威廉斯控制它有一点儿困难,马房助手也使劲拉它的马缰。
老约翰·史考特,他的庞大身躯即使由这个距离看去也不会认错,他从马房出来走向他跳动的种马,显然是要安抚它。
宝拉喘着气。埃勒里迅速问道:“怎么回事?”
“汉克·郝勒迪在人群中。那里,就在‘危险’正要通过的那一点上方。距约翰·史考特大约五十英尺远。凯萨琳没跟他在一起。”
埃勒里把她的望远镜拿过来找到了郝勒迪。
宝拉坐进椅子里:“埃勒里,我有一股好怪的感觉,有些事不对劲,看他多苍白……”
高倍数的望远镜把郝勒迪拉到埃勒里的眼前几英寸之处。那男孩的眼镜都蒙上了蒸汽,他在发抖,仿佛他在发冷,然而埃勒里却可以看见他的脸颊上的汗珠。
接着奎因先生陡然挺直身体。
约翰·史考特刚走到“危险”的马头旁边,他粗壮的手臂正要把种马的头拉下来。在那一瞬间,汉克·郝勒迪在他的衣服里摸索,下一刻他的手里就握了一把枪。奎因先生几乎叫出来,因为虽然枪管抖动,但郝勒迪先生颤抖的双手拿着的手枪所指方向很清楚是直指着约翰·史考特,接着一声爆响,一团烟雾由枪口冒出来。
芭莉小姐跳起来,而且芭莉小姐真的叫出声来了。
“啊,这个疯狂的年轻蠢蛋!”奎因先生茫然地说。
受到枪声的惊吓,“危险”往后退。其他的马开始起舞。一转眼间下面都是受惊的纯种马。史考特抓着“危险”的头,质疑地往上看。惠特尼用尽全力来控制发狂的种马。
然后郝勒迪先生又射了一枪。再一枪。第四枪。在枪声的间隔之间,马已经退到约翰·史考特和郝勒迪先生所拿的手枪之间。
“喔,老天,喔,老天,”宝拉咬着手帕说道。
“我们走!”奎因先生喊叫,然后他就朝向那里冲过去了。
当他们到达郝勒迪先生发射的地方时,这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在他周围的人群还吓得不敢动。在看台的其他地方则有如地狱。
在混乱中,警察在倒地的“危险”和其他乱闯的马匹间匆匆拉起警戒线,埃勒里和宝拉设法溜过去。他们看到约翰跪在那匹黑色的种马身旁,他的大手缓缓地抚摸着它光滑的脖子。惠特尼看起来苍白又迷惑,卸下了小小的马鞍,赛场的兽医正在检视“危险”身侧接近肩膀的弹伤。一群赛场职员在一旁热烈地讨论。
“它救了我的命,”老约翰自己低声地说着,“它救了我的命。”
兽医抬起头:“很抱歉,史考特先生,”他冷酷地说,“这场比赛‘危险’不能跑了。”
“是。我想是不能。”史考特舔一舔嘴唇,“它——它严重吗?”
“要等我把子弹挖出来才知道,我们必须立刻把它送医院去。”
一位赛场职员说道:“运气太差了,史考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找出开枪射你的马的无赖。”
老人的嘴唇扭曲。他站起来看着种马的侧肌。惠特尼·威廉斯带着“危险”的马具,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播音系统报告,编号五号的“危险”删除了,一等其他参赛的马恢复平静,在起点排好之后,障碍赛就会立刻开始。
“好了,各位,让开让开,”医院的车子以及尾随在后的起重卡车赶来时,一个赛场警察说道。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射击这匹马的人?”埃勒里问道,纹丝不动。
“埃勒里。”宝拉紧张地低语,用力拉他的手臂。
“我们会逮到他,我们有很清楚的描述。走开吧,麻烦你。”
“呃,”奎因先生慢慢地说,“我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吗。”
“埃勒里!”
“我看到他而且认识他。”
他们被带到经理的办公室,这时正好宣布“高岗”赢了圣塔安妮塔障碍赛,获得十万元奖金,它以两个半马身的差距获胜……可以说,几乎像击倒“危险”的射程一样长。
“郝勒迪?”约翰·史考特以强烈轻蔑的语气说道,“那个没种的年轻人想要射我?”
“我不会弄错的,史考特先生。”埃勒里说道。
“我也看见了,约翰。”宝拉叹道。
“这位郝勒迪是谁?”赛场的警察主管问道。
史考特简单地告诉他,也提到前一天的争执:“我打倒他而且踢了他,我认为他能够来找我的唯一方法是带把枪。而‘危险’替我承受了报复,可怜的小东西。”第一次他的声音颤抖了。
“呃,我们一定会逮到他,他不可能逃掉,”警察冷冷地说,“我会把这里封得比鼓还要严实。”
“你知道吗,”奎因先生说道,“史考特先生的女儿凯萨琳从昨晚就失去了踪迹?”
老约翰的脸慢慢涨红:“你认为——我的凯萨琳涉及——”
“别傻了,约翰!”宝拉说道。
“不管怎样,”奎因先生冷冷地说,“她的失踪与今天此地的攻击事件不会是巧合。我建议你立刻去找寻史考特小姐,而且顺便把‘危险’的马具拿来,我要检查。”
“嘿,你到底是谁?”警察咆哮着问道。
奎因先生一脸不在意地告诉了他。那个警察看起来有点敬畏。他打了几个电话到警察总局去,然后派人去拿“危险”的马具。
惠特尼·威廉斯,还穿着制服,把小小的赛马马鞍拿进来,丢在地上。
“约翰,我对发生的事感到万分抱歉。”他低声说着。
“那不是你的错,惠特尼。”宽阔的肩膀垂下来了。
“啊,威廉斯,谢谢你,”奎因先生轻快地问,“这就是‘危险’几分钟前配挂的马鞍吗?”
“是的。”
“就是枪击之后你卸下的那一副吗?”
“是的。”
“有没有人有机会接触它?”
“没有,我一直带着它,除了我没有别人接近它。”
奎因先生点点头,跪下来检查空无一物的鞍袋。看过了翼片上的焦黑弹孔后,他的眉毛因困惑而皱起来了。
“还有,惠特尼,”他问道,“你多重?”
“一百零七磅。”
奎因先生再度皱眉。他站起来,召唤警察主管,他俩低声交谈,那警察的表情有点狐疑,他耸耸肩,快步地走了出去。
当他回来时,一位穿着极讲究且有些面熟的男士陪着他。那位男士看起来有点悲伤。
“我听说有个疯子对你开了好几枪,约翰,”他遗憾地说,“但却击中你的马。运气可真背。”
在这个暧昧的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