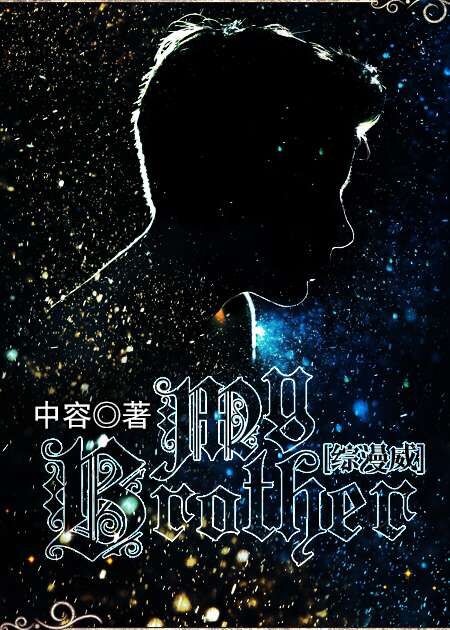断笛 上 by 朱雀恨-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远远地,传来一声悠悠笛音,那笛音是如此的清越,轻易便盖过了风声。苏锦生的心随之荡漾,只觉魂魄都飞到了天边。
他撩起袍摆,沿著小道一路下山,到了半山腰间,小道拐了个弯,扎进林木深处,跑到底,视线霍然开朗,一片池塘展现面前。月光照著池畔的芦苇,银白的芦花缎子般闪亮,就在那芦花丛中立了个男子,背对著苏锦生,正横笛而立。
苏锦生放慢了步子,一寸一寸挪到那人身後,心底的某处,有什麽蠢动著,酸涩、甜蜜而又痛楚,他迟疑著,然而终於伸出手来,抱住了那人。脸颊贴到那坚实的背脊,心便安稳下来。苏锦生闭紧了眼睛,只觉得自己命悬一线,而这个人就是他救命的稻草,他一切的一切,都交在了这个人身上。
“来了?”那个人问。
“嗯。”
“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我说的那些话,吓到你了。”那人转过身,捧住苏锦生的脸庞,温热的手指在他脸颊上轻轻摩挲:“冲……”
听到那人这样叫自己,苏锦生心里微微一震,这麽说,他还真猜对了,在梦中他变成了司马冲──晋元帝的第三个儿子,那麽,自己的这个“哥哥”又是谁呢?
“知道吗?”那人叹息似地喃喃低语:“我真怕你不来,真怕从今往後,你再不认我了。”
借著幽微的月光,苏锦生看清了他的眉目,那并不是一张汉人的脸孔,这人皮肤极白,鼻梁笔挺,眼窝深陷,头发、眉毛都是浅褐色的,一双眸子却黑得仿佛化不开来。这个人居然跟Simon长得一摸一样。
可苏锦生知道,他不是Simon,《晋书》上说过,司马冲同父异母的哥哥司马绍有著一半的胡人血统,长得身量高挑、褐发白肤,不用说,眼前这个男子就是司马绍了。他和司马冲是血亲兄弟。但他那些话,是一个哥哥会对弟弟讲的吗?
“冲。”
苏锦生还没回过神,司马绍突然拥紧了他,一只手托住他的後脑,低头含住了他的嘴唇。苏锦生本能地挣扎,然而司马绍不容许拒绝,他捏开苏锦生的下颌,坚决地探进舌去,从齿列到上颚,一寸不放地撩拨。苏锦生被他吻得膝盖都软了,合不拢的口中泻出低低的呜咽,司马绍顺势卷住他的舌,轻吮慢吸,直到那舌头屈服、回应,跟他的纠缠在一起。
苏锦生的心怦怦乱跳,几乎撞破了胸腔。对於性,他从小就心怀恐惧,因为那可怕的梦,他把性跟屈辱、死亡联系在了一起。这麽多年,他没有谈过恋爱,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敬而远之。可是,在这逼真得吓人的梦里,他第一次尝到了接吻的味道。不仅仅是吻,还是逆伦的吻,哥哥与弟弟,这样唇舌交缠、彼此贪恋,明明是那样扭曲,那样肮脏的关系,可是感觉一点也不坏,反而充满了危险的愉悦感。
为什麽会这样?这是属於司马冲的感觉?还是说,因为Simon说过,不管发生什麽,都不是真的,因为这是一个无须负责的梦,这是他人的过去,所以自己才会这样无所顾忌吗?
苏锦生无法思考,嘴唇被狠狠地碾压著著,濡湿的舌头纠缠不休,苏锦生撑不住,向後倒去,司马绍干脆把他打横抱了起来,一边吻著,一边朝林间走去。
前方有融融的灯光,临池筑著一带竹轩,司马绍把苏锦生抱进了去,放到榻上,珠纱罗帐低低垂落,笼出一片旖旎之色。床边铜灯未熄,空气里有暗暗的甜香,似龙涎、如麝香,再熟悉不过,多年来这味道一直在苏锦生的梦里萦绕。
“冲,我的冲……”司马绍拥著苏锦生,灼热的气息吹在他耳後,暖暖的,说不出的麻痒。苏锦生的心跳得更快了。恍惚间,只听一声布帛撕裂的声响,轻软的袍子滑落下去,与此同时,司马绍的手也按上他光裸的胸膛。
“你什麽都不用管……”司马绍的声音急迫而又沙哑,他一手将苏锦生按在锦被之中,一手取过条绢带,敷住了苏锦生的眼睛:“交给我好了。”
身子被转翻过来,苏锦生听到司马绍倒抽了一口冷气:“冲,你真好。”
灼热的手指落在苏锦生身上,沿著腰线缓缓游走,这抚摸是这样焦灼,又是那样克制,仿佛沙漠中的旅人面对著仅有的一滩清水,渴得要命,偏又舍不得喝,然而欲望终於冲破自制,雨点般的吻落了下来。
小小的乳珠被咬住了,齿与舌捻弄、诱惑。伴著细微的疼痛,酥麻的感觉也在胸中流窜奔涌,苏锦生不禁低呼出声,他伸出手,求救似地抱住了司马绍的脑袋,司马绍的头发披散下来,丝丝缕缕,萦绕在他指间。
腿被打开的时候,苏锦生瑟缩了一下,司马绍按住他,俯过身,突然将他的性器纳入了口中。
4
苏锦生不由呆在那里,答案已是昭然若揭。Simon说对了,哪有什麽断笛托梦,所有的梦都是记忆的重组,只是这一次,这段记忆属於前生。一千七百年前,他就是司马冲,此刻他正在重温自己的过去。
“冲。”司马绍从身後拥住了他,一手搭到他手上,抚著那玉笛:“你没来的时候,我跟自己说,今夜你要是不来,我就把它扔进西池里。”司马绍说著笑了笑,捉起他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你的名字,我会刻在这里。然後,一辈子都不看。”
“这算什麽?记住还是忘掉?”
“几时你忘了我,几时我忘了你。可是,你忘得掉我吗?”
“怎麽可能,生下来,我就认识你了。”苏锦生看著铜镜中的司马绍:“再说,就算我忘了,你也会来找我的,对吗?就算过了一千七百年,也是一样。”
正说著话,门外响起一声低低的咳嗽,接著,便是个尖细的声音:“世子,王爷宣您觐见。”
“德容?”司马绍拉过被褥帮苏锦生盖好了,自己披衣起身:“出什麽事了?大半夜的宣我?”
德容咳了一下,再没了声响。
“进来说话!”
随著司马绍的厉喝,一个瘦削的内侍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低著个头,看似敛眉顺目的,眼角的余光却往苏锦生身上直溜,神情间颇有难色:“事关紧要,老奴……”
司马绍朗声一笑:“有什麽话是冲不听的?”说著隔著被子把苏锦生揽到怀中:“说吧。”
苏锦生脸上发烫,恨不能缩进被子里去。却听德容重重地叹了口气:“长安来信,今上已经殉国。”
这话说出来,屋里顿时一片死寂,苏锦生只觉得司马绍揽著自己的胳膊紧了紧,随即便松了开去。
因为断笛的缘故,苏锦生对两晋的历史格外留意,尤其是司马冲生活的那个年代,更是倒背如流。当时晋朝国力衰微,胡人作乱,刮分中原,晋朝的版图一缩再缩,名门望族纷纷逃到江南避祸,只留一个可怜巴巴的晋湣帝守著都城长安。公元317年年末,匈奴攻破了长安,十七岁的小皇帝被俘,次年早春就被害死。不用说,德容说的就是这件事了。
湣帝一死,晋朝的帝位便空了出来,而这个宝座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便是司马绍和司马冲的父亲,琅琊王司马睿了。这司马睿十年前便从长安来到了江南,坐镇建康,虽然天下人都知道,早晚晋室的王权会传到他手里,但司马睿为人谨慎,虽然有六个儿子,却迟迟没有立下王储。现在,他突然宣长子司马绍觐见,不但是要商讨继位大事,只怕也跟立太子有关。
果然,司马绍问:“爹爹只宣了我?”
德容把头一低:“还有二世子。”
司马绍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德容走近床边,服侍他穿好衣裳。司马绍回过身来,对苏锦生道:“我先走了。你好好歇著,爹爹那边的事一完,我就回来。”说著在他光裸的肩头盖了个吻,转身去了。
苏锦生伏在枕上,听著司马绍和德容的脚步声渐渐远了,他刚刚经过一场云雨,身上倦乏,可是脑袋里乱哄哄的,一时之间倒也睡不著。他记得《晋书》上说过,司马睿的六个儿子里,最有希望当上太子的是长子司马绍、次子司马裒。其实,无论从长幼之序,还是从天资来论,司马绍都远比司马裒出色,但他身上的胡人血统太过明显,隆鼻褐发,怎麽看都不像司马家的人,司马睿总觉得若将大位传给了他,这晋室的天下便好像落入了胡人手中。
眼下,司马睿将长子、次子同时召去,可见这太子的人选还是悬而未决。
想到这里,苏锦生不由为司马绍担心起来,他竭力回忆《晋书》,想知道太子之位最终到底传给了谁,哪知脑海里头竟是一片空白,所有318年之後的事情竟似被一笔抹去了,一点都记不得了。
“是我太累了吗?睡一觉就记得了吧。”苏锦生这样想著,把头埋进了锦被,枕褥间还留著司马绍的气息,想到之前那疯狂的缠绵,苏锦生的耳根又热了起来,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梦,就算这一切曾经发生过,也早就成为了历史,可是心跳的感觉是如此真实。苏锦生掂起枕上的一根褐发,用手指绕起,犹豫了一会儿,终於贴到了唇上。
司马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次日中午。苏锦生还没睁开迷蒙的睡眼,便被吻住了,司马绍把手伸进被褥,摸索著他的身子:“还不起来?干脆别起来了。”
苏锦生乍然醒来,不适应这样的亲昵,边推边躲,然而他生来怕痒,司马绍又专挑他腋窝、腰间下手,苏锦生被他弄得又笑又喘,两人很快滚作了一堆,呼吸越来越急切,脸颊也飞红起来。
眼看真就下不了床了,苏锦生的肚子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司马绍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饿啦?”他伸出手,捏了捏苏锦生的脸颊:“走,吃东西去。”说著,便从榻边取来苏锦生的衣物,一件一件帮苏锦生套上。苏锦生昨夜眼见著德容服侍司马绍穿衣的,知道他这样的人,平日里只怕连衣带都不是自己系的,更别说伺候别人了,连忙按住他的手道:“我自己来吧。”
司马绍却就势把他抱到怀里,贴著他耳畔道:“什麽你啊、我啊,冲,你是我的。”他轻舔他的耳垂,仿佛要把苏锦生整个儿吞下去:“从今往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苏锦生被他弄得膝盖都软了,也就由他作为。好在司马绍顾念他饿著,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仔仔细细帮他理好了衣服,又把他抱到几案前,就著铜镜帮他绾起了头发。
苏锦生起先并不习惯这麽被人抱著,受人照顾,然而司马绍做起这一切是那样的坦然,尤其是抱他的时候,自自然然地把他搁在自己腿上,那一份亲昵并不仅仅是情人间的贪恋,更是血亲才有的密切。苏锦生望著铜镜中的司马绍,不禁去猜测著他的年龄,他该有二十岁了吧,比自己大了四、五岁,也许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这样抱著自己了,他是自己的哥哥啊。
“呃”,好容易帮苏锦生绾成发髻,却还是有几缕散发落在外头,司马绍无奈地皱起了眉:“看来,还是得找德容。”
“这样就好,”苏锦生笑著站起来,“我才不要德容。”
司马绍闻言也笑了,牵著他的手出了竹轩。轩外的垂杨下系著匹高头骏马。司马绍解开缰绳,扶著苏锦生上了马,依旧将他揽在身前,绕过一池春水,缓缓地朝山下行去。
苏锦生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虽然眼前是一千七百年前的南京,城池格局都大不一样,连城名都不是南京,而叫做建康,但是山川、湖泊却没有大改。苏锦生认得出来,眼前这山是覆舟山,这一池春波,便是有名的西池。《世说新语》里有记载,这池塘,连同池边的竹轩都是司马绍用一夜的功夫,派门客疏浚、修建而成的,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来说,堪称一桩奇迹。
苏锦生按捺不住好奇,便问司马绍:“你干嘛一夜之间修起这西池,慢慢来不好吗?”
“不好。”司马绍沈默片刻:“你真不知道我为什麽一夜起西池?”
苏锦生被他那麽一问,心里没来由地一荡,却听司马绍低低地道:“那年是你十二岁生日,我送了你一双翠璧,你却说:得连城璧,不如得神仙池。那一夜,我便起了这池台。我只当你是懂的,”他收紧了环在他胸前的手,“原来你不懂吗?”
苏锦生脸上发烧,一时间说不出话,只是倚在他怀里。司马绍低下头来,轻吻他的发鬓:“冲,我等了你那麽久。”
5
骏马下了山路,沿著条通衢大道向城中行去。苏锦生见街面上行人越来越多,不好意思跟司马绍过分亲密,便坐直了身子,不再靠在他怀中,司马绍也不强求,只是双手绕在他胸前扣著缰绳,虚虚地抱著他。
因为是走在闹市,司马绍把马速放得极缓,一路便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笑著一一回应。苏锦生发现这些人里不仅有乡绅士子,更有贩夫走卒,不由大为惊讶。司马绍怎麽说也是琅琊王世子、皇室贵胄,两晋时期门第观念是极重的,世家子弟个个眼高於顶,乡下人走过身边,都要沐浴更衣,以扫俗气,司马绍这个样子,苏锦生要不是亲眼看到,真是想都不敢想。
他正惊愕不已,却见司马绍在一所普通的民宅跟前勒住了马,翻身下来,抬起鞭梢轻叩门扉,不多时,那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中年妇人迎了出来,见了二人,微笑起来:“绍儿,你们来了?”
苏锦生见这妇人虽是布衣荆钗,却风姿绰然,肤如积雪、高鼻褐发,顿时明白过来,眼前这妇人只怕就是司马绍的生母,胡女荀氏了。
《晋书》说过,这荀氏出生卑微,又不容於司马睿的原配庾氏,生下孩子後不久就被司马睿遣出了王府,她的两个儿子司马绍、司马裒则被交给其他嫔妃抚养。野史上说,司马裒再没跟亲娘往来过,司马绍却常常去看生母,如此看来,竟是真的了。
想到这里,苏锦生连忙下了马,想要招呼,却不知叫她什麽好,只得腼腆一笑。
司马绍却大方得多,叫了一声“娘”,牵著司马冲的手往里就走:“我们饿了,快烙冲最爱吃的香饼。”
荀氏闻言便笑:“好、好、好,我就知道,你不是来看娘的,只是冲著香饼才肯回来。”
仿佛为了印证她的话,苏锦生的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三人都是一怔,随即相视大笑。
荀氏的香饼果然名不虚传,配饼的肉汤更是浓稠美味,苏锦生真的饿了,又是头一次尝到这种异族美食,几乎放不下碗,吃得满头热汗。荀氏笑微微望著他:“慢慢来。”说著掏出块罗帕,要递给他。
“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