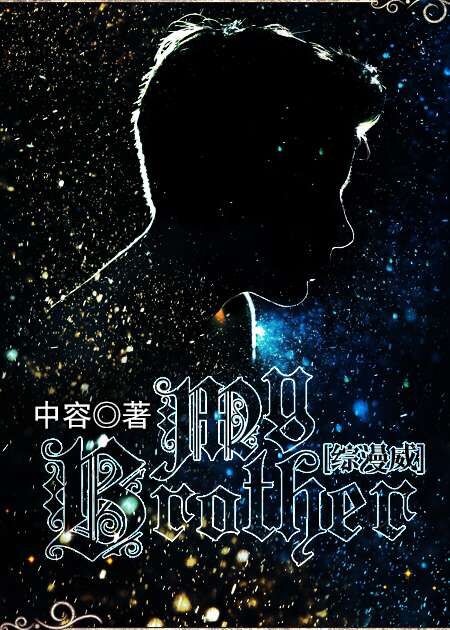断笛 上 by 朱雀恨-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冲!”
“如果没了你,我活著做什麽?这两年里,我一天天看著自己烂掉,我以为自己烂光了,你也不会看我一眼,我已经死心了,可你又回来了。你知不知道,只有你摸著我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的,我跟别人做,身子再快活,这里……”他拉过司马冲的手,贴到胸口:“这里是死的……不会跳……真的,我很久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了……现在我好容易活过来,你又要丢开我吗?我不走,我宁可跟你死在一道!”
“冲,你怎麽总是不记得,你姓司马!”
这话说出来,司马冲便是一怔,他盯著哥哥的眼睛,慢慢地松开了手:“你来找我……你送我出城……只因为我姓司马?”
“你知道不是的。”司马绍攥住他的手腕,“这两年,你以为我好过吗?你以为我就不想来找你吗?可我不能,如果见了你,我一定放不下的。可我毕竟是太子,不能那麽任性。”
“冲,不单单是我,你也不能任性。万一我和爹有什麽不测,匡扶晋室的担子,就要由你来扛了。你是爹亲生的孩子,又有东海世子的头衔,毗陵封地广袤,假以时日,休养生息,未必扳不倒王敦。”
“扳倒了王敦又如何?”
25
“扳倒了王敦又如何?”司马冲抓著他两只手,眼泪直滴到他手背上:“如果只剩我一个人,那有什麽意义?你怎麽总不明白,我要的……我要的不过是……”
“我明白……”
“不,你不明白。”司马冲摇头,他紧咬著嘴唇,仿佛下了莫大的决心:“绍,有件事你一直不知道,其实我很早、很早就喜欢你了,你总当我是小孩子,才会那麽粘你,其实不是的,我是有心的,所以我才会对你说‘得连城璧,不如得神仙池’。後来,听说你为我起了西池,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那晚我在佛前许愿,若能得你垂青,就是永坠阿鼻地狱也甘心,老天要怎麽罚我都可以……你一定想不到吧,十二岁的弟弟是那样的……”
“可是,我想不到天会这样罚我,我想不到二哥会死,会出那麽多事,王敦会打进建康。我以为它只会罚我一个人的,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假如让我重新选过,我绝不敢那麽贪心。”
“绍,其实……你不跟我在一起也可以的,你要娶别人也可以,甚至……你不喜欢我了都可以,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我希望能常常见到你,像哥哥、弟弟那样就好了,你能看著我的眼睛,跟我说话,你能对我笑……你也好、爹也好,弟弟们也好,都能平平安安的……那样的话,就好了……”
他越说声音越低,整个人也朝前俯去,恨不能把自己没入尘埃。
“傻孩子。”司马绍叹息著揽住他,埋下头吻他的头发:“冲,你会那麽吃药,那麽不爱惜身体,不仅仅是在气我,也是在惩罚自己吧?你以为那样,老天就可以放过我,放过其他人了?”
“我不知道……”
“冲,你听我说。即使我跟你什麽都没发生过,二弟还是会死,王敦也还是要兵临城下,那跟你没有关系,要怪只能怪我们生在了帝王家。既然姓了司马,受百官朝拜、万民供奉,就不能仅仅为自己活著。”
说著,他轻轻梳理弟弟的头发:“你看,眼下建康的城防虽然溃散,但京畿护卫还在,再怎麽说,凑上百来个人护送爹爹出城,还是可以的。但他绝不会走,我也不会,因为他是皇上、我是太子,这个时候,我们就该留在这里,哪怕是引颈待宰,也是我们的职责。天下人会知道,司马氏没有畏怯,更不会屈服。匈奴人杀了湣帝,有爹爹在建康起事,这一次,王敦就算杀了爹爹、杀了我,也还有你。……冲,你会把毗陵变成第二个建康,对吗?”
司马冲听到这里,揽紧了哥哥,一个劲地摇头。司马绍不再说话,拿斗篷包住了他,抱小孩一样将他抱下了楼,夥计早已牵过马来,司马绍将司马冲放到马上,一边替他拭泪,一边道:“好了,别让军士们看到这个样子,往後你就是大人了。”四顾无人,他忽然凑近过去,在司马冲唇上盖了个吻。
司马冲伸出手来,想要再抱他,他却狠下心肠,在马臀上猛拍了一下,司马冲下意识地环紧了马脖子,再回头望去,尘埃滚滚,哥哥的身影已越来越远。
26
日头慢慢爬上中天,往常这个时候,朱雀桥一带再热闹不过,可此时却是冷冷清清,店铺也好、人家也好,都紧紧合著门板。司马冲这才觉出,叛军真的是到了城下了。
司马冲明白,他该听哥哥的,立刻去朱雀桥头。就像绍说的那样,他们活著,首先是为了这个姓,其次才是为自个儿。可是他又模模糊糊地觉得,也许路并不只这一条,也许他不用去毗陵。突然,他想到了什麽,顿时调转马头,往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
再次见到司马冲,郭璞显得有些吃惊:“你怎麽回来了?”
一旁的四儿顿时垂下了眼去,不用说,司马绍来找司马冲的事情,他已经告诉了郭璞。
司马从脱下斗篷,缓缓地叠好了,抱在手里:“王敦不是一直叫我去武昌,一直想见我吗?眼下他都到石头城了,倒不请我去了吗?还是,”他微微一笑:“他原打算杀了皇上,再让你绑我去见他?”
被他这麽一说,郭璞脸色都变了,急忙摒退了四儿,掩上房门,低声道:“世子,我跟王敦是走得近些,但绝无弑君谋逆之心。你看,太子来找你,我明知他要送你走的,也未阻拦,更没跟王敦报信。怎麽说,你我也是忘年之交,连这点你都信不过我吗?”
司马冲望著他一声不吭,心里却也软了下来,时局动荡、君弱臣强,也怪不得郭璞依附王敦,其实满朝文武又有几个不是这样,都是些墙头草,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了。
“世子……”
郭璞还要说什麽,司马冲摆了摆手:“别这样叫我,听著都生分。景纯,我即刻就要见到王敦,你能帮我安排吧?”
郭璞点了点头:“这倒不难,只是……”
司马冲把斗篷放到桌上:“景纯,我知道许多事情你都看在眼里,但你没跟人说,往後你也不会跟任何人说吧?”说著,他把斗篷推到郭璞面前:“这是他的衣裳,你帮我保管吧。我这一去,再没脸穿著了。”
郭璞怔怔地看著那斗篷,半晌才伸出手,接了过去:“你放心,我不跟人说一个字的。可是,”他抬起头来,盯著司马冲:“你真想好了?”
司马冲把哥哥的斗篷和马都留在了郭家,郭璞给王敦修书时,他就站在一旁,一字字看郭璞写下,到了这个时候,他反而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平静。郭璞送他上牛车时,他还笑了笑:“景纯,那马有些欺生,你多费心吧。”
等牛车驶近石头城已是黄昏,司马冲拿出郭璞的书信,兵丁进去通报了,不多时便将司马冲引进一顶大帐,帐中摆了几十条几案,却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带路的兵士请司马冲落座,又端来了美酒佳肴,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司马冲只当王敦就要来的,攥著衣摆,闭目而待,谁知坐了半天,眼看著天一点点黑了,月亮都爬上了半空,帐外才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响。
他正了正衣襟,举目望去,却见两个军士掀开了帐帘,手中刀戈一架,在帐门内又立了道刀门,等了片刻,只见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探了进来,低伏著从刀戈下走过,待那人直起身来,司马冲不由愣住了,来人竟是王敦的堂弟,中书事王导。
王导见了司马冲也是一惊,这时,後面的大臣也源源不断地低头进来了,司马冲粗粗算去,居然有几十个人,朝中文武竟来了大半,那些人入到帐中,却没一个敢就座的,这样一来,便跟独坐的司马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7
司马冲虽然生性散淡,很少跟这些朝臣往来,但是眼睁睁看一班长者立在自己跟前,到底觉著不安,正要起身,却听“呛朗朗”一声,守门的兵士收起刀戈,垂手而立,外头靴声咂咂,大踏步地走进一个人来。
“诸位都到了麽。”那人如电的眸光在帐内扫了一圈,这才落到司马冲脸上,唇边泛出一丝笑意:“世子,久等了。”
自从禁苑围猎一别,司马冲跟王敦有两年没见了,此时重逢,却觉那人一点都没变,灼灼的目光落在身上,依然给人火烧般的错觉。司马冲强忍住不适,迎著他的目光,端坐不动。王敦见他并不回避自己,唇边的笑意更深了,竟撇下满帐的文武,径直朝司马冲走去。
眼看他越走越近,甚至抬起了手,仿佛要去碰司马冲的脸孔,司马冲心里的厌恶和恐惧都被放大到了极点。这次来,司马冲虽然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可眼下众目睽睽的,他实在无法忍受,就在王敦摸到他的前一刻,他突然朝著王敦跪了下去,避开了那只大手:“东海世子司马冲,拜见王将军。
帐中的官员们见司马冲跪下了,惊慌之下,也呼啦啦跪倒了一片:“我等拜见王将军。”
王敦哈哈大笑,一把搀起了司马冲:“世子跟我客气什麽?能见著你,我来建康,也算不虚此行。”说著往司马冲身旁一坐,俨然将这一桌当了主席。
百官听他如此说话,无不变色,却都低垂著脑袋,连大气都不敢出上一声。
王敦捏著司马冲的手,缓缓地环视众人:“诸位都是国之栋梁,我一介武夫,哪受得起这般大礼。”说著将手一挥:“都起来吧,看座。”
当下百官依著官阶在帐中落座,仆役们奉上茶来,可谁都没有心思去动。中书事王导朝王敦拱了供手道:“将军此来为的是除奸勤王,眼下刘隗、刁协都被将军击败,逃离了建康,将军功成也可歇兵了吧?”
王敦听了淡然一笑,捏著酒盏道:“贤弟,你带著这些人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吗?多年不见,一开口就是些俗事,真是一点长进没有。”说著,拉过司马冲,把酒盏送到他唇边,逼他喝了一口:“你看看东海世子,多麽识趣。”
司马冲垂著头,硬是把那口酒咽了下去,他既不看王敦,也不去看百官,可众人的目光扎在脸上,再厚的脸皮,也要被戳破了。王敦却还嫌不够一般,揽住他的肩,状似亲昵般问:“这些年有没有再练箭呢?”
这话问下去,只听帐角“!当”一声,有人将杯子扫到了地下。王敦抬眼看去,却是朝中重臣,仆射周顗,周伯仁,王敦攻下建康前,曾跟周顗在阵前交过手的,此时便朗笑道:“这是怎麽了?伯仁,你醉了不成?还是前日之战,打得不够尽兴吗?”
“尽兴?”周顗并没有喝酒,眼睛却是红的:“对!我只恨心有余、力不足,不能尽兴一战!”
“伯仁好胆色!”王敦哈哈大笑:“你倒说说,我今日的作为,世人将如何评判?”
众人听到这儿,心下都是一凛,王敦这几句话,摆明了是在挑周顗发怒,只等他骂出“乱臣贼子”,便好将他就地正法。有好心的官员,便偷偷去拽周顗的衣裳,谁知周顗丝毫不惧,拍开了那人的手,正要开口,司马冲却抢先接过了话头。
“将军胸怀天下、抱负非常,世人若是只看表面,见您直逼建康,屯军不朝,难免说您有谋逆之心,可要是他们能懂您的一片苦心,知道您并不会逼宫,此来只为诸奸臣、扶晋室,自然会说您是一个忠臣。”
司马冲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没有冒犯王敦,言辞间又下足了绊子,拿个“忠臣”的帽子拘住了王敦,叫他不好逼宫。群臣听了,都是一愣,众人望著这个以荒唐、放浪著称的世子,一时间也糊涂起来,不知他到底是站在王敦一边,还是别有隐衷。
王敦初听那番话,沈吟不语,接著便是一笑:“我又小看你了,你还真会说话。”
司马冲摇头:“我不过是替天下人说一句心里话。将军功劳盖世,又是大晋堂堂的驸马,怎麽可能弑君谋逆,做那些遭万世唾骂的勾当?不管旁人怎麽说,我总是相信将军的。”
一席话说下去,王敦并不应声,只是望著司马冲,也不在知想些什麽。众人等得心都焦了,他才笑了,抓过司马冲的手,攥在掌心:“这话说得,倒像是情话了。都说太子能干,依我看,你可比他聪明,要不,你来做太子吧?”
众人听到这里,都在暗抽冷气,司马冲脸上却淡淡的:“但凭将军吩咐。”
28
周顗忍无可忍,当下推翻几案,冲出了大帐,王敦却也不去理会,吩咐下人摆开了酒席。众人哪里吃得下去,又不敢违逆王敦,勉强喝了几口酒,只盼著酒席早些撤下。哪知王敦兴致极高,又召了帐下的参军前来作陪,这些参军一个个霸气凌人,连逼带灌,一直闹到半夜,百官不胜酒力,纷纷醉倒。
司马冲却没有醉,王敦喝起酒来并不像个武夫,大多时候他都是自饮自酌,除了开头做戏般的那一口酒,他再没逼过司马冲,百官醉倒之後,他甚至松开了揽著司马冲的手,这样的王敦,让司马冲觉得陌生,他甚至暗暗在想,也许王敦会放过他,也许王敦要的只是面上的臣服。
“你酒量不错。”王敦忽然说。
司马冲略略一怔,这才注意到,除了王敦这边的人,他是唯一醒著的一个。
“哪里,将军才是海量。”
王敦听了,便是一笑:“两年不见,你可真变了不少。”他伸出手来,捏著司马冲的下颌,盯著他莹亮的眼睛:“更会说话了,脾气也好了许多。我在武昌可听说你不少的事情……”
明知自己和哥哥的事情甚为隐秘,司马冲心头还是一颤,当下转开了视线:“都是流言吧。”
“是流言。都说你醉生梦死,很不成器,有了五石散,就什麽都不在乎了。可你真要是这麽一个荒唐人,为什麽会来见我?”
“我怕了。”司马冲抬起眼来:“你说过的,如果我觉得害怕,可以来找你。”
“怕什麽?”王敦摩挲著他的脸颊,声音有些沙哑。
“怕你。”司马冲望著他:“怕你的大军,怕再死人。我二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再有人出事。”
“司马睿已经把你过继给东海王了,他不当你儿子了,你还管他?”
“他总是生了我。”
“呵,你还真好心。”王敦推开司马冲,他像是有些暴躁,倒了杯酒一口灌下:“你这个样子,可活不久的。”他捏著酒盏,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在问司马冲:“这麽个乱世,又生在帝王家,你是怎麽活下来的?”
“不知道。”司马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