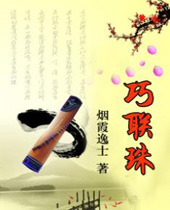凤凰珠-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章二十三、错身而过
七月初六 郑州
屋外阳光明媚,艳阳高照。
四海客栈里,陆小凤正躺在大盆热水里。这已经是他洗的第三盆水了,现在这水到还清亮。方才他走进客栈的时候,满身的泥泞,不似那风流倜傥的陆小凤,到似那街头上的叫花子。
他陆小凤混成了这副模样,到是拜了朱停的福。说什么终寻得了如何在天上飞的法子,却让他在深山里蹲了数日吃尽了苦头。
陆小凤长长的舒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低低笑了笑,好在结果还算不错。
听着窗外行街串巷的小贾高声叫卖,享受着痛快的热水澡,陆小风决定做个会享受的人。
去郑州最大的酒楼——海棠楼,大吃一顿,大口喝那里的海棠酿。他已经很多天没好好吃顿饭,好好喝回酒了。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开门的声音。
小二跑进来道:“有位大爷,给你留了张条子,说是有要紧的事。”
陆小凤笑道:“找我的都是要紧的事。拿过来吧。”
可当他看了条子,却笑不出来了。
小二道:“那位爷说了,爷您要是看了条子面色不善,便到海棠楼一聚。”
郑州最大的酒楼——海棠楼,彩阁雕窗,金扁碧榜。热闹如海,生意红火。
二楼第三扇窗户旁的衣架上,挂着件大红披风,街上的人只要抬头,一眼便能看见。
这二楼的第三扇窗户是海棠楼里最好的雅间。
而就在这雅间里,陆小凤正在等人。现在他心烦气燥,四条眉毛,没有一条舒展着,通通皱做一团。脸色灰暗,他本应大吃一顿,再大醉一场的,现在却全没了胃口。
他抚弄着手里的杯子,一口把杯里的酒喝干。
叹气,酒是好酒,十年的海棠酿,喝到嘴里却满是苦涩。
不禁摇头,从何时开始,酒也没了往日味道。
正暗自神伤,一个锦衣华服的人推门而入,坐到陆小凤的对面。此人乃是大内侍卫头目,“潇湘剑客”魏子云。
陆小凤也不抬头,只看着空了的杯子,一副悠载样子。
对方是只老狐狸,这是陆小凤心里早认定了的。你越着急 他便越不急,总会被抓到把柄。
陆小凤淡淡道:“事情怎样?”
魏子云在大内混迹多年,查言观色的能力,又怎是寻常人可比。
他见陆小凤虽然面色沉静,手却一刻不停的转动桌上杯子,早已了然。
想到陆小凤心中焦急,面皮上却故做镇定,不觉暗笑。
心里清楚,却又怎能轻易放过这平日里,嚣张骄傲的凤凰。
魏子云缓缓道:“花公子现在身在京城。”
听了这话,陆小凤再也端不住架子,急道:“那花满楼可是无事?”
魏子云眼里闪过一丝忧虑道:“你自己看吧。”
将一指宽窄的细绸,随手一抛,这丝绸就像是浮云般向陆小风飘了过去
丝绸本是至柔之物,却犹如被拖着一般送到陆小凤面前,魏子云手上功夫可见一般。
但此时的陆小凤却没有心情夸赞这一手俊功夫。
他的眼睛盯着,绸缎上的一行蝇头小楷。
“队六人,尽没。公子伤,送京师医。”
公子伤,送京师医。
七个字,看的陆小凤心惊肉跳,什么样的伤,一定要送到京城才能治。
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有了行动。
腾的起身,手中的杯子,落在地上,酒水飞溅。
陆小凤呆呆看着碎作数瓣的酒杯,又看向魏子云一字一顿,道:“我得走了。”
魏子云看着陆小凤,目光复杂,良久道:“你去吧。”
陆小凤抱拳谢过,便从二楼飞身跃下,不见了踪影。
魏子云看着对面空空的坐位,地上的碎瓷,幽幽而笑。
七月初九 石家庄
清晨,太阳还没露全了脑袋,街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
王安生照常提着前街上小酒馆里打的两钱黄酒,打着哈嚏,支起了自己的小摊子。
王安生是个书生,考了半辈子的试,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读书人肩不能提手不能挑,学问又不多,讨不到营生。为了糊口,便在街上支个摊子,替人执笔,带念家书。
这日,王安生刚坐下,椅子没捂热,正感叹世事不公,生不逢时。
生意就找上门,还是大生意。
一辆马车停在了他的小摊子前,车上下来位公子,在他对面坐了。
上下打量这公子,眉目俊郎,风度不凡,可面色却十分不好。
不是重病,便是重伤。
王安生道:“这位公子,可是要寻人代写文章?”
公子摇摇头道:“想请先生帮在下看本书,不知道先生可否愿意?”声音不大,显然是中气不足。
王安生道:“这……”这样生意从不曾听说,也不知道这公子什么打算,又怎敢答应。
公子似乎看穿王安生心思道:“先生莫多想,书便是这本,请先生过目。”说着从怀中将书取出,交于王安生。
王安生接过书,蓝色的皮子,没有题目,订的十分结实。
翻开书,竟然一字没有。再翻,还是白页,再翻,再翻,统统是白页。
王安生怒从心生,将书摔在桌上,怒道:“公子,莫非消遣小人。这书上一字未有。”
对面的人竟也是一惊,拿过桌上书,翻开一页页摸过。
秀眉紧皱,若有所思。
此时王安生才发现,面前俊朗公子双目无神,竟是个瞎子,顿觉心中愧疚。正要开口说些什么,突然由远及近,一阵急促马蹄,一匹快马卷风而过,向京城方向去了。
那马乌黑皮毛,四蹄雪白,端的是匹好马。
那马上的人,着大红披风,雪白长衫,也是个大好男儿。
王安生被那一人一马的光彩吸引,再次感叹世事不公。
等回过神来,那位公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远远望去,马车已走的远了,只看一片青烟中隐约的轮廓,似是朝南去了。
正要再发感慨,忽见桌上留有一锭银子,足有百两。看左右无人瞧见,立刻将银子收好,摊子也不要了,捂着银子奔了家去。
心道:今天端的是好运气,不知道碰上了哪路的贵人。
话说,那在骑乌云照雪宝马上的大好男儿,不是别人正是陆小凤。
这乌云照雪宝马本是魏子云的坐骑,硬是被陆小凤抢了来,连赶三日。从郑州到了石家庄,这日傍晚便到了京城九门提督郑国安府上,根据魏子云的传书,花满楼便是被送到此处疗伤。
然而,陆小凤却是迟了一步,花满楼已在前日离开了。
章二十四、七夕
七月初七
大脑从混沌中清醒,花满楼试图通过触摸了解自己处境。
然而只是轻微的移动手臂,一种难以忍受的钝痛便席卷而来。
同时,耳边传来清脆的童声:“大夫,大夫,公子醒了!公子醒了!”一串轻巧的足音伴着叫嚷渐渐远去。
接着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五个人先后涌进了屋子。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足音轻微,落步却十分沉稳,应是魏忠,魏公公。紧随其后的一个,步伐极大,频率微慢,身上带有盔甲碰撞的脆声,应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将领。而另外三人脚步虚浮并非练武之人,又身带药香,应是方才童子所唤大夫。
三位大夫中年岁最长的一位,坐到花满楼身边,开口道:“花公子总算是醒了,不知现在可否让老身为公子诊脉。”
花满楼轻声道:“劳烦了。”
老大夫三指轻扣于花满楼腕上寸、关、尺,闭目细听。
约四息,老大夫便停手皱眉,唤了身边略微年轻些的两位大夫,分别诊过。三人眼神交换,皆有难色。
老大夫转身道:“魏大人,郑大人,可否暂时回避。”
魏忠,郑国安先是一楞,随即道:“黄御医,说话何必如此客气。我们这就离去。”说罢,两人转身离去。
看两人确实走远了,黄大夫正色道:“花公子,我已请两位大人先行离去。请务必如实回答我等问题,万不可有所隐瞒。”
花满楼微笑道:“当遵医嘱。”
三位大夫,又对视一下,还是由黄大夫开口:“公子此次中毒之前,可曾另外中毒?”
花满楼道:“是。”
黄大夫道:“可是尚有余毒未除?”
花满楼道:“是。”
黄大夫道:“公子近日可曾接触过极寒之物?”
花满楼道:“是。”
黄大夫道:“公子月内可曾受伤大量失血?”
花满楼道:“是。”
黄大夫顿了顿道:“受伤之时可是行了房事?”
花满楼脸上无端飞起一抹红霞道:“是。”
黄大夫叹了口气道:“公子所受内伤本不重,应无大碍。然公子,脉象虚濡,指下空虛,浮取极力,按之无力空洞,随手空空,气血脾虚。加之余毒未消新毒又至,毒入血脉,引发潜藏寒症。此症源在太阴,乃遭风寒之邪侵犯所成,现却发于少阴,已寒伤六经。??”黄大夫说到此处,停了下来。
花满楼面色不变,缓缓道:“黄大夫,但说无妨。”
黄大夫道:“公子体内,寒邪已深,六经具染。虽可抑制,恐难拔除怕是已留下病根。以后逢阴寒湿潮,便有复发。况且公子体内尚有二毒纠缠,现在虽相互抑制暂不发作,可若不除去,公子一旦动用真气,定然气入邪路,走火入魔。”
花满楼微笑道:“花某本非争强好事之徒,所练些微功夫不过为强身健体而已。”花满楼听黄大夫言语,心中明白这毒一时是解不了的。
黄大夫听此话只道:“老夫无能,老夫无能啊。”
待大夫们离去,屋子重又恢复宁静。
只听得一声轻叹,绕于屋中。
晚色已浓,华灯早上,远远听到街巷上的繁华。
待侍童奉上汤药。
花满楼问道:“我可是昏睡了多日?今日是什么日子,听得外面好生热闹。”
侍童道:“公子睡了三日,今日已是七月初七,外面是七夕灯会。”
花满楼微一沉默道:“今日星光可好?”
侍童笑道:“今日天气甚好,连一只喜鹊的影子都见不到,怕都到天上去搭了鹊桥。”
花满楼笑道:“如此甚好,你且将窗子打开,让风吹进来些。”
侍童上前将床前窗户打开,又为花满楼披了衣服,便出屋去取瓜果。
窗外,繁星漫天,一道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牛郎、织女隔河相望,遥遥相对。
感受夜色星光,不觉轻吟:“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
“好雅兴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平白在屋内响起。
花满楼也不惊讶,笑道:“高人出手相助之恩尚未谢过,此番再见不知为何。”
那人笑道:“牛郎织女也可在七夕团聚,你却永失爱妻,难见爱女。着时过的落寞凄凉啊。”
那人的话就像一根刺,刺在花满楼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花满楼淡淡道:“伊人以逝,伤怀复又何用。”
那人扁扁嘴道:“当真无趣。”
花满楼道:“到是可惜了。”
那人叹道:“我且送你去见一人,你便高兴了。”
花满楼道:“什么人?”
那人道:“一个知道陆小凤在哪的人。”
花满楼微微一楞,随即道:“那确是应当见见。”
不一刻,待侍童端着满盘的乞巧果子回来的时候,房间中已经空空如野,只留下一张字条。
“突遇急事,不及告辞。多日捣扰,惟有来日感谢——花满楼”
章二十五、海水汤汤
七月二十三日 宁波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颁布禁海令,严禁人民驶船出海,各地港口多因此败落。然宁波港乃钦点的通商口岸,海外贸易与番帮的贡品多经此运达中原。因此非但不见衰败,反而越加忙碌繁华。各地商人货品云集,大有苏杭之风。
此刻响午未到,阳光火辣辣的灼烧着大地。似刚有一批货船到达,街上商贩往来,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这时一辆速度奇慢的马车,便显的与周遭景象格格不入了。
车里坐着的是位白衣公子,本是相貌堂堂的俊郎哥儿,此刻却形容憔悴,面色苍白。似是不堪路途劳累,似是强忍病痛折磨,公子双目紧闭,两眉攒簇。
马车缓缓前行,不多时停在一间茶楼门口。
公子下车入楼,虽是一付单薄身量,却不减风骨,清丽潇洒。
进得茶楼,小二上前招呼,给了赏,寻清净地方坐下。不一刻奉上茶水,点心。
楼里说书先生正讲那陆小凤传奇,说到大破青衣楼,困死霍休一节。
那说书的扇子一敲,轻咳一声道:“前面说到那陆小凤与花满楼追查幕后主使,将那青衣楼主霍休逼的走投无路,退无可退,眼看就要束手就擒。谁知那霍休却是老奸巨滑,退到屋中石台附近,搬动机关。只听“轰”的一声,上面竟落下个巨大的铁笼来,将霍休还有那石台通通罩住。”
此时一人打断道:“那霍休可是自寻死路?”
说书的道:“客官莫急,但听下文。”
“话说这铁笼子乃是由百炼精铜铸成,净重一千九百八十斤,就算有削铁如泥的刀剑,也未必能削得断,何况人力。原来此处是间密室,唯一的出路便在那石台下面。霍休此举竟是要将花满楼与陆小凤困死在这密室之中。
这当口,陆小凤却是哈哈大笑,突然抬臂挥手,十几青铜钱夹带劲风,向霍休打了过去。霍休没有动,也没有闪避,只等这些铜钱穿过铁笼的栅栏,他才招了招手,这十二枚铜钱就突然全部落入了他的掌里。这老人手上功夫之妙,连陆小凤看见都不禁动容,脱口道:好功夫!??”
台上先生书说的好,下面众人听的是如痴如醉。
白衣公子也不由想起当时那人狐狸般的笑,嘴角微扬。随即想到那人现在也不知身在何处,面对何等艰险,心里却又是五味陈杂,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
说道关键处,说书人扇子一撂,案板一拍,给徒弟递了个眼色,开口道:“诸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那小徒弟赶紧端了個铜盘绕著茶馆一路谢场:“谢谢大爺,谢谢捧场,明儿再见。”
底下一片嘈杂,叹息声伴着叮叮铛铛的打赏声,一路响了过去。
没了书听,众人就着话茬,说起了陆小凤。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仿佛亲眼见过般,事情说的有鼻子有眼。
不知是哪个说道:“前一日听说,陆小凤最近与大内侍卫合作。又破了西南异教,勤了百十来号人呢。”
“确实,不过听说那异教教主,却逃脱了。”
“听说那异教教主,会些个邪法。长的青面獠牙,三头六臂,非寻常人。”
众人你来我往,这异教教主,已然变做怪物。
白衣公子摇头轻叹,江湖流言,几真几假。
微微而笑,心中却是千回百转。
未时已过,外面热气聚集,茶楼里海风袭袭,到也凉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