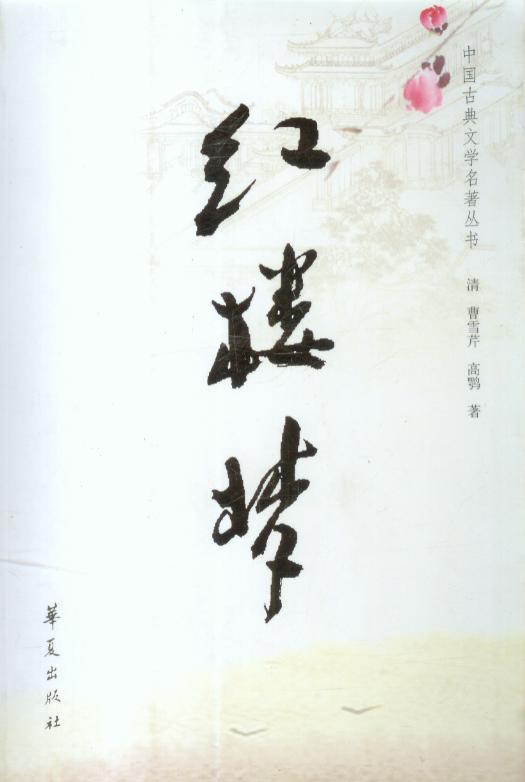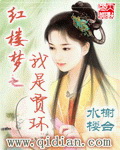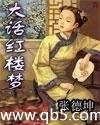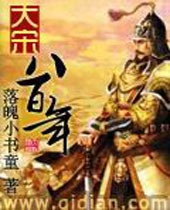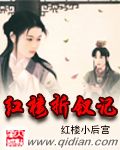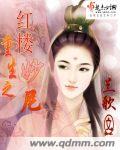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直接相关,甚至说曹家的事故,是“以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变局为其关纽”(《曹雪芹小传》第236页),这是周汝昌贯彻始终的红学观点。,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为读者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政治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是周汝昌具体考证出来并提出创见。
被称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是明遗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厉之士,但与曹寅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宁还京师任内务府郎中,杜赋长诗送别,其中写道:“昔有吴公子,历聘游上国。请观六代乐,风雅擅通识。彼乃闻道人,所友非佻达。又有魏陈思,肃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古来此二贤,流传著史册。”又说:“我观古人豪,保身谓明哲。其道无两端,素位即自得。置身富贵外,蘧几何通塞。譬如运瓮者,醯鸡非所屑。外身身始存,老氏养生术。”接下去还有:“经纬救世言,委蛇遵时策。奇文君能赏,疑义君能晰。”通篇感情深挚不说,主要是规劝曹寅如何为官处世,明显地涉及政治态度,如“素位”、“委蛇”等等,可见“二人非泛交”。这首诗是周汝昌从杜的《些山集辑》中找出来的,著录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详细考订。他提出:“曹寅等人当时之实际政见何若,颇可全面研究。”《红楼梦新证》(上)第313页。而杜在为曹寅的诗集所写的序里,更单刀直入地写道:“与荔轩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这是说开始对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后来发现曹寅和三国时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觉得原来的“户限”没有必要了。
那末,什么是“陈思之心”呢?周汝昌在曹寅《南辕杂诗》第十一首的小注里找到了线索。诗是七绝,四句为:“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小注是:“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曹寅:《楝亭集》(下)第3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曹丕受禅而曹植痛哭,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就中包含着对司马氏篡汉的预断,因为曹植于司马氏的野心早有察觉。所以周汝昌发现的这条线索是极为重要的。待到他看到明代张溥的评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愤怨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于是恍然大悟,说道:“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五),载1962年6月2日《光明日报》。就是说,陈思王曹植有臣汉之心,杜说“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证明曹寅也有臣汉之心。结论是否完全符合曹寅实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明遗民杜认为曹寅有臣汉之心这件事关于陈思王曹植的臣汉之心,丁晏在《陈思王年谱序》中也说过:“陈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汉之不幸也。夫陈王固未尝忘汉也。魏王受禅,王发丧悲哭,其《情诗》曰:‘游者叹黍离,行者歌式微’,《送应氏诗》曰:‘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故宫禾黍之感,有余痛焉。《赠丁仪王粲诗》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称其父臼‘皇佐’,大义凛然。服事之忠,唯王能守臣子之节,使其嗣位,岂有篡汉之事哉!”《见三曹资料汇编》第 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被严丝合缝地考证出来了。只此一例,即可见出周汝昌先生红学考证的功力。还有根据曹家习惯的命名方法,由曹寅的一个弟弟字子猷,逆推出他的名字叫曹宣,来源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犹,考慎其相。”从而找到“迷失”的曹宣,就红学考证来说,的确是一种学术贡献。
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红楼梦新证》的第八、第九章和附录编,就是对这几方面问题的考证《红楼梦新证》第八章为“文物杂考”,辨析丁曹雪芹画像、脂砚斋藏砚,“怡红”石印章和曹雪芹笔山;第九章为“脂砚斋批”,分脂批概况、脂砚何人、申著作权、议高续书四节,及补说三篇。。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参见《红楼梦新证》(下)第856页至第868页。,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有一条批语写道:“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以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批语中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许多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但周汝昌先生继续坚执己说;这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吴恩裕和吴世昌的贡献
考证派红学队伍相当庞大,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外,还有一批不乏个人心得的有影响的学者。早在1925年,李玄伯就著文对《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北京《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4日。;后来,1931年,胡适得到甲戌本,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不久,李玄伯又在《故宫周刊》上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根据曹寅、曹颐,曹朋的奏折,比较详尽地理出了曹家的一般状况,并认为曹雪芹是河北丰润曹氏的后裔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载《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第八十五期,1931年5月16日、23日。。方豪于1944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考》,则系统考证了《红楼梦》里的外国地名和外国物品,包括外国呢布、钟表、工艺品、饮食、药品、动物、美术等,一一追溯其来历,指出其中之洋货大都是贡品,从而见出《红楼梦》中之贾府以至于曹雪芹的家族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方豪:《红楼梦新考》,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5月版。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99页至332页。。对于多种西洋器物,方豪尽可能考证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在社会上的流行的情形。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到洋漆架,第五十三回写到洋漆茶盘,方豪查到了雍正赐给葡萄牙使臣的礼品单,其中有一箱全部是洋漆妆奁,另外一箱有洋漆柿子盒一对和洋漆盖碗四件,说明洋漆器物在清初是很贵重的。又如自鸣钟,是最早传入的西洋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即带有此物,到乾隆时已普及士大夫家,但康熙时还相当珍贵。《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一个金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而另外四五箱铜锡器皿总共卖了三百银子。所以方豪得出结论说:“《红楼梦》之作必在乾隆前也。”结论正确与否,自当别论,考证之细,令人赞叹。还有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也是考证派红学的重要人物。曾次亮考证曹雪芹的卒年,引入“时宪历”,证明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载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增加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论证力量。王利器1957年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王利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甚有裨益。朱南铣和周绍良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红楼梦书录》原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增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名一粟编著;《红楼梦卷》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一种,分第一、第二两册,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者亦署名一粟。是汇集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资料最全、最丰富的两部书,给予红学研究者的嘉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吴恩裕和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考证派红学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曹雪芹的生平》连载于1954年8月12日至31日、9月1日至30日、10月4、5日香港《大公报》,共二十四篇,五万多字,相当于一本简略的《曹雪芹传》。。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③《有关曹雪芹八种》包括:一、四松堂集外诗辑;二、四松堂集外诗辑跋;三、懋斋诗钞稿本考;四、鹪鹩庵笔麈手稿考;五、永忠的延芬室集底稿残本;六、明义及其《绿烟琐窗集》诗选;七、敦敏、敦诚与曹雪芹;八、考稗小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十种》把原《八种》的第一种移作附录,另外增加“红楼梦脂砚斋批语浅探二则”、“曹雪芹卒年考辨存稿三篇”、“记关于曹雪芹的传说”三种。1963年中华书局版。,1963年,又扩展为“十种”③,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发掘,敦敏的《懋斋诗钞》手稿、敦诚的《鹪鹩庵笔麈》手稿、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及抄本《四松堂诗钞》和《鹪鹩庵杂诗》,都是吴恩裕先生发现的。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做过事,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见《四松堂集》卷一。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芹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第428页至第429页;1976年增订版《新证》已修改旧说,认为吴恩裕的看法“为近是”,见《新证》下第721页。。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时候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
所以吴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二敦诗文中,除“当时虎门数晨夕”句,“虎门”一词凡五见:一为敦敏的《黄去非先生以四川县令内升比部主事进京相晤感成长句》云:“虎门绛帐遥回首,深愧传经负郑玄。”二是敦敏的《吊宅三卜孝廉》有句:“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三是敦诚的《先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一文,里面有“乙亥宗学岁试,钦命射策,诚随伯兄,试于虎门”的记载。四是敦诚的《寄子明兄》说:“松堂草稿,嵩山已序之矣。尚留简端,待兄一言,幸即挥付。仙旧序,希为转致,异日同在虎门一书,何如?”五是敦诚的《寿伯兄子明先生》诗,其中有句:“先生少壮时,虎门曾翱翔。文章擢巍第,笔墨叼恩光。”,证明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至第1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个别学者尚有异见赵冈认为“虎门”一词有时指宗学,有时指考试。敦诚诗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是指与雪芹一起参加乾隆丙子(1756年)年的顺天乡试,亦可作为一说。见赵冈《红楼梦新探》上篇第44页至第66页。又,高阳提出,雪芹是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该校与右翼宗学都在石虎胡同,距离甚近,故与敦氏兄弟缔交。见高阳《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一文,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33页至第140页。,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