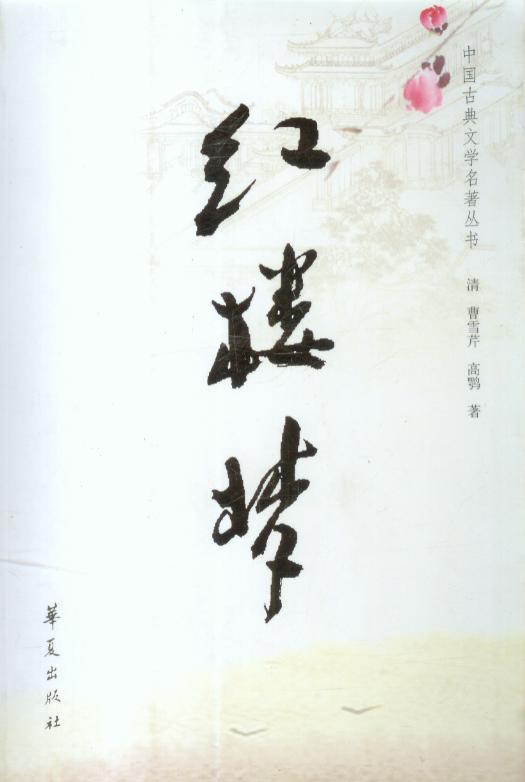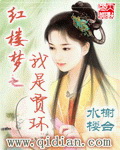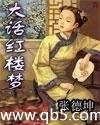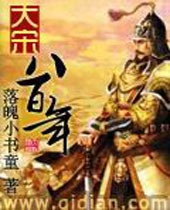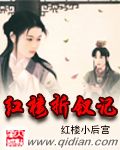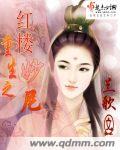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这就是王梦阮、沈瓶庵两位批评家所理解的《红楼梦》,以及他们所摹拟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矛盾心境。不能说这些看法毫无道理,主要在于如何具体看待《红楼梦》里的人和事。
《红楼梦》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自然要有相应的人物和情节,也就是王梦阮和沈瓶庵所说的“其人”和“其事”。他们在《红楼梦索隐》的“例言”中写道:“是书流行几二百年,而评本无一佳构。下走不敏,却于是书融会有年,因敢逐节加评,以见书中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即偶尔闲情点缀,亦自关合映带,点睛伏脉,与寻常小说演义者不同。以注经之法注红楼,敢云后来居上。”这说得够大胆也够自信的了。下面,不妨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王、沈所说的《红楼梦》里的人和事。
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诏书,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五台有清凉寺,帝即卓锡其间,吴梅村祭酒所为清凉山赞佛诗四章,即专为世祖而发。廉亲王允世子著《日下旧见》,载世祖七绝一首,末句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黄袍换却紫装裟。”近人《清宫词》,内有“清凉山下六龙来”之句,皆咏此事。
又一说世祖出家在天泰山,为京西三山之一,都人有“山前鬼王,山后魔王”之谚,魔王谓即世祖,众口一词,流传不禁。剃度时做诗数章,传本不同,有“来时鹘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又“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等句;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与《日下旧见》中所载小异,均为世祖出家之证。康熙之世,圣祖屡幸五台,并奉太皇太后而行,皆有所为。且至今京师谚语,谓人虚诞曰孝陵,孝陵者,世祖之空陵也。渔洋咏鼎湖原云:“多事桥陵一杯土,伴他鸿冢在人间”,即指此乎?又茂陵怀古一首,亦对世祖而发,故有“缑氏仙何往,瑶池信不回”之句。父老相传,言之凿凿,虽不见于诸家载记,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情僧之说,有由来矣。
至于董妃,突以汉人冒满姓(清时汉人冒满姓,多于本姓下加一格字,或一佳字,似此者甚多,不胜枚举)。因汉人无入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泱泱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一册,第6至第7页,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
总而言之,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与董小宛恋爱的故事,这是《红楼梦索隐》一书立论的全部基础。可惜,关于清世祖到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传闻和间接推测,从来没有直接证据。史家所谓的清初三大疑案:太后下嫁、世祖出家、雍正夺嫡,尤以世祖出家的材料依据最薄弱。把没有直接证据的传闻作为立论基础,不管故事编织得如何周详,也缺乏可靠性。至于被顺治皇帝封为贵妃的董鄂氏,为什么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更是无任何真实依据的历史传闻。孟森在《董小宛考》一文里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68至第194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以确切的史料考定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死于清顺治八年,活了二十八岁。而世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比小宛小十四岁。当小宛“长逝”时,世祖不过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两个人“年长以倍”,不可能发生如传说中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何况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记小宛与巢民的情事甚详,明载小宛于顺治辛卯年正月初二日“长逝”,哪里还会有被豫王掠入宫中的事情?小宛死后即葬在影梅庵中,所以冒巢民才作《影梅庵忆语》,同巢民相契的文友的诗作中也多有佐证详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86至第188页所引陈其年、吴园次、龚芝麓诸人诗文。。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三派之一的王、沈发动攻击,使用的就是孟森的考证材料。后来,孟森先生还著有《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两万余言,广引博征,丝丝入扣,彻底揭穿了顺治去五台山出家的妄说。其中有几处关键性的致疑点,孟森一一加以考辨,使之无以立足。
第一,史载清世祖崩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而《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据传说,认为“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到底何者为是?对此,孟森引《玉林国师年谱》的明文:“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选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则世祖崩殂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历历可考,毋庸置疑。王文靖是代世祖起草遗诏的汉大臣,他在自撰年谱中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不仅载明世祖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而且说明系出天花死的。此外,孟森又引录张宸写的记载世祖崩殂情形的一篇杂记,其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辛丑正月,世祖皇帝殡天。”当时曾“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证明世祖患的是痘疾。
第二,所谓世祖的遗诏是驾临五台山后,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因而“语语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对这种说法,孟森让起草遗诏的汉大臣王文靖站出来讲话,证明遗诏是世祖崩殂的前一天,即正月初六日所写,“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是奏知皇太后以后宣示的,因此不排除有皇太后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臣的意思掺入。诚如孟森所剖解:“以太后为枢纽,而四辅臣之将顺寄亲,敷衍满族,与宗亲满族之自争利益,皆在此遗诏中决之。故知王熙之撰诏,大半为太后辅臣之指,不言温树,情势宜然。”这应该是遗诏胪列罪己各款的真正原因。
第三,关于吴梅村所作《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历来被视作世祖出家的重要旁证,孟森先生一一重新加以笺释,说明此四首诗写的是董鄂氏死后,准备在五台山建道场的事,与世祖出家无涉。特别第三首,其中的四句写道:“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明白暗示世祖未及动身,即已崩殂。吴诗约写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在世祖遗诏颁布之后,铺陈瑰丽,情致绵绵,但纪事不应有二解。
第四,孟森先生考定,世祖之皇贵妃董鄂氏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氏系内大臣鄂硕女,十八岁入宫,顺治十三年八月册封为贤妃,同年十二月晋为皇贵妃,深受世祖宠爱。董鄂妃死后,世祖悲痛至极,也是事实。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所切之董,即此董鄂妃,绝非江南名妓董小宛。而且,世祖崩殂后,另有一位董鄂氏“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247至第278页。,孟森先生考出,这是董鄂贞妃。还有一位宁懿妃,也出自董鄂氏。由此可见,将世祖之妃董鄂氏附会为董小宛,纯属无稽之谈。
历史上既然并没有清世祖与董小宛恋爱并出家的事实,那么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便崩塌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略加考察,看王、沈是怎样具体进行索隐的,以便从观点和方法上总结是非得失,给该派红学以客观的历史的评价。
《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是敷演情僧即清世祖的故事,书中以宝玉况情僧,以黛玉况董妃,因而不得不费尽心思地去搜寻两者的“关合之处”:
如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也。
这说的是数字方面的“关合之处”。此外还有性情的“关合”,如:
宝玉不读书而文采甚茂,是圣人天禀聪明处;世祖优于文学,与宝玉正同。宝玉一生,儿女情深,不喜谈家国正事,大有不重江山重美人之意。处处为情僧张本。
如果这些地方就算“关合之处”,《红楼梦索隐》所举例证未免太少了,我们还可以替他们多补充一些。但例证再多,能说明什么呢?不是同样可以举出比这更多的不相“关合”的例证吗?比如宝玉喜欢吃胭脂,世祖未必喜欢;宝玉骂“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蠢”,世祖并没有这样骂过;宝玉平时“毁僧谤道”,世祖延高僧入禁中,极为好佛;宝玉崇尚一种平等的思想,待人接物很随便,世祖则不能不摆出皇帝的架子;宝玉给芳官起名为“耶律雄奴”,并说这是“犬戎名姓”,世祖无论如何不会这样糟蹋自己的祖宗,如此等等。借用王、沈的话说,《红楼梦》里这类世祖与宝玉不相“关合”的例证甚多,“分见各卷,不复详举”。我们采用这种反证法,足可以证明《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和具体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尤其荒唐的是,因为宝玉的伯父是贾赦,贾赦的夫人是邢夫人,宝玉的父亲是贾政,贾政的夫人为王夫人,于是《红楼梦索隐》的作者便由此四人的名姓中抽出赦、邢、政、王四字,说这是“直言摄行政王”的事。清初,多尔衮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不久又称“皇父摄政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53至第354页。。叔也好,父也好,这和宝玉与贾赦、贾政的关系,实在无任何“关合之处”。况且贾赦是宝玉的伯父,尤不相关。这些地方,完全暴露出王、沈索隐的牵强附会的实质。
关于黛玉与董小宛的所谓“关合处”,《红楼梦索隐》胪列的例证更多,然而仍不堪一驳。如说: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巡盐御史即为盐官,二字谜语趣甚(书中用谜语者甚多)。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谑矣。不特此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种,故黛玉爱葬花;小宛能烹调,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饮不饮,故黛玉最不能饮;小宛爱闻异香,故黛玉雅爱焚香;小宛熟读楚词,故黛玉好拟乐府;小宛爱义山集,故黛玉熟玉溪诗;小宛有奁艳集之编,故黛玉有五美吟之作;小宛行动不离书史,故黛玉卧室有若书房。且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潇湘妃子之义,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不然闺人断无以妃自名名人者,盖有本也。况小宛实为贵妃,故黛玉不但有妃子之称,且现妃子之服。又小宛著西洋褪红衫,人惊绝艳,故潇湘窗帧,独言茜纱,有意关合处也。
如果说前面所举清世祖和贾宝玉的一些例证,还勉强可以从数字和性情上找到某种“关合”的话,那末黛玉和董小宛的这些倒证,许多恰好是不相“关合”的。一个名白,一个名黛,就可以附会为“粉白黛绿之意”;依此,《红楼梦》中的小红,不是也可以与小宛“关合”,构成红白相间吗?琬,去掉了玉旁,写作宛,便是与林黛玉“平分各半之意”,那么《红楼梦》中具备“平分”条件的何止一个黛玉?小红即红玉,不是同样可以“平分”吗?小宛二十七岁入宫,黛玉进贾府时十三岁。错了——黛玉进贾府时年仅七岁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六章“红楼纪历”亦有考,可参看。,差不多是小宛入宫年龄的四分之一,不是“恰得小宛之半”。
退一步说,即便黛玉送贾府时年龄是小宛的一半,何以两者就有“关合”呢?两个人都“善病”,也许可以勉强算作“关合”,那末,一个爱梅,一个爱竹;一个善栽种,一个爱葬花;一个烹调,一个裁剪;一个熟读楚辞,一个好拟乐府;一个穿褪红衫,一个有茜纱窗,又“关合”在何处呢?毋宁说这恰好是不“关合”之处。至于说黛玉又名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更是不折不扣的杜撰。《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得明白:
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这才是黛玉称潇湘妃子的真正来历、直接内证,可以使《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无丝毫辩解的余地。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的不科学,还表现在认为一人可以影射多人或多人皆可影射一人。如影射董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