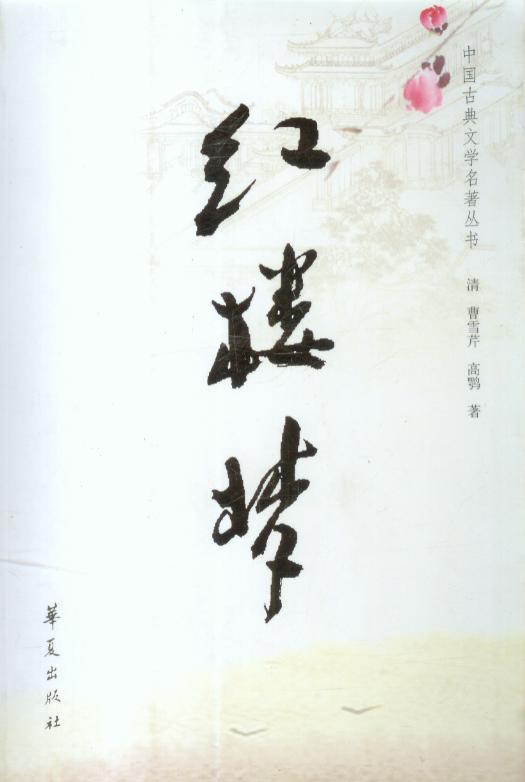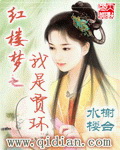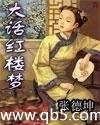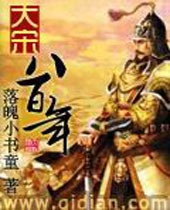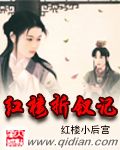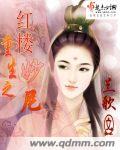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的特异之处,是联系清中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思潮,来讨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认为清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新兴市民阶层抬头了,于是便需要有表现他们理想的新文艺。他说:
新的社会阶层不满于封建教条之束缚,而要建立自身的新文化,这就是对封建制度做斗争的新知识群之意识形态。其特征就是人们自我之醒觉与发见,强调人类性去反抗封建的传统,对抗中世纪礼教的人生观,把人性从礼教中解放出来,于是有新型人性之新理论的建立,便形成了清初的启蒙思潮。当时南方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已提倡致用精神,北方学者颜元、李琳主张实践主义,都是这种思潮的最初表现。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57页。
因此文章提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形象的观点,并列举出表现在他们身上的八种新人特征,即第一,迂阔怪诡,聪明灵秀之气在千万人之上;第二,任性所为,无处不流露真情;第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遣教;第四,怀疑孔孟和朱子,动摇封建教条的中心思想;第五,一反旧日重男轻女之说,而重女轻男;第六,暴露门阀的丑恶;第七,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以强凌弱;第八,对弱者富于同情心。这样来概括贾宝玉等人物形象的思想特征,可以说是发了五十年代以后许多文章的先声,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研究者持此种看法。
陈觉玄的文章还指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新型人性意识的发展并不充分,原因是当时的商业资本必须依赖封建势力为后盾,虽不满于封建势力,又无法摆脱封建的羁绊,获得独立的发展。因此文章说:“在这样的矛盾之下,作家们乃不能成为自由的创造者,而不能不服从封建的特定的规律。既依据封建特权者所制定的规律来指导一切生活,故作者虽激情地创造出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而又不能任他的意志自由发展。他衔了五彩晶莹的一块玉出生,象征他一生的生命,而又常常为了它生气,几次要抛弃它、砸碎它。后来它竟丢了,宝玉也就失去灵性,任人播弄了。”就是说,宝玉身上的弱点和局限,也与明清之际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有关。文章最后总结道:
在十八世纪上期——雍正末年间,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只能暴露着旧社会的丑恶,尚未能憧憬到未来。由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乾隆三十年到五十年间,曹氏高氏所著的《红楼梦》,隐约地看到了新的理想,而又为旧势力所阻碍,终不能和它结合。这是由于当时市民层本身太软弱了,他们虽满怀着青春的理想,却不敢向封建势力正式挑战,只好把热情寄托在真假难分的梦想里,遂以幻梦预定出人们的行为,而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仍是新旧社会嬗变期中智识者意识的表现,也就是全书的基调所在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73页。
作者在文章中虽然没有使用唯物史观的字样,也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但基本上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阐述有一定理论深度,主要论点和理论思路被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五十年代及后来一些从同一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包括影响很大的文章,在观点上并没有比这篇文章增加更多的新东西。所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说法,这篇文章也提出来了,指出“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同时又以官僚身份经营商业”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63页。等等,这类一个时期成为红学文章的套语,原来也来源有自,不是后来论者的发明。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两本书,我指的是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前者初版于1945年,共五章:第一章是导言,申明对以往各种考证的态度及辨析《红楼梦》前后的异同;第二章论述曹雪芹的时代个性及其人生观;第三章分析宝玉、黛玉、宝钗、凤姐、贾雨村、薛蟠六个人物形象;第四章从家庭、教育、政治与法律、婚姻、社会、宗教、经济等方面,剖析《红楼梦》的世界;第五章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大部分章节在成书前都曾发表过第五章《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发表于1934年11月26日和12月3日的《国闻周报》;第三、四章《红楼梦》的世界和重要要人物分析,分别载于1935年《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第774至第777期及第814至第816期;第二章以《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哲学》为题,发表于1938年出版的上海《光明》杂志第3卷第3号。,成书时文字和篇章结构有所调整。
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学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学,末了,必得探讨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学中的地位。”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84页,1945年正中书局印行。是的,这一点对小说批评更为重要。李辰冬谈了四个方面,即人物描写、艺术结构、作品风格和情感表现,与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的文学巨匠比较着谈,处处紧扣作品本身,颇具说服力。他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既赋予人物以独特的个性,又不把人物简单化:
写李妈妈的可厌,赵姨娘的无识,夏金桂的凶泼,晴雯的尖刻,贾政的道学,贾环的下贱,贾赦的尴尬,薛蟠的任性,迎春的懦弱,妙玉的孤高,袭人的佞巧,并非让读者卑视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戒;他所以写湘云的天真,贾母的慈爱,宝钗的贞静,黛玉的多情,熙凤的才干,探春的敏慧,李纨的贤淑,贾兰的好学,也并非让读者赞扬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模范。他只是平心静气,以客观的态度,给每个人物一种性格,仅此而已。平心静气,客观态度,唯善于移情的人,才能如此,且因为他善于移情缘故,最易捉住人物的灵魂,所以《红楼梦》里许多几段或几句话,就创造了一位不朽的人物。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91页至第92页。
大观园中每个人物的室内陈设与主人性格的关系,为后来许多红学文章所津津乐道,李辰冬对此早有极细致的分析,也是举的探春、宝钗、黛玉三人住室的例子参见《红楼梦研究》第90至第91页。。他还将外貌与心理相联系,证明曹雪芹不仅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且是一位生理和相术家。其论《红楼梦》的风格则说:“将中国一切语体文的小说与《红楼梦》比较之下,就知道它的文字,更较成功。其成功之由,因作者确实的向自然语言下功夫,且因善于移情关系,能体会每个人物应有的言谈与语调,所以贾母有贾母的话,熙凤有熙凤的话,黛玉有黛玉的话,宝钗有宝钗的话,刘老老有刘老老的话。总之,因性格与年岁的不同,言谈的腔调也同时而异。”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103至第104页、第106页、第102页。认为《红楼梦》标志着语体文小说创作的成熟,给北京话一种“不灭的光荣”,是中国将来文字的模范。通过分析俗语和成语的运用,得出结论:“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小说家,并且是中国惟一无二的语体散文家。他的文字从日常语言中来的,然较日常语言还要流畅,还要自然。换言之,就是他把语言美化了,即令是下等的话,一到他的手里,就失了其卑贱性,而成为一种美感。”②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103至第104页、第106页、第102页。同时还正确指出,《红楼梦》的风格是诗的风格②。
《红楼梦》对情感的宣泄和文字的运用,达到高度圆熟,李辰冬比之为玩手球的演员:“球在他的手里,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时而球停于头,时而球立于脚,他的身上没一处不可以停球,高低上下,莫不旋转自如。好像球是为他一个人预备的,因为他真正握住了球的重心。曹雪芹对于中国文字,就有这种本领。他要喜,文字也喜,他要怒,文字也怒,他有多少情感,文字也有多少情感,在我们手里是死的文字,一到他手,就生龙活虎,变化无穷。曹雪芹之伟大,不只由于环境,不只由于移情,而也由于善为运用表现内心的文字。所以一部完善的作品,是内容与形式双具的,缺一,不能谓之真正的杰作。”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111页。他对曹雪芹的文学成就的总的估价是:
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 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赛尔望蒂(即塞万提斯——引者注)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这段文字笔者引用的是单篇发表时的文字,参见《红楼梦研究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49页。
这与我们今天对曹雪芹的评价殊无不同。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辰冬非常重视,认为是衡定《红楼梦》的价值的一篇重要文章,把它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相提并论,反映出作者有意与王国维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相承继。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初版于1948年,署名太愚,1962年和1963年改写了大部分篇章,1983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关于此书,我写有长篇评论拙著:《读红楼梦人物论》,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三辑。,现摘抄一段总体评价,供读者参考。
《红楼梦人物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落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的窠臼,摒弃了流行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剖解人物形象,来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清末民初的研究《红楼梦》的诸家中,重视人物形象分析的不在少数,如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很大篇幅都是论赞的《红楼梦》人物;西园主人的《红楼梦论辨》,也有人物论部分。至于各种题红诗,如焕明的《金陵十二钗咏》、姜祺的《红楼梦诗》、周澍的《红楼新咏》、黄金台的《红楼梦杂咏》、王墀的《红楼梦图咏》和朱瓣香的《读红楼梦诗》等,更主要是品评人物,抒发感慨还在其次。但这些都是片断的论述和偶拾琐记式的看法,远不如王昆仑同志的《红楼梦人物论》系统。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人物论》写作时间相近,设有《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专章,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也不能和《红楼梦人物论》相比。就对《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的透辟和具有系统性来说,王昆仑同志的《红楼梦人物论》,在解放前出版的红学著作中,堪称首屈一指,1948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由十九篇文章组成,重点论述的人物有袭人、晴雯、秦可卿、李纨、妙玉、惜春、紫鹃、芳官、探春、平儿、小红、鸳鸯、司棋、尤三姐、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贾母、刘老老、王熙凤、贾政、贾敬、贾赦、贾珍、贾琏、贾芸、贾环、门子、焦大、茗烟、柳五儿母女、龄官、傻大姐、史湘云、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等三十八人,《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形象都包括在内了。而且由于作者运用了先进的思想作为研究人物的指导,重视《红楼梦》中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两类不同人物的思想分野,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统治者形象,不仅进行分析和评论,也在进行揭露和鞭挞,对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形象则一往情深的加以赞颂,因此使《红楼梦人物论》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思想政治倾向的论著。其中《贾府的老爷少爷们》、《王熙凤论》等篇里的痛快淋漓的剖析,既是在论述《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里的人物,也是指斥横行于当时的反动势力。
《红楼梦人物论》主要是从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和道德的角度,来分析和评述《红楼梦》里的人物,从美学的角度加以评析则显得不够。这是本书的缺点,也是本书的特点。1962年王昆仑同志重新改写《红楼梦人物论》时,对特点有所发扬,对缺点有所是正。
小评批评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红楼梦人物论》的不足之处,不妨碍它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红学进入五十年代,开始了自有红学以来最不寻常的经历。不论是胡、蔡论战,还是考证派红学在材料方面惊喜的发现,影响的范围都是在学术界之内。只有五十年代初期环绕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展开的讨论,波及到了整个社会,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红学的发展来说,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笔者无意重新探究那场讨论的前因后果,更不想对学术以外的现实政治因素细加辨析。只愿指出,如果单纯从学术的层面着眼,当时对俞平伯的研究红学的角度和方法,存在很大的误解。李希凡和蓝翎在批评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中,即表示不赞成把考证的方法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认为:“考证的方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辨别时代的先后及真伪。俞平伯先生却越出了这个范围,用它代替了文艺批评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在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集,第67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显然没有将俞平伯的文学考证和胡适的历史考证区别开来,忽视了俞先生所追求的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合流的特征,这是非常大的误解。
误解的后果是多重的。俞先生本人固然因误解而蒙冤,障蔽了读者对他的红学研究的理解,就研究方法而言,则使考证与小说批评分道扬镳。从作品出发的文学考证,和小说批评原无矛盾,包括分析艺术形象,也可以辅之以考证的方法。现在视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