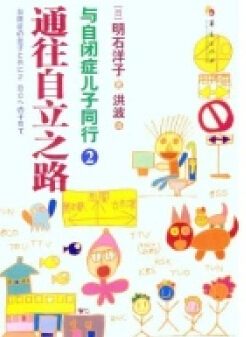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人曾经规定,每个成年健康人所需的食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和一个法国兵的口粮相等,并且不能有任何减缩而不损害到个体的健康。
在牛奶不充足的地方,补充人的体力的主要食品是大量地食用的肉类;因此大致每天每一个成年人需要三分之一磅左右。但是如果人们今天,例如说,要在法国一举而普遍实行共有共享制,人们在开始时就不可能给每个需要肉的人每天三分之一磅肉,因为不然将会在短期间把一切现存的牧群都消费光。这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各个大城市里的大多数小手工业者本来差不多每天就吃三分之一磅肉。不错;但是这些人虽然多,而比较起大群的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来,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种一个国家的牲畜数量和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这个国家具有一个不良的政府的最明显的证据。
人民是否有吃的,现有的牧群数和仓库里的存量是否足敷人民的需要,这是今天的那些政府很少关心或根本不去关心的事。只要他们,那些当政者们自己能够生活在快乐丰足中,他们的统治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来说,面前摆的永远是吃喝不尽的最好的肉,最上好的食品和饮料;他们还关心什么别人的不足;他们的统治根本不是为了别人,而是统治别人为了自己。
因此这也就不足为怪,如果说人民的单纯的、绵羊一样的忍耐会一旦变成一种不可羁勒的鬣狗式的暴怒。受到保护的愚蠢、荒谬和不义堆积得太多了。以前,人们还可以用毛掸子来拂去不正当的行为,而现在就必须用条帚来扫除,不久就有用粪叉子的必要了。
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来证明,目前的情况持续愈久,革命的经历就会愈可怕。
法国现在大约有六百六十八万一千头牛。其中大约每年宰杀三分之一,以致牛的数量虽然有随时繁殖以及国外输入的补充,但是和人口的增加相比,仍然有重大的减少,而那些吃肉的游手好闲者却不断地增加,因此肉价愈来愈贵,而工资却愈来愈少,现在已经有许多农民几乎每月吃不到一块肉。
现在我们以每头牛平均出六百磅可食用的肉计算,这样法国全部牧群的存量共可出产肉四十亿零八百六十万磅。
只要人们在三千三百万的法国人中供应二千四百万人每天三分之一磅定量的肉,一年就要吃去二十九亿二千万磅,因此尽管继续有繁殖,二年之内就要把全部现存的牛群吃光,第二年就要吃到羊和家禽,然后再吃到残余的猪、马、狗和猫。
据统计学家计算,如果人们把今天法国所消费的一切的肉平均分配,每人每日还得不到四分之一磅。
有人也许可以说:是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牧畜过剩的国家哩,它们可以用他们的余额来供应法国。
完全对!例如瑞士就输送许多牧群到法国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它的牧群太多了呢?
在瑞士有许多地方,在那里牛奶和马铃薯是唯一的食品。我曾经在琉瑟恩省的一个地方看见过一些七周岁的孩子,他们不知道面包是什么东西。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已经三年没有享受过面包;更不必说这些人有一块肉或是一碗肉汤送进他们嘴里了。在许多德语区里,大多数雇农和农妇只有在星期天才吃一次肉。
爱尔兰把肉类和粮食供应给英国的市场,而十分之九的本土居民却大部分倚赖马铃薯生活。
因此在金钱制度下,一个国家的某些产品出口并不足以证明这些产品和它的人口相比已经有富足和多余。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为了生存和劳动在他的食品里绝对地必须有肉;何况事实上那些游手好闲和从事无益工作的人也早已比那些必须汗流满面地去挣他们的面包吃的人更习惯于吃肉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前面那种人来说变革也就更加痛苦,如果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武装了的人民群众起来坚持要求根本推翻一切而拒绝任何渐进的措施的话。
在德国,它的牲畜表面上比法国多,并且它的数目也到处在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还是赶不上人口:甚至,根据最近摩尔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托所作的统计调查,德国的平均消费量甚至还小于法国。
你们看!我们那些聪明睿智、至尊至贵的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就是这种状况。在一切国家里必需品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之间的失调都在走向同一的可怕的前途,并且这个前途愈往下走,就愈更可怕。
而那时候,那种愚蠢的恶意的蠢材们,象通常一样,又会来责备那些未来的革命者们的残酷和暴虐了,如果后者为了消除罪恶,不得不给社会动一次痛苦的手术的话。
今天,如果说什么地方必需品的生产有富余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此尽任何力。如果这些政府是以共有共享为原则,而不是以分散孤立为原则的政府,那末它就要说:因为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已经证明,一个人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品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必须把必要的食品的生产提高到和增长的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因此至少每三个人必须有一头牛。但是牛数不够这个比例: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那些高贵的大人先生们也算在里面。
今天,如果共有共享制在任何一国普遍实现,在这个国家里不论最初的第一或第二年都不允许宰杀太多小牛;同样,在这段时期我们还必须在牛奶和肉类的享受上励行最大程度的节约,只有对从事最繁重劳动的劳动者才配给他全份的肉食供应。我们将必须忍受这样的牺牲,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成倍增加牲畜数量,并使它能和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此外人们还必须下决心把一切供奢侈用的马匹都训练为耕马和战马,任何牧场草地不得改为农田,并且必须以最大的关心注意用于农业和牧畜事业。不止如此,人们还必须从邻近的,还没有实行共有共享制的各国尽可能大量地输入牲畜和食物。而在那里,我们除了用加倍的、加若干倍的价格去收买这些东西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为此,凡是能搜寻出来的一切金子、银子都必须用于这个目的。人们要这些废物有什么用,根本又不能吃它。而如果这些国家的当权者禁止输出的话,那就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战争,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比那些生活在旧秩序里的其他社会是更有力量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我们的战士才能吃到丰富足够的肉类。在战时,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肉都供应给战士;而其余的人就可以在节约上来考验和证明他们的贡献,以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把他的个人利益贡献给现存和未来世代的全体人的福利。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就是现存的社会关系是这样一种状况,它迫使未来的共有共享制的创立者不得不在接任行政管理之初便立即励行一种严格的节约,因为必须立即约束住某些人的已经恶化了的欲望,并且即使这样也还并不能满足眼前的急迫需要和人的合理的愿望——正是因为这样,因此在人口和它的全体成员的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产品之间的失调愈剧烈,改革的经历也就愈显得可怕。你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一切国家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境况都贫困到象在英国一样;你们试想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发了一次社会革命;试问那时候胜利了的人民会仅仅满足于渐进的办法吗?试问由于急速、彻底地摧毁了一切现存的事物,能够不严重地侵犯到那一切长期习惯于旧制度的、耽于淫乐的富人们的生存和利益吗?
你们愈是在国内造成更大的贫乏,那末一旦人民在一次革命之后要求和你们平等地享受的时候,你们的困乏也就愈甚了。现在人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目前我们有些什么手段可以来推行这种社会改革?这就是:
1.继续进行教育和说服。39)
在这方面除了我们个人的热情外,我们还要利用出版自由和法庭的公开审判。借此就能把我们的言论说出去。
2.把现在已经存在的混乱状态加速地推到它的最高峰。在这方面需要有若干人的牺牲,最好是那些地位高的、为一切社会阶级视为典范的、德高望重的人物。借此就把事情做起来了。
这第二个手段,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
如果尽管有一切合理的理由,而那些政府也不采取措施来改善人数最多的最穷困的阶级的处境,相反,如果混乱不断地继续增长,那末一切凡是在宣传启发之外还有一点胆量勇气的人,就必须停止再去反对这种混乱,相反,他们应该设法把它推到最高峰。从而使贫苦人民在那增长的混乱中得到一种满足和快乐,就象士兵在战争中得到了一种快乐一样,而那些被压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到的不便就象富人们在战争中所感到的不便一样。
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总不能不感觉;那时候被他们所保卫的那个混乱我们就不去保卫它了;那时候那迄今几乎是由我们单独承担的这个混乱的恶果,就必须由他们一起来分担了。那时候,总而言之,他们那个混乱的制度对于他们将糟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它对于他们将比那漫漫无期的奴隶制对于我们来说还更可厌些。
当我们必须应用这第二个手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说服启发,再去建立系统和提出各种改善的建议了,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说我们要什么,而是只要把凡是我们所不要的一切,都用这个办法去对付它。
但是只要有可能应用这个手段,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的组织的一无是处;因为如果这个组织对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手段也就起不了作用了。
此外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
以一种过于漫长的秩序去进行过渡,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如果人们手上有了力量,就必须一下子把蛇的头打烂,也就是说不是要在敌人中造成流血屠杀或是劫夺他们的自由,而是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
如果人们在过渡时期不去削弱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如果人们还保障他们的一部分自私利益,人们就给了贫穷的、受苦的人民一个道义上的坏榜样,并且如果那样一个人还剩下些什么贫乏的、远不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减低人民的困苦呢,这种困苦即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消除的,因为它已经侵蚀的太深了。甚至用最激进的改革的方法,人们也不能一开始就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然的欲望并因而把残余的物资都完全消费净尽,而是必须对残余的物资厉行这样的节约,使它在短时期内能成倍地增加起来,然后人们才能增加享受和减少劳动;甚至劳动时间在最初两年内也不能立即减少到每日六小时,因为那时候迫切地需要开垦一切荒地,建造为生产和产品的交换所必需的铁路,运河以及工厂、机器。此外在这个时期内很可能战争还要占去大量强壮的人手。因此如果说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可能在最初两年内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或是大量增加他们的享受,那末如果除此而外还要去保障那些被击败了的富人和有势力者的特权,那就会不成话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强迫那些习惯于淫乐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去劳动和放弃财产,而是必须通过他们的财富的逐渐消损而使他们不必有剧烈的冲击而一步步地习惯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然的享受。
在推翻了现存秩序之后,凡是为了使最初两年内的牺牲变得轻些而可能去做的事都必须着手做起来;因此,在组织劳动和管理的同时,必须立即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一个措施,并且同时它也是新组织的基础。
在战争中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劳动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上不得优于最年轻的鼓手或是公路上的砸石子的人。如果在战时全部肉食口粮都供了军队之用,那末领导者就必须和其他的劳动者完全一样地度斋日。如果对于农民和工人每月有十五天斋日,对于行政管理机关和学者也就同样有十五天的斋日。如果要求人民耐心地忍受那在开始时所必要的节约,那末这种节约的榜样必须在一开始就做出来。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地缓和的过渡时期,那末我们就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现在,治疗社会的罪恶已经不可能不应用种种暂时性的毒药,已经不能不带有那由此而来的、被动的混乱的扩展;但是在五十到一百年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可怕得多。
因此我们不要说,人类对这件事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
如果人们让穷人注意看一看那些储积起来的产品,并且对他说:“去劳动!然后你就去取吧!”他就会完全懂得,有要比一无所有好!
最糊涂的人也不会糊涂到拒绝送上门来的利益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那个混乱的制度随时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机会去以毒攻毒的话。
反对个人的战争或是流血的革命,我们让那些政治家去干;反对私有财产的战争或是精神的革命,必须我们来干。
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
一旦风暴来临,就不能再象当年在哈姆巴哈那样为了无用的讲论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了:而是必须象闪电一样地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