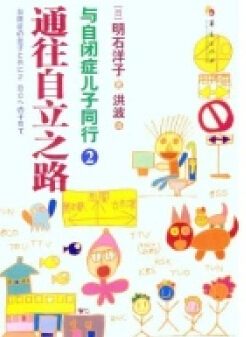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们的核心①发动了关于财产共有共享原则的口头和手写传单的宣传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多方面向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印刷一些证明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传品。“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当时在人民群众中还是不被人所知的,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法文著作,也许“巴贝夫的密谋”可以算作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要搜求到这本书必须化很多钱。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完整的对资本和才能赋予物质特权的联合组织的社会学说,就是傅立叶的社会制度;此外,在若干年前也有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欧文的制度,但是它既不为大家所周知,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完整的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就是说一种这样的学说:它彻底地解决了这些主要的问题,它向我们证明,——尽管有一大批人从事不舒适的、有害的劳动,又有一大批人专在享受,虽然这些享受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尽管这样,人们如何能够来建立一些组织和制度,并按照这些组织和制度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促进而不会危害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①“核心”是指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同盟试图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在巴黎的全体德国人中去。
由于共有共享原则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员魏森巴哈和霍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经委员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二千册。为了筹措印刷费,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现了令人极为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腾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间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订的工作,另一些人出钱,甚至在没有钱的时候把他们的表送进了当铺。
从这时候以后,为了传播共产主义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毛勒尔以及特别是阿伦兹,这个德籍的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绩和报酬则十分谦让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认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更能作贡献的人。可惜有这种品质的人不多,但是没有这种品质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彻底的运动。①
①魏特林对亨利希·阿伦兹大加称赞,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恩格斯在1846年8月间把巴黎工人的意见通知在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不是魏特林单独一人写的。他提到阿伦兹(显然和魏特林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西蒙·施米特和奥古斯特·贝克尔这些人的名字。魏特林在这里所写的整个这一段,特别是第二句,使人有理由可以设想恩格斯所传达的推测至少对于《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是相符的,并且这个工作还同时有好几个人参加。就《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来说,也可以设想,魏特林的朋友和协作者曾经在搜集资料上帮助过他,这当然绝不减损他的功绩和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自己也说:“……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上文所提到的推测,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理解为对于魏特林的作者身分有争论的意思。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梅林、卡勒尔、施吕特以及其他人等都不曾对此有过怀疑。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移动,在1839年已经向着德国国内发展。184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结社里,发现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趋向混合在一起,这至少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推断出来,就是:在许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共产主义小册子①。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口头和文字宣传更为有力,发挥作用更大的举动是高贵的巴尔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领导的起义。这个年轻而颇为富有的人组织了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坚强的秘密会社,他为了这个组织献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于5月12日下午自己带着这三百人到大街上,指挥进攻,这是千百万平常人所称之为疯狂的举动,他们不明白,那些高贵的心灵由于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往往会促成怎样的强有力的进步。三百个幼稚的、赤手空拳的男儿对抗十万武装起来的雇佣兵和资产阶级骑士!而这是由一个可以安享青春富足的人所自愿地决定并且勇敢地执行的行动,为了希望由此可以给穷人们重建那久已失去的平等的天国!②
①《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在出版之后不久就在德国流传。例如制鞋工人亚克毕就在1839年春季从巴黎带了许多册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去。
②魏特林似乎一直没有放弃他对于举行暴动以及对于统治阶级有一天会自愿交出他们的财产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但是在第一版里,他曾经带着渺茫的希望表示过这种可能,认为可能找到若干个别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会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来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他在“结束语”里写道,“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并不把一切寄托倚赖在这一点上”。对于布朗基和巴尔贝斯所领导的起义,他只是赞扬这些战士们的胆量和果断,他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丧失了这种品质。并且他把这些因素绝对化了,认为这些主观因素比客观的社会条件对于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百个牺牲者,在六处街道掩护体后面,以拼死的勇气一直战斗到力竭而死。人民舍弃了他们。晚间九点钟,最后一个掩体被摧毁。巴尔贝斯就在这里负伤倒了下去。当时还有唯一的一个也负着伤的人站在他的身边保卫他,是一个金色散发的德国鞋匠。你们记住这个坚毅的德国人的名字:但泽巿的奥斯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若干年前据报道他已经在监狱里变成疯人了。在胜利的二月革命之后,巴尔贝斯的殉道者们从监房里走出来,在尊敬和光荣的欢呼声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关于我们的奥斯屯却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起义被镇压以后,迫害又加到一个德国流亡者名叫沙佩尔的身上,并且把他遣送到伦敦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同时移植到了伦敦,在那里同样经过沙佩尔、莫尔、鲍威尔以及其他人等的努力,经过长年的、辛苦的经营得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并且能够对于宣传工作提供丰富的养料。在伦敦协会①的工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可以特别提出,是在1844年参加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中的负伤者、被捕者和遗属们的募捐这件事,在募捐的同时,还散发了一份告群众书,号召举行另一次更惊人的起义。
①“伦敦协会”是指“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它是由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在他们从巴黎被放逐到伦敦之后,于1840年2月7日组织成立的。恩格斯曾经写道:“这个协会是同盟(指‘正义者同盟’——原编者注)吸收新盟员的地方,而因为共产主义者照例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于是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在魏特林居留伦敦的那几年(据推算是从1844年8月到1846年3月),摩利是协会的会长,沙佩尔是秘书兼会计。
1840年出版了卡贝的一本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写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①。尽管卡贝、欧文、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没有满足批评家们的理智,但是那些最高贵的心灵和感情却在他们这里找到了满意的东西,并且凭借它们得以在各种混淆视听的局面下保持清醒。
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经过烦琐的理智挑剔出来的空白,由傅立叶加以填补了,但是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平等这个意义去填补的。共产主义赢得了更多人的心灵和感情,而傅立叶主义则赢得了更多的重理智的人,以至于傅立叶的这种只要和平行动的和对富人阿谀的理智,在那些具有高尚感情的和自傲于革命传统的法国人眼里失去了信任,因此这就再一次给我们指出了,为了真正的实现我们的理想,只能依靠那些有理解力的热烈的心灵,而不能依靠那种冷静的、淡漠的、自私的理智。②
①里查·拉霍蒂埃作为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信徒,是新巴贝夫主义的主要代表。1839年出版了他的《社会改革原理初步》,184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新巴贝夫主义哲学的小册子《论社会法则》。1841年起他主编《博爱》杂志。参看罗琪尔·加罗第:《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1954年柏林版,第191页。——德奥多·德萨米(1803—1850)起初是卡贝的信徒,后来反对他,主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出版了一个期刊《平等之友》。他的《公有法典》出版于1842年。德萨米以及其他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168页),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
②(参看本书第301页注①)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第二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说得更清楚。他说:“因此我们看到,那种规定共产主义的本质的力量,不在于矫揉造作、字斟句酌的流畅的词句,而是在于心灵的高贵的感情;而那种以培养和加强这种感情为已任的理智,则可以最好地领导这种感情”。对于魏特林来说,共产主义和宗教一样也只是一件“心灵的事”。
1840年,欧文在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中也著名了。他和傅立叶一样,早在1830年的革命之前就久已为社会主义而努力。他的名字在书刊和报纸上被广泛地提到,但是他的学说的真正的本质却被我们的文学骗子们一直掩盖着,这些文学骗子们的兴趣在于通过对事实的歪曲而使谬误能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所接受。他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把傅立叶体系里足以代表傅立叶学说的、以及与共产主义者所热心的事业协调一致的那些主要部分译成德文,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把每一句美丽的琐屑的废话,倒是尽快地译成了德文。我们在政治进展的道路上处于精神落后和跛踬状态,特别要归罪于德国文学界这种不良的歪风。在我们这个寓言式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禽兽世界里,那些有审美修养的、腰缠万贯的雄蜂、猿猴和八哥们,在一切理智和感情失调的呓语疯话里作领唱人,而无数有教养的、有智力的人——如果他们要生活的话——就只能跟着这个调子走。
1841年出版了蒲鲁东的最好的著作:《什么是财产?》,①这本书由于它的结论而著名:“私有财产是贼赃”。这本书,作为对于私有财产的最好的批评,在任何情形下将是社会主义文库里的一颗永远灿烂的明珠。蒲鲁东此后还写了不少值得一读的书,但是很可惜其中不时出现许多损害自己政党力量的、并且把共产主义当成攻击目标的字面争论,可以说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七年之久,被共产主义者当成是自己人来尊敬的蒲鲁东,故意不理采或是根本抛弃了卡贝和傅立叶的学说,并且表示,他秘藏着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七年之久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批评的焦点上,在这个时期内,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他孵化的那只《经济主义》的神秘的鸡蛋;但是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正象我们在类似情形下通常所看到了的: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事已经由蒲鲁东自己来证实了,他最后孵出的这只小鸡和其他满地跑的小鸡一模一样,就象我们分不出这只鸡蛋还是那只鸡蛋一样。蒲鲁东给我们的七年之谜终于揭晓了,原来是一本叫作《信用和流通的组织与社会问题的解答》的书①。希望法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沙漠里不要把我们这位经济学家的离开正道的绿洲当作是所约定的迦南地,最好把它扔在一边,仍然按着巴贝夫、巴尔贝斯、拉斯拜尔②以及其他人等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①这本书以两篇论文的方式分别发表:1840年,《什么是财产?或论法权与政府的原则。第一稿》。1841年,《什么是财产?第二稿。致布朗基教授书。论财产》。
①这本书出版于1848年。
②拉斯拜尔(1794—1878),医生兼化学、医学和生物学著作的编辑。他是“人民之友社”的社长,这个社是1830年革命期间成立的。他因参加1848年的革命,被判处五年徒刑。
显然,这七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七年。蒲鲁东诚然是一个令人注意的作家,但决不象我们无知的德国批评家向全世界吹嘘的那样重要的经济学家,这是马克思已经部分地加以证明的。③若是仅仅按上面所提到那本书来评判,我根本不会把他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他以前的那些著作在我的批判的天平上增加了一个较大的砝码的话。总之,1843年蒲鲁东关于社会改良的知识,和他对共产主义的攻讦所令人推想的比较起来,发展要少得多。这是随时都可以给他证明的。被压迫人类的事业必须有卓越的心灵来领导;这些领导者不应该容忍一个毫无心肝的人吹毛求疵的诋毁、攻讦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名称,我们是用这个名称称呼我们的党的。这些吹毛求疵的人简直就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究竟在于什么。更进一步说:象蒲鲁东这样一个甚至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人——这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无疑可以看作是一种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