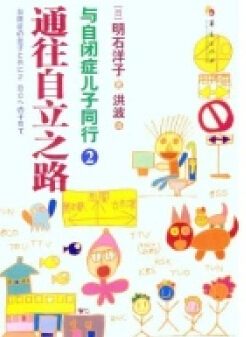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国人来说无疑可以看作是一种牺牲——当然他也应该读过1842年由德拉拉琪亚和1844年《新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是看过早在1829年英国人布雷写的那些论文。①如果他没有读过,这不能构成对他原谅的理由;如果他读过,他就应该知道,共产主义者是把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的。
③这里他指的是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出版于1847年,是对蒲鲁东1846年《经济矛盾的系统,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的答复。
①路易·亨利·德拉拉琪亚(1807—1891),邦纳罗蒂的学生和朋友,是瓦德省的国务参议官兼教育厅长。他主张选任蒲鲁东为瑞士科学院院士。他是“青年欧洲”的会员,在这个团体解散之后,组织了一个急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协会。“正义者同盟”通过西蒙·施米特与德拉拉琪亚有若干联系。约翰·布雷(1809—1895)是欧文的信徒,宪章运动者,主张所谓“劳动货币”,并进行理论工作。大概魏特林采取了他那关于交换银行的意见,这种意见曾为蒲鲁东所利用。
1841年,在经历了若干次失败的努力尝试之后,共产主义在瑞士的德国劳动者之间第一次传播开来,并且得到良好的成果。在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建立了四个公共食堂:日内瓦、洛桑、威维斯和摩尔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的组织。同时在日内瓦也创办了一份月刊《吁助德国青年》,由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所支持,拥有一千名订户。
当时,我们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出版自由,并且散居在国外。我们只是一小群人,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随时准备为我们的事业而牺牲。现在我们有了出版自由,我们和数百万德国劳动者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建立了几百个各种不同的协会,但是人们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却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非常不好的!在心灵和感情上你们还没有什么光辉的杰出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人民之友》,这是一份由具有高贵心灵的年轻人施略费尔主编的在柏林出版的报纸,虽在销行,却收不回它的印刷费用。许多类似的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出版物,都由于缺乏订户而很快的相继停刊。《初选选民》是一份共产主义的周刊,在刊物的题旨方面,任何刊物也比不上它,但在发行量上,它却敌不过别人,在柏林及其近郊不过销行一百五十份。《盟兄弟》是一份拥有二百人以上结盟弟兄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协会的机关报,已经出版了四个月,只有三百七十份订户。①
①《人民之友》1848年出版了十二期。有1947年莱比锡的影印版。——魏特林所创立的《初选选民》1848年10月及11月出版于柏林。《盟兄弟》于1849年在他从柏林放逐之后居留在汉堡的时期出版于汉堡。
1842年,由于巴黎、日内瓦、拉·萧德封、洛桑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使《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能够印行二千册。约有三百个工人各自尽了他们的力量,以取得这本书为酬分担了全部印刷费。
在这个时期里,一些有特殊表现的人之中——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高度热情的人,他们从自己高贵品质和无私忘我的光辉榜样,鼓励了更多有热情的人和他们一样勇于作出牺牲,在这些人之中,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哥本哈根的彼得逊和西蒙·施米特,还有洛灵根的一个鞣皮工,这个工人由于他的出身好,他比前面两个人有更好的表现。
1843年春,我们的共产主义月刊,由于警察迫害不可能在伯尔尼和日内瓦印刷,后来只好迁往苏黎世印刷。在这时候出版了制刷工人阿·狄迟(A·Dietsch)的《千年之国》,①在阿脑的晁克斯的农民邻居之中作了很多的宣传,这本小册子拥有广大的读者,到现在已经印过三版。
同年春天,在苏黎世正准备出版《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在完成校改清样之前,这本书的稿样和我所有全部书籍和文件一起都被没收了。继此之后,对于共产主义者的逮捕、审讯、驱逐和遣送出境日益扩大。在我们的行列里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奥古斯特·贝克尔、西蒙·施米特、彼得逊、克里斯田生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时候仍然在坚持着;参看:阿·贝克尔的《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和《愉快的消息》。②同年,还出版了另一本书,它使共产主义在德国得到最早的传播,这真是值得感谢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瑞士官方出版的,在若干时期内没有遇到任何审查的障碍,我指的是《布伦奇里报告》,其中包括人们在逮捕我的当晚在我那里搜寻来的信件和手稿。在苏黎世被没收去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由于共产主义者的热情,努力设法把原稿从司法机关的手里夺了回来,此后在伯尔尼出了第一版。
①1843年出版。
②《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出版于1844年。《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快的消息从1845年4月至9月由贝克尔出版。
1844年,德国哲学也归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是赫斯,然后是吕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的镜子》、《威斯特伐利亚的汽船》和巴黎《前进报》等)。可惜后者这些人虽然用他们的尖锐的批评为事业而服务,却也并不是永远没有伤害自己人这样的事。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于1840年曾经有一个匈牙利文译本,并曾于1846年再版。此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两书也在这一年再版,并且两者都被译成挪威文,《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的法文节译本早已于1843年印行。
海尔曼·克利盖,在威斯特伐利亚热心地为共产主义宣传辩护之后,这时候已经前往美国。他的富有鼓动力的言论在美国燃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创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周刊《人民论坛报》。①但是克利盖的思想和感情都是风云多变的。起初,克利盖使他的共产主义适应于民族改良派,这个党派要想通过每个公民分得一百六十亩田地来解放全人类。后来他干脆放弃了共产主义,而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宣传鼓动。这时候在纽约出版了《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第三版和一个英译本,以及《呼救》②的第二版和它的英译本。
①《人民论坛报》第一期出版于1846年1月5日。题词是“劳动万岁!打倒资本”!从第十期以后采用了“青年美洲机关报”(它是当时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的领导机关,参看本书第47页。——中译本编者注)的字样。在经过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1846年5月的批评之后取消了题词。这份报纸于1846年12月停刊。
②魏特林写的这本小册子《向劳动和愁苦人们的一个呼救》第一版,出版时间应该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第二版出版于1848年。
运动就象一道地下的炽烈的火山熔流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在社会各阶级之中,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向四面八方冲开道路,它壅积在火山口下,时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托马斯·闵采尔、巴贝夫、邦纳罗蒂、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是我们的神圣的红旗,同时也是我们新联盟的标志;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我们的格言,伟大的街垒战是我们的口号,革命就是我们的战斗上的号角。
如同在一个饱经噩梦的漫漫长夜之后忽然觉醒一样,二月革命的愉快的消息欢欣鼓舞地袭击了我们,这个胜利的结果,即使是最热情的战士也未曾预料到的。由于意外的胜利突然到来,就错过了为实现那些已经受到承认的原则作好必要的措施,所以只能为下一次的战斗做些新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六月间,由于原则上的分歧发生了争论,这里面的激进分子分成两个营垒。经过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效果丰硕的四天街垒争夺战,向全世界表明了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即使是倾向君主主义的和倾向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联合的政党,也不能长久把它压制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势力的成功,一切反动的力量已经认识到有结成一个同盟的必要,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盟。
巴黎和维也纳的流血的街垒战,对于那些未来属于他们的党派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划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的原则,通过这场战斗,是更为必要了。
但是这种划分的必要性还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分子①还没有象在巴黎和部分地在维也纳那样普遍地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例如在柏林,并且部分地在维也纳,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计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那时候人们将不能从他们真正的利益出发受到教育,而将被日常的新闻和哗众取宠的空谈所包围。人们将会尊崇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的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卖弄口才,而其中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人们虽然可以因此保持在兴奋中,但是在这种兴奋里,人们的革命精神却逐渐地消失了。人们终将明白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们的行动并不能真正实现他们言论里所提出的那样光明的远景。
①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
这些人往往竟弄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不惜为取悦资产阶级而对群众去说教,而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却讳莫如深。其结果使群众处在徬徨焦虑的、旷日持久的不安状态和一种不可言喻的紧张混乱之中。人们听信他们的演说,不止一次地去参加他们所鼓动的示威集会,但总是发现这些人并不在场,或是偶而出现一下,就又用好听的辞句去平息人们原是在他们鼓动起来要干的事。即使不是这样,在他们所发动的那些示威运动里,对于那些还记得六月斗争的全部伟大英雄气概和场面的人来说,也根本没有丝毫值得兴奋的东西。那些最受欢迎的人民演说家,我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简直象个戏剧演员,如果有一天——维也纳失败的消息传来,柏林的一切有思想和有感情的民主主义者都充满了悲悼和愤激情绪的日子里——当着这样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就会听见这些演说家们在挤满了人的俱乐部里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因为本晚门口的收入偶然有余,谨向耶各比——为了他那真理的空谈——致敬而举行一次火炬游行。
我们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二月革命的伟大事件所感动。在宽敞的民主外衣遮掩下竟和那个从前的政党联合成了一个党,这个从前的政党是我们曾经和它斗争过的,而且它永远要保持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人们称它叫资产阶级也罢;称它叫民主主义也罢都是同样恰当的。
为这种合并而作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君主主义者在1848年11月里大胆而傲慢地要和民主资产阶级决斗,资产阶级吓得动也不敢动,他们听任他们的国民大会受迫害,听任弗兰格尔的军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不敢进行丝毫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市民保卫团在所谓维持秩序的借口下,却杀害了十几个手无寸铁的劳动者,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种胆怯懦弱的先例。在这个日子里就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柏林的左派和口技家们——其中五分之四是流亡的犹太人①,如果他们在自我牺牲上都能象他们演说一样杰出的话,该会把全欧洲都解放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等待着,想别人给他们从火中取出革命之栗。但是无产者却不再接受他们的嗾使去干这种事。无产者首先要看看国民大会和市民保卫团是不是敢站起来抵抗,因为打击本来是针对着他们的。无产者对于这两个集团的行动,从来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党,作为这样的一个党,对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它在事变发生之后,无论对于国民大会或是对于市民保卫团,只要他们的核心,他们的党不通过公开的参加抵抗的信号,那么,是不可能对他们抱什么同情的。
①魏特林并不是反犹太者。但是由于他的忌恨,特别是对马克思,并且一般地对于他所轻蔑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的忌恨,使他不由己地使用了反犹太的话语。
因此,我们同他们去搞统一行动是不会赚取到什么的。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幻想的盟友,在危难的日子里你是找不到他的,我们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所集合起来的群众,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把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样,群众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有更多的信心,在那里面会表现出更大的勇气。①
①在前面的几段里(第308页起)魏特林对他的革命理论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这个叙述表现出他对于1848年革命的性质和由于这种性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完全不理解。参看本书导言。
因此再不要谈什么和敌对分子的融合了。我们是人,是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一种理想,在这个理想里,社会的一切成员公平地、有秩序地共同分配生活上的劳动和享乐;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我们自己要为实现这种最高的社会理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我们甘愿同甘共苦,患难相扶。因此我们用这个名词来称呼我们的党是最好不过的。为了那些不完整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心灵感情上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的话——是根本不能真正激发起我们的热情的。但是没有热情我们就不能有勇敢、大胆的行动。因此,我的弟兄们!起来!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爱,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对我们的事业胜利的信心,这个事业是我们曾如此成功地保卫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