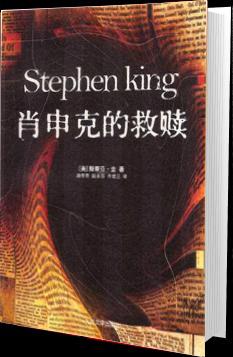丘克和盖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最后,近黄昏时,人和马都感到非常疲乏,赶车的伯伯说:“喏,马上就要到了!在那个小山坡后边转个弯。在那儿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就是他们勘探队的屋子……喂,喏——喏!……快跑!”
丘克和盖克高兴地发出尖叫,跳了起来,但是雪橇猛地一拉,他们又一起向干草上面倒了下去。
妈妈微笑着,揭去了毛绒头巾,只戴着她那顶毛茸茸的皮帽子。
转弯的地方到了。雪橇猛地一转,直向那矗立在一片小小的背风空地上的三座小屋驶去。
多奇怪啊!没有狗叫,也看不见人,烟囱里也没有烟冒出来。所有的小路都被厚厚的雪封住了,周围像冬天的墓地一般静寂。只有几只白腰的喜鹊无聊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去。
“你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来了?”妈妈惊慌地问着赶车的伯伯。“难道我们就是到这儿吗?”
“原来说好是什么地方我就送你们到什么地方,”赶车的伯伯答道, “这几所小屋子就叫做‘地质勘探队第三站’。那小柱上有标牌呢……念一下吧。也许,你们要去的是第四站吧? 那就得向另一边走上两百公里了。”
“不,不”妈妈向标牌看了一眼答道,“我们找的就是地质勘探队第三站,但是你瞧,门上挂着锁,台阶上积着雪,那些人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赶车的伯伯自己也觉得奇怪。“上星期我们还运粮食上这儿来的:面粉啦、洋葱啦、马铃薯啦。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队员是八个人,队长是第九个,连看守老伯伯一共是十个……这可用不着担心!难道他们还会被狼吃掉……你们等一下,我到看守老伯伯的屋里去看看。”
于是,赶车的伯伯丢下羊皮袄,大踏步地跨过雪堆,向最外边的那所小屋走去。
一会儿他回来了。
“屋里没有人,炉子倒是热的。那位看守老伯伯还在这儿,看来他是出外打猎去了。唔,晚上他一回来就能把一切告诉你们了。”
“可是他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妈妈叹了口气。 “我自己也看得出,这儿早已没有人了。”
“他会告诉你们一些什么我可不知道了,”赶车的伯伯答道,“他既然是看守人,总会告诉你们一些消息。”
他们费力地把雪橇驶近看守老伯伯屋子的台阶前,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从那儿通到树林里去。
他们走到穿堂里,在一些铁铲、扫帚,斧头和棍子旁边走过,又在一张冻硬了的,挂在铁钩上的熊皮旁边走过,然后走到屋里。赶车的伯伯跟着他们把东西搬了进来。
小屋子里很暖和。赶车的伯伯到外面去喂马,妈妈默默地给大受惊吓的孩子们脱去了外衣。
“到爸爸这里来,到爸爸这里来,现在到了这儿他却走了!”
妈妈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苦苦地想。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站里没有了人?现在又怎么办呢?乘车子回去吗?她身边的钱刚刚只够付给那个赶车的伯伯。那就是说,要等那位看守老伯伯回来。再过三个钟头赶车的伯伯就要回去了,如果那位看守老伯伯不是很快就回来呢?那时候又怎么办?你得明白,从这里到最近的火车站和电报局差不多有一百公里呐!
赶车的伯伯进来了,他向四面看一下,用鼻子嗅了嗅,走近了炉子,打开了炉门。
“看守老伯伯到晚上会回来的,”他安慰他们说, “这儿炉子里还放着一钵卷心菜汤哩。如果他出外很久,他就会把汤钵移到冷地方的……随你们怎么办好了,”赶车的伯伯出了一个主意, “事情既然这样,我也不是一根无情的木头,我可以不要钱把你们送回车站去。”
“不,”妈妈推却说,“我们回到车站也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在炉子上放好茶壶,浸暖了腊肠,吃喝起来。接着,当妈妈检点东西的时候,丘克和盖克就开始爬到暖和的炕上去。这儿散发出桦树帚、热烘烘的绵羊皮和松木刨花的气味。因为心绪恶劣的妈妈不做声,所以丘克和盖克也就不做声。可是很长久地不做声是不行的,由于没有事情做,丘克和盖克很快就睡熟了。
他们没有听见赶车的伯伯怎么离开,也没有听见妈妈怎样爬上炕来和他们并排躺下。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是一片漆黑。大家都是一下子醒过来的,因为门阶上传来了脚步声,接着穿堂里发出了哄响——大概是铁铲跌倒了。房门开了,看守老伯伯手里拿着一盏风灯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只毛茸茸的大狗。他从肩上卸下猎枪,把一只打死的野兔丢在长凳上面,然后把灯举向暖炕问道:
“这儿来了些什么样的客人啊?”
“我是这儿地质勘探队队长薛辽金的妻子,”妈妈从暖炕上跳下来说, “这是他的孩子,如果你需要,这儿还有证件。”
“他们就是证件:坐在暖炕上的这一对,”看守老伯伯喃喃地说,一面用灯照着丘克和盖克惊恐的脸。 “多像他们的爸爸啊——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尤其是这个小胖子。”他用手指把丘克戳了一下。
丘克和盖克都生了气:丘克是因为人家叫他小胖子;盖克呢,却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比丘克更像爸爸。
“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上这儿来?”看守老伯伯望着妈妈问道,“并没有叫你们上这儿来呀。”
“怎么没有叫我们来?是谁叫我们不要上这儿来?”
“就是没有叫你们来。是我亲自替薛辽金队长上电报局发出的电报。那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我队暂去大森林,缓两星期来。’薛辽金队长既然写过‘缓来’,那就是必须缓来,而你们却自作主张了。”
“什么样的电报?”妈妈问道。“我们什么电报也没有收到过。”于是,妈妈好像寻求支持似的,迷惑地向丘克和盖克望了一下。
在妈妈的注视下,丘克和盖克相互恐惧地瞪着眼睛,急急退到暖炕里边去。
“孩子们,”妈妈怀疑地看着两个小宝贝问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们收到过什么电报吗?”
暖炕上开始发出干燥的刨花和桦树帚的沙沙声。但是没有一声回答。
“回答我呀,淘气的家伙!”妈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们一定收到了电报,可是没有把它交给我是不是?”
又过去了几秒钟,然后从暖炕上发出了均匀而又和谐的号哭。丘克发出了又低又单调的哭声,盖克呢,却发出了比较尖细的、颤抖的哭声。
“真要命!”妈妈叫道,“真要把我送到坟墓里去了!好啦,别再拉你们的汽笛吧,把事情的经过好好说给我听。”
可是,丘克和盖克一听到妈妈要进坟墓,就哭得格外响亮了。过了好久,他们才互相抢着说话,一面毫不羞耻地把过错推诿给对方,一面把这不愉快的故事说了出来。
对这样的人,你能有什么办法?用棍子打他们一顿吗?把他们关到牢狱里去吗?铐上镣铐送去做苦工吗?不,妈妈决不会这样做。她叹了口气,叫一对小宝贝从暖炕上爬下来,擦净了鼻子,洗过脸,然后问看守老伯伯:她现在得怎么办才好。
看守老伯伯告诉她,勘探队接到紧急命令上阿尔卡拉希峡谷去了,回来至少得在十天之后。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度过这十天呢?”妈妈问:“你得知道,我们身边并没有带什么吃的啊。”
“你们就这样住着吧,”看守老伯伯答道,“我给你们面包,再把那只野兔送给你们——把它剥去毛皮煮熟好了。明天我得到大森林里去上两天,我要去检查一下兽阱。”
“这不行,”妈妈说,“我们怎么能孤零零地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我们都不熟识。这儿都是森林,还有野兽……”
“我把另一枝枪留给你们好啦,”看守老伯伯说,“棚下有木柴,小山坡的那一面有泉水。那边口袋里有麦片,罐里是盐。至于我呢——我对你老实说——可没有工夫照料你们……”
“这样凶的坏伯伯!”盖克低声说。“丘克,让我们跟他说说吧。”
“还说哩!”丘克说。“这样一来会把我们统统赶出屋子。你得等一等,等爸爸回来了,我们再把一切都告诉他。”
“爸爸又怎么样!爸爸回来还早哩……”
盖克走近了妈妈,坐在她的膝盖上,竖起眉毛狠狠地瞅着这粗暴的看守老伯伯的脸。
看守老伯伯脱去了短皮外套向桌子走去,凑近了灯光。到了这时候盖克才看清楚:原来那件短皮外套,从肩头经过背上,直到腰部,撕裂了一大块皮子。
“把卷心菜汤从炉子里拿出来,”看守老伯伯告诉妈妈,“那儿木架上有汤匙和碗,请坐下来吃吧。我还要缝补皮袄。”
“你是主人,”妈妈说,“你去拿汤请我们吃好了。把皮袄交给我吧:我会比你补得更好些。”
看守老伯伯抬眼来望妈妈,刚巧碰上了盖克恶狠狠的眼光。
“哈!你倒是个固执的小家伙,我看得出来,”看守老伯伯唠叨地说着,把皮袄交给妈妈,然后上木架那儿去拿碗碟。
“这是在哪儿撕成这个样子的?”丘克指着皮袄上面的破洞问道。
“我没有把熊对付好,因此它抓了我一把,看守老伯伯很不愿意地回答,把那钵满满的菜汤嘭的一声放在桌子上。
“听见吗,盖克?”当看守老伯伯走到穿堂里去时,丘克向盖克说。“他和熊打了架,一定的,他今天这样生气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盖克早已听到了一切。可是他不欢喜任何人来欺侮他的妈妈,即使那是一个能够和熊打架的人。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看守老伯伯就带上口袋,猎枪和狗,系上滑雪板滑到森林里去了。现在他们只能自己对付着过活了。他们大小三个一齐去取水。在小小的山坡后面,一道泉水从积雪的陡削的岩石中间流出来。泉水上面冒出浓密的蒸气,好像从茶壶里冒出来的一样;可是当盖克把手指放到泉水里去时,却觉得这水比冰还冷。
后来,他们拖来了木柴。妈妈不会生俄罗斯式的炉子,所以木柴好久没有燃着。可是一到炉子生着了以后,火焰却旺得使对面窗子上的厚冰很快就融化了。现在,从玻璃窗里望出去,可以看清楚整片树林的边缘、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喜鹊和青山的岩石重叠的山顶。
妈妈会给鸡开膛破肚,剥野兔皮却不行。她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来做这桩事情,那几乎可以剥好和剖开一整头公牛或是母牛。
盖克对于剥皮丝毫不感到兴趣,但丘克却很愿意帮妈妈的忙,因此他得到了野兔子的尾巴。那条野兔尾巴非常轻柔、蓬松,如果把它从暖炕上面往下一丢,就会缓缓地飘到地板上去,好像降落伞一般。
吃过饭,他们三个人一齐出去散步。
丘克劝妈妈带上猎枪或者至少带上几颗猎枪子弹,可是妈妈并没有带上猎枪。
相反的,妈妈故意把猎枪挂到高高的铁钩子上面去,然后站到小板凳上把枪弹塞到上面的那个木架上,并且警告丘克:如果他胆敢试试从架子上哪怕是拿走一颗枪弹,他就不用想过好日子。
丘克顿时满脸通红,急急忙忙地逃了开去,原来已经有一颗枪弹放在他的衣袋里了。
多么奇妙的一次散步啊!他们像鹅一般地排成单行,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向泉水走去。寒冷的、淡蓝色的天空,在他们头顶上面发出光辉,青山顶上尖尖的岩石,好像神话里城堡的尖塔一样,直向空中伸去。好奇的喜鹊,在寒天的沉寂气氛中尖声地喳喳叫着。灵活的灰色松鼠,在浓密的柏树枝中间敏捷地窜来窜去。在树下柔软的白雪上面,印上了陌生鸟兽的奇异脚迹。
突然,大森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发出了呻吟、轰响和折裂声。那大概是树顶上的结成冰的大雪块,一边压裂着树枝一边在往下掉。
以前盖克住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以为整个世界就是由莫斯科的一切组成的,也就是由莫斯科的街道。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公共汽车组成的。
现在他又觉得;全世界是由一片又高又稠密的树林组成的了。
总而言之,如果太阳照在盖克头上,他就会相信世界上是没有雨和乌云的。
如果他自己很快乐,那么他就会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也都很高兴,很快乐。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又开始了。那位看守老伯伯还是没有从树林里回来,于是恐慌笼罩了这所盖上了雪的小屋子。
尤其是在黄昏和夜里,格外使人害怕。为了不让灯光招来野兽,他们牢牢地关上了穿堂门和房门,又用粗席严密地遮住了窗子;其实,应该完全相反地做,因为野兽不是人,它们倒是害怕火光的。风呢,恰好又在烟囱里吼叫。当大风雪用尖利的夹雪的小冰屑敲打着墙壁和窗子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有什么在外面推着,搔扒着似的。他们爬上暖炕去睡觉,妈妈给他们讲着各种故事和童话,讲了很久。最后,妈妈开始打瞌睡了。
“丘克,”盖克问道,“为什么魔法师只在各种故事和童话里才有?如果真的有魔法师,那会怎么样?”
“连妖巫和鬼怪也真的有吗?”丘克问。
“不!”盖克厌恶地挥了挥手,“不要鬼怪。他们有什么用处?如果有魔法师,我们就可以请他飞到爸爸那儿,叫他告诉爸爸,说我们早已到了这儿。”
“可是他凭什么东西飞呢,盖克?”
“唔,凭什么……只要挥动两手或者随便怎么样一来,这个他自己知道。”
“现在挥动两手是很冷的,”丘克说,“你看我戴着多好的手套和无指手套;即使是这样,当我拿木柴时,手指还是冻僵了。”
“不,丘克,你倒说说看,有魔法师不是很好吗?”
“我不知道,”丘克可打不定主意了,“你记得吗,在我们的院子里,米奇加住的那间地下室里,从前不是住过一个跛子吗?有时候他卖面包圈,有时候就有各色各样的女人和老太婆来看他,他就给她们算命:谁的命运好,谁的命运不好。”
“他算命算得很准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后来人民警察把他抓走了。从他的房间里,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