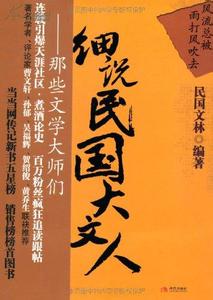文人做官-龙应台-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一刻钟,没有半途而废。因为中间可能半途而废,或者譬如说在议会你受到侮辱的时候,你甩袖而去,这是最简单做出来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发生,或者是说在府内你对于那个原有的官僚的机器,你跟他有所抗衡,而后说我不干了,那么官章又放下走了,这也很可能,很容易发生。但是那种决然而去,我觉得都是遗憾。而且呢,我也会担心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文人作家进入到官僚的机器里头去实践,我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个到最后一个评语说,你看吧,能批评的人不能做事,你看吧,知识分子他就是熬不过。
主持人:百无一用是书生。
龙:我是不是要当这个例子?所以到最后真的做完了走的时候,一方面是非常深的感恩,就是说完全不是我龙应台多么了不起,而是台北的文化人如此的温柔敦厚地帮我走过,是集体的合作,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够做到最后一天真的太感谢了。
主持人:这是不是您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明,就是说龙应台作为文人我可以当官,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龙:这种话不能自己来说。
主持人:是,我说。
龙:其实当然它客观上是证明了说你以为是只会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就绝对不能做事,不见得。有人做了,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更高的程度证明了说,在台北它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发展阶段,到了一个阶段它已经第一个,它的体制竟然能够容许这样一个性格的知识分子进去工作。然后也正式地说它这个城市已经发展到它的文化人,文化人平常是每个人都是头角峥嵘、文人相轻的。但是他可以为了这个城市的将来的共同的远景而共同地来扶持一个文化人做事,所以它更高的程度不是证明了龙应台这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而是证明了这一个城市,在20世纪21世纪交接的这个阶段里头,这个城市成熟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更大地证明了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体制。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觉得过就是说在任内自己的这种率性而为的文人个性和政治利益有过相冲突的时候?
龙:冲突很多,每天都面临这个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冲突是使得我必须折损我最核心的文化的信念,因为从一开始进去我就知道说,我想法是我一定要弯腰。因为你为了城市的大的建设,而且文人不能够有一种傲慢,我在一个市区政府的体系里头,警察局部门怎么说,卫生部门是怎么说,都市发展的规划的部门怎么说,交通的部门怎么说,我文人不可以有一种傲慢说,我说的算数。你进去之后,政治一定是一种协调的艺术,我设法来了解你这个规划工程部门怎么想?然后我要试图,如果我认为我的古籍的保存,比你开这条路要重要的话,我不能够用文化至上来说,我说的算数,你凭什么?所以我必须先了解它的需要,然后用他们听得懂,而且接受的语言,把我的文化的思维传输过去,所以这个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协调,也需要很多的弯腰。
主持人:这您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文人的性情,去附和政治的游戏?
龙:我一点都不觉得,不。我觉得这个是文人必须有的谦虚,而且弯腰是绝对必要的。在做政治妥协的时候,但是脊椎不能弯,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三年之中,我没有中途而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是我的核心的理念,就是说我的脊椎骨必须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可以完,可以做到结束。
主持人:那当初就是说您自己给自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或者说理念,如果说遇到了让我脊椎弯的事情。
龙:我就走,那一定走。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那样的话,就是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您现在还那么认为吗?是玩笑话,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龙:当初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玩笑话,而且也是自我嘲讽的那个环境之下讲的话。但是当这一句话被挑出来印出来,那么那个环境那个自我嘲讽的环境就不见了,就剩下这一句话了,孤零零一句话,那你也不可能有机会去解释。那我也不在乎。但是对于鲁迅先生,我的看法到今天还是我觉得他的小说短篇小说是一流的,绝对地好。那他的杂文呢,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然会觉得,他的杂文就是说尖酸刻薄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的杂文也是比较是针对眼前的现实做的立即的反映,跟我自己的杂文当然后来就是不同,完全不同路了。就是说我是尽量地避免尖酸刻薄的这一个性质,但是,因此当时在说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我觉得杂文是可以谑而不谑,是可以尖锐而不刻薄,是可以同时针砭现实,但是又有历史的纵深,这是我自己对最好的杂文的要求。
主持人:就是您自己的杂文风格上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比如像我感觉,读您《野火集》的时候,我自己就明显地感觉到,好像还是有鲁迅杂文的风格在里面。那么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受过鲁迅杂文的影响?
龙: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那答案是完全没有。原因是鲁迅的书在台湾是完全是禁止的,那么在我读书的过程里头,从来就没有读过鲁迅的东西。一直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要到是非常晚了,恐怕就是都到了写《野火集》之后,因为很多人提到说跟鲁迅的关系,我才特别去把鲁迅的东西拿来看。那么当然这个跟我在我是南部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小孩有关,在台北读大学的话,你这个地下流传的书可能还看到一点点的鲁迅。我在南部比较闭塞的乡下,就是完全不知道鲁迅的作品,所以这中间影响完全是没有的。
主持人:因为大陆读者看鲁迅的杂文是很多了,而且接受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最开始的时候,您的《野火集》到大陆来,也是遍地烧野火,买这个书都非常难,令一时洛阳纸贵。那么大陆当时有些学者,就觉得这是台湾的女鲁迅。
龙:那么这是历史的偶然了。
主持人:那么在思想上,比如说对待国民性的批判,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您和鲁迅是不期地有这个共通性,文风上并没有说去受他什么影响。
龙:对,完全没有。就是说写野火的时候,恐怕都还没看过鲁迅,如果说文风上有任何的相似的话,那就是完全的巧合。可是呢,我们批评的东西有相似的批评的对象。这只不过显示就是说这个历史常常重复自己。我们现在批判的东西你回头去看,这个胡适的时代批评过,你再往前看,梁启超的时代批评过,你再往前看,恐怕龚自珍也批评过,所以就是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每一次就是以不同的语言来表达。
主持人:鲁迅是历来把杂文当成匕首和投枪,那么您从《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到《百年思索》《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心态文风上有很多的变化。您开始曾经讲过就是写出了《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是因为当时自己的一种天真,率性的天真,那么后来的这些成熟,有没有把当初这个率性的天真消失掉,或者说减弱了?
龙:我觉得两者不可全。野火它当时是绝对的天真写出来的东西,如果说当时就知道一个现象后面的所有的拐弯抹角的黑暗的东西的话,而且你如果知道说里头多少人做过尝试,去改革,然后那些人都是头破血流,或者是就关在监狱里头去,如果这些全部都知道的话,你就不要去写了,你不可能写。因为你不知道就是初生之犊真的是不知道这种事情,你才会去写。那《野火集》其实它的特色不是在于它批评什么东西,其实主要是在它的文字,因为你批评同样的现象不是没有,只不过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去表达它,《野火集》的文字是煽动性很高的。所以它当时的危险性也在这里,是跟天真有关。可是你说,后来的文字譬如说《百年思索》,你看中间有十五年的距离,那么《百年思索》跟野火差距非常非常大了,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是百年思索跟天真还是有关系,否则也不会去写。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的存在的。
主持人:是肯定存在。就是比如说作为大陆读者来说,您给他们造成这种思想上的冲击,肯定更多的是来自那种具有煽动性的,天真或者很狂放的那种《野火集》,对《百年思索》呢,可能就要弱了许多。就是作为读者来说,这个困惑就在于好像说龙应台在文学上的变化,可能对她自己来说是个得,而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个失。比如说到了《百年思索》,他可能觉着当初您的那种天真减弱了。
龙:那是跟现实状况的关系,就是有很多大陆的读者他会觉得他所看到的问题,他希望龙应台再写像野火集那样有煽动力的,而且是有撞击力。
主持人:对,就大陆读者恨不得您永远写野火集。
龙:对,没有错,我也知道。
主持人:就是大陆的读者比如说包括我来说,所接受的那种约定俗成的一种杂文的社会共有的观念,好像还是喜欢正视淋漓的现实。譬如像鲁迅先生那种一个也不可饶恕的那么一种杂文的写作的方法和观念,那么您觉得杂文好的标准在哪儿?它是不可宽恕呢?还是要保留一些余地?或者说像您现在这样,我感觉是向历史哲学的纵深去发展。
龙:恐怕都不是这样的。而是我自己心目中好的杂文第一个是它的文字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只是牢骚的发表,跟发泄的话,才能够进入文学的这个水准里头去,进入这个文学水准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你不要给我任何的借口,说是里头讲的东西多么透彻,或者是这个事情多么重要,或者是它的个性抒发多么厉害,你先告诉我,你这个文字有没有到达艺术的水准,我第一个要求是文字。
主持人: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看你的本事大小,关键还是看文字。
龙:关键是文字,其他全部都是借口。先看文字,那然后呢,要看说,你对于事情的看法的深刻与否,我觉得就是这两件东西的,没有别的,其他都是假的。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觉得譬如说作为杂文的这种对社会现象和阐述自己文化观念的犀利锋芒上的表现,会随着文学的这种边缘化,有所减弱?或者也变得边缘化,而无足轻重了呢?
龙:杂文是跟社会现实关系比较紧密的。在台湾这种批评性的,批判性的野火式的杂文,野火被称为说是台湾批判杂文的滥觞一个开始。但是今天像《野火集》这样的杂文在台湾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很多人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作家在写了。因为他的社会民主了之后呢,每天的社论,每天的报纸这变成是记者在写的东西,那么记者写的东西,就不是文学的东西了。那么杂文那种批判现实的那个功能已经被民主的譬如说议会所担负了,被民主正常的管道被报纸所担负了,所以文学里头对于现实的批判这个东西,就相对减弱了。因为没有那个需要了。(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