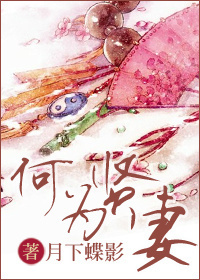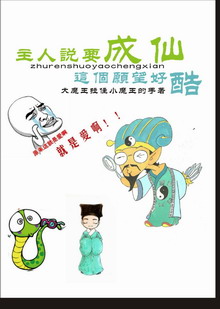主人何为言少钱-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风一阵总吹来。
早知今日都狼藉,
何不留将次第开?
正是道出了月桂怒开怒放的干脆,虽谢得凄凉,却开得漂亮。
可越微人独爱宋之问《灵隐寺》中的那一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它虽是写的桂花,但却被他认为是对桂花糕最妙的赞美。
其实深究起来,他爱吃桂花糕也许并非是因为桂花糕的美味,而是因了一份“求而不得”的执着。越微人是一个人,纵使再如何天纵奇才、旷绝古今,他也只是个凡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无所不能,而他的无能就在于这一块小小的桂花糕。
抚养燕少千的十多年,除了练剑,他从未强迫燕少千干过任何她不愿意做的事。燕少千是个懒人,因此,也就成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祖宗,而过去令江湖人士闻风丧胆的“修罗刀”、现在让绿林豪侠心惊胆战的“红袍客”在年年岁岁的历练下,化作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万能师父。
他可剪刀细裁罗叶裙,也可为扫洒门庭、侍弄娇花;他甚至可化腐朽为神奇,将鄙陋粗食化作满汉全席,却独独做不了那道简单容易的“桂花糕”。
上天就是这样“赐予”了这个完美的男人一点小小的瑕疵,诚然越微人尝试过千遍万遍,却真是从未成功过,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沾染了太多杀孽的手,触不得那样晶莹剔透的物件儿。”
那一日的天气格外闷热,他就那样冷冷地自嘲着,窗外的云也被这样的寒意定住了身,年幼的燕少千就这样看到了全然不似平日的越微人,那样一种深深的自我厌弃,扼地她喘不过气来。
于是,她开始学做桂花糕。淘洗干净的江米摸在手里有些细腻温良的感触,碾成粉末的芝麻散发出浓郁的芬芳,还有那新开的月桂金黄的,有一种甜蜜到让人沉溺的香味。
一次又一次,终于赶在越微人生辰之前学会,半寸厚的梅花状桂花糕,盛在白底的冰裂瓷盘里越发的透亮可人。
燕少千永远也忘不了他看到那碟点心时的样子,细长的凤眼里,冰封的腊月河一下转成了明媚的碧湖水,粼粼的波光映着那夜的明月,碎了天上云辉。
那时,他小心地拿起一块,小心地咬下一口,凉凉的桂花糕刺激了他的味蕾,眼泪就这样流下来,直直的坠成一条线,晃了燕少千的眼,也晃了燕少千的心。
人人都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却终是忘了后一句:“只是未到伤心处。”
八月十六的月亮本是最圆,却因了他的明珠泪而缺了半边……
今夜,本是残月凉如水,越微人依旧是小心地拿起了一块,依旧是小心地咬下一口,凉凉的桂花糕依旧刺激了他的味蕾,但笑容忍不住浮上来,他的少千还是老样子,依旧能做出让人感到幸福的桂花糕,依旧像个孩子,聪慧也诡黠。
昭德殿。
鸽子早就飞走了,寂静的宫殿里越发显得空旷寥落,燕礼恭手握着捏成团的条子,阖了眼,靠在了那张人人眼红的龙椅上。他在等人,等一个妓院的老板。
宫门未被打开,一道黑影就飘然坠地,是个男人,一个极美的男人,单就这样恭敬地跪着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妖娆之气,“闻人辛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挥了挥手,示意他平身,燕礼恭冷冷地问道:“怎么回事,你也会把人跟丢了?”
“到了烨州境内,便有人出来阻拦,像是天枢阁的人。”没有畏惧,简单地陈述了事实。
“辛,不要让我失望。”年轻的声音里没有感情,唯剩迫人的压力。
闻人辛见惯了他那副样子,款步上前,“我似乎还没有教你失望过。”冷冷的勾起唇角,绽出一个罂粟般惑人的笑,“燕肆湖那边也会叫你满意的。”
“但愿。”再睁开眼时,寂静的昭德殿里依然空旷寥落,仿佛从未有人出现过。
“李桓,摆驾锦淑宫。”走出昭德殿,对身边的总管吩咐道,今晚应是轮到淑妃了。
内廷总管太监特有的尖细嗓音响起,一帮众人簇拥着年轻的帝王向锦淑宫行进。
深夜肃王府,世子房内来了贵客,是个男人,一个极美的男人,慵懒地倚坐在床边都透出万种风情。
“驰远,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幽都吗?”他教燕肆湖太过吃惊。
“想你了呗,来看看你不行吗?”故作娇态的男人竟不显矫情,反倒生出几分令人我见犹怜的楚楚动人。
“你来的怕不是时候。”时下暗流汹涌,燕肆湖有些担心道。
“放心,我待会儿就走,来告诉你件事,烨州是天枢阁的总坛。”
“什么?”那儿原是慕华山庄的地盘啊。
“你没听错,我走了。”话音刚落,黑影一闪,屋内只剩燕肆湖一人。
第二天,牡丹巷七十二家烟花会馆都炸了锅,因为,“长安第一楼”的花魁,不见了!
第十三章 梅花烙
慌了神的鸨母就这样直挺挺地站在身侧,闻人辛吹了吹茶盏里浮着的叶儿,轻抿了一口,又慢悠悠地放下了,“黛姬逃了?”妖冶的双眸里满是玩味的神色,倒不见什么吃惊或着急。
怎么会吃惊呢?他一路跟着那两人出了长安,直到进了烨州才失了那两人的踪影。至于着急,那就不好说了。急也急不来,不过,那两人这么一走倒也未必尽是坏事。
先前他费尽心思却什么都没查到,要说这两人是因为太过平常而没有消息,那是任谁也不会信的,哪个寻常人甩下一百万两银票眼都不眨?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人背景太过强大,以致皇家暗卫的眼线也是触及不到。
他们这一走看似失了线索,可也多了条线索,至少,现在他闻人辛就知道了三条至关重要的信息:其一,近年来神秘崛起的天枢阁总坛在烨州;其二,那两人与天枢阁关系匪浅;其三,那女子定然是肃王骨血无疑,否则,为何肃王一回朝,他们就离了长安?
闻人辛知道这些不代表眼前的鸨母也知道这些,看那惶惶不安的样子定是吓得不轻,这可不是什么小事,虽比不得庙堂之上你争我夺,可就一家妓院而言,失了头牌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
“罢了,原就是没签卖身契的自由身,走了便走了吧,好歹先前还留了一百万两银票,闻人楼也不亏。”岂止是不亏,暗卫这边倒是真赚到了,不然他上哪儿去找一个肃王千金?
眼见着自家主子半分怒气都没有,鸨母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但还是有些忐忑的,实在是没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闻人楼好歹是“长安第一楼”,想进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可那丫头硬是没头没脑地如了愿,自家主子是想也没想就留下了她,还严令自己不可透露半点风声,连卖身契都没签。也不好签,人家那银子不见得比自家主子少。可留着这样的人在眼皮底下,究竟是为什么呢?
再说现下,招呼不打一声,两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主子竟也不怪罪,还像得了便宜似的,她是越发地觉得高位者心思的难辨了。
待那鸨母退下,闻人辛突然忆起九门提督搜查那天出现的女子,他自是知道那是有人假冒,也知道那人必是与黛姬一同的琴师,但那琴师原本是没那种夺人之色的。见过许多次,只觉得长得极其俊美,却并不如当日在暗处看到的那般艳光四射,尤其是左额上的花锱,真真是赤红似血、灿然欲滴,竟不像贴上去的,反倒像是原就生在脸上一般!
原就生在脸上!
这六个字如惊雷一般在闻人辛脑中炸开来,震得他浑身一颤。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总将额发垂着,怪不得那张俊美的脸在笑起来的时候左额总令人觉得那么不自然。想他闻人辛浸淫易容术经年,竟没想到这一层。
初时,燕少千和越微人才到闻人楼,闻人辛就暗中窥探过多次,几经确认方才肯定二人没有易容,想来也是,有不可估量的背景,也没有什么易容的必要。可万万没有料到,容是易了的,只不过是仅易了左额上那一块!
那斜斜的梅花枝就这么生在脸上,是何等样的别致,再加上那样出色的琴艺,除了江湖上风闻已久的“红袍客”,还能是谁?
如此,那女子岂非正是“墨衣剑”?肃王的千金是“墨衣剑”,这也太教人难以置信了吧。
“碧玉箫,梅花烙,赤柴旧琴连广袖,冷艳红袍客。”闻人辛缓缓地念出这十八个字,字字句句总都是玩味,“红袍客与天枢阁,呵,有意思。”
明明是正午光景,艳阳当空,太傅府中看书的韩家三公子却突然打了个寒战,然后就听得下人回报,“三少爷,礼部杜侍郎求见。”
未待韩若鲤应声,杜涵川便急急地闯了进来,张口就是那一句:“黛姬不见了!”
韩若鲤先是一愣,再是一惊,半晌没出说一个字,杜涵川以为他是惊得说不出话来,刚想出声宽慰,却见韩三公子忽的笑了。
“你个呆子,莫不是惊得傻了,笑个什么劲儿?”杜涵川纳闷儿了。
“佛曰,不可说。”
那洋洋的得意之色衬得那英气勃发的脸满是顽皮,好不天真可爱,杜涵川真是觉得他被惊得傻了。“唉,你别吓我,我只是来告诉你这个被韩老头禁足的呆子,黛姬不见了,你别真给我傻了。”
“我好得很!”你才傻了呢,懒得理你。回了这句话,韩若鲤就作势要走。
杜涵川却不言语了,两眼死死地盯着韩若鲤,仿佛生生地要在他身上灼出两个洞来。很显然,韩若鲤那四个字激怒了他。
见他如此,韩若鲤也觉出方才失言了,再怎样这样拂人心意颜面的话说出来都是不该的,便开口道:“你不用担心,黛姬不会有事的,就凭她手上的扶风剑,别人就伤不得她分毫。”
杜涵川依然不言语,韩若鲤继续道:“你也清楚的吧,她那模样少说跟肃王有七分相像,留在这长安未必是好事,如今不见了倒该庆幸了。”
明白这是韩若鲤再给自己台阶下,杜涵川的脸色也软了下来,“这只是其一。”
“什么意思?”韩若鲤不解。
“还记得黛姬的琴师吗?”杜涵川压低了声音,谨慎问道。
“没见过,他每次都在帘子后边儿,不过琴技是相当了得。”韩若鲤如实以告。
“今日,我听闻人楼的良宵姑娘说起他。”那良宵也是闻人楼的琴师,亦是住在远心小筑,只那人住在最里头,别人平日是决计见不到的,只她偶然间瞥过一眼。“她说那人生的一副绝好的皮囊。”
“那又如何?”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韩若鲤依然不解。
“你可曾听说九门提督搜城的事儿?”
“听过。”
“可是有人说花魁黛姬修长高挑、凌厉逼人、美艳不可方物,远胜当年闻人楼第一人孟燃嫣?”
“是。”对啊,韩若鲤一下子明白过来。黛姬他是见过的,说修长高挑、凌厉逼人是恰如其分,说美艳不可方物却是明摆着睁眼说瞎话了。
“当时,良宵刚巧走过,就站在满庭芳门边,也是第一次见到黛姬,就她所言,黛姬与那琴师身形面貌几乎无二,只左额上多了一枝梅花烙。旁人离得远,恐是以为那是贴上去的花锱,她靠的极近,却知道那就是生在面上的胎记。”这一番话说完,杜涵川看了看若有所思的韩若鲤,知道他是和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
沉吟半响,韩若鲤开口了,“你的意思是,那晚众人见到的是那个琴师?而且是原本易容,现下以真面目示人的琴师?”
“不错。你不觉得他像是江湖传说中的一个人吗?”杜涵川再次提醒。
“传说中的一个人?”传说中的人有必要到烟花之地做娼家男子吗?可黛姬不也是如此吗,身怀绝世武功却甘心在闻人楼挂牌。念及黛姬的剑法,韩若鲤觉得有什么在脑中一闪而过,正当此时,听得杜涵川朗声念道:“碧玉箫,梅花烙,赤柴旧琴连广袖,冷艳红袍客。紫金钗,莲花印,天蚕华锦束柳腰,绝傲墨衣剑。”
“听过这首词吧,从三年前开始传唱至今,你就是再怎么书呆子,兵部侍郎做了那么久,江湖的事也该知道一些吧。”
显而易见的真相,但韩若鲤就是不敢将那两人的名字说出口,他的手在抖,鼻尖上隐约可见细细的汗珠,他在怕,他怕这真相一旦被自己点破,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头。
杜涵川的话也止住了,他原也是在怕,想来想去还是惶然不安,又找不到可以说的人,父亲那里显然是说不得的,也只有眼前这呆子是个实诚人,这才急急地赶过来。可话说到这里就算止住了,那以后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
韩若鲤见平日对诸事都不甚用心的杜涵川也是一副眉头紧蹙的样子,突然心一横,终是要说的,只是个早晚而已,索性就将这层窗户纸捅破吧,日后的事日后再说,“红袍客越微人和墨衣剑燕少千,对不对?江湖和朝廷,对不对?”
“对。”杜涵川唯有一字以应,那人可是肃王的骨血,肃王是朝廷的人,她是江湖的客,这中间隔的何止是几城几镇,那可是整个天下啊!眼前虽看不出什么,将来势必要起些风雨的。再说肃王拥兵自重,皇上要罢他是迟早的事,只愿别将那人卷进来。
第十四章 恨离别
过了暮春天气,留连戏蝶也飞不了几日,自在娇莺更是啼不了几声,转眼就到了梅子黄时,天气闷热自是不消说的,然,更教人头疼的却是连绵不绝的雨意。
近日,连天阴雨,燕少千站在取元轩门口已是等了许久,却依旧丝毫不见那丝一般的雨线有断的意思,整片慕华七十二峰都蒙在这样的湿意里,有种难以明了的迷茫。
长安城里此时亦是濡湿一片,整日里巷口街道都难见几个人影,就是见到,也都是执伞而行,匆匆忙忙。
那乾元殿里阴霾压顶,堂下的诸位是大气都不敢出的,綦江水患,恐有改道之危,这也就罢了,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西北却又大旱,幽都尤为严重,此为天灾。自古,人不与天斗,如今旱涝双至,更是杀得朝臣措手不及。
可是,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