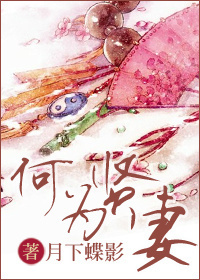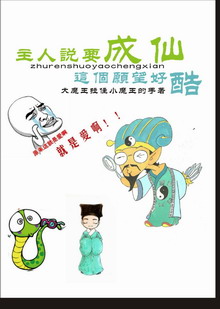主人何为言少钱-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诸位栋梁之才不敢发声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月氏国大军压境、兵临幽都城下!
“众卿可有话说?”燕礼恭冰冷的声音从殿上传来,没有一丝变化与波动,让底下站着的众人冷汗直冒。
“怎么,我泱泱大暨朝所谓的人才济济就是如此吗?”缓缓的语调,甚至还带着几分调笑的意味,却仿佛吐着信子的毒蛇,直直的钻入人的耳,舔舐着人的心。
“陛下息怒,微臣以为綦江上下自古富庶,缓些时日应该不成问题。反倒是羌幽十三州应先予以赈款。”户部侍郎苏平虽面露惶恐,但还是出列禀奏,毕竟出赈款的事最后还是落在户部头上。
“哦?那爱卿缘何如此以为啊?”燕礼恭问得很是温柔,可听在苏平耳里又是另一番滋味。
“回禀陛下,且不说幽都乃我大暨西北门户,必不能失,月氏兵临城下实乃打的乘虚而入的算盘。”一句话说完,苏平略微抬了抬头,约摸在打量燕礼恭的脸色,还未看清就听得一句:“说下去。”
声音不似方才那般冰冷,反而低沉了几许,苏平那颗高悬的心稍稍定了些:“西北久旱未雨,若久不得赈济,灾民暴动,那时幽都内忧外患,加之肃王如今身在京城,军中无人坐镇,军心必乱,届时月氏更是有恃无恐……”
苏平还欲继续,但燕礼恭止住了他,问了一个不太相干的问题:“爱卿以为朕所设的西北兵马总督许驰远如何?”那声线刻意地压低了,掺杂着玩味与示威。
苏平刚想回答,杜涵川就抢先道:“许总督雄才伟略、惊才绝艳,有他坐镇幽都,月氏国应暂时不敢轻举妄动。”顿了一下,杜涵川道:“陛下恕罪,微臣方才僭越了。”
仅是那一句,苏平回味过来才惊觉自己方才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皇帝与肃王貌合神离,对肃王手中的羌幽七十万大军更是忌惮非常,自己那一句“肃王如今身在京城,军中无人坐镇,军心必乱”正是戳中了皇帝的痛处,若不是杜涵川出来插一句,后果怕是不堪设想,遂感激地投去一眼,杜涵川也不甚在意。
谁人不知许家正如日中天,深得皇帝宠信,许家的这个养子更是备受皇帝青睐,三年前,区区二十五岁的年纪就官拜西北兵马总督,统辖一方军政。
其实,众人又岂会不知皇帝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不过就是将自家亲信派去幽都,一来监控肃王,以便随时掌控羌幽十三州;二来牵制肃王,兵权一分为二,肃王再怎样也不至于一手遮天,就算将来真的反了,也不可能毫无顾忌。
这边,燕礼恭沉吟片刻,道:“着户部先将綦江所需的银子拨了,幽都、月氏的事容后再议,退朝。”旨意下得甚是干脆,以致一干众人还未回过神,皇帝明黄色的身影已消失在乾元殿的阴霾里。
是夜,闻人辛又来了昭德殿,却没再跪着。
“陛下,今日早朝之举甚为不妥。”那美丽的男人认真起来连话都咄咄逼人了几分。
“如何不妥?”燕礼恭懒懒地倚在龙椅上,虽是闭着双眼,可也有三分戾气。
“事分轻重缓急,切不可因小失大,陛下若想借月氏之手除了肃王的七十万大军,那就大大的错了!”闻人辛对着燕礼此时竟是恭声色俱厉。
“如何错了?”依旧不为所动。
“月氏若是开了幽州这道门,将来势必步步为营,要吞掉大暨也未可知,陛下莫要姑息养奸、养虎为患!”
“肃王、月氏哪个不是虎?养哪只又有什么区别。”越发的漫不经心起来。
“陛下的意思是要我将那羌幽十三州拱手相让于月氏?那直说岂不更好?”闻人辛怒极反笑。
“你可知羌幽十三州每年上缴的赋税是多少?”燕礼恭忽的睁了眼,侧过头盯着闻人辛。那双琥珀色的双眼就这么直直地将眼光射过来,看得闻人辛一愣。
见他不答,燕礼恭又问:“那你可知羌幽十三州的七十万大军每年要耗掉我大暨多少军饷?”平日里或冰冷、或温柔、或不为所动、或漫不经心的声音此时提高了七分,带着质问,如刀一般。
不待闻人辛回答,燕礼恭又道:“西北之地,难生寸草,几无人烟,年年大旱,朕要这一块吸朕血的不毛之地做什么?让月氏虎视眈眈?让肃王拥兵自重?让国库日渐空虚?还是让綦江方圆三千里良田惨遭水漫?”
一连四个反问,饶是七窍玲珑如闻人辛也不知如何作答,然,也只是片刻,他便答:“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大暨可衰,不可没。弃羌幽十三州于不顾,或许可甩掉一个大包袱,或许可趁机罢了肃王,又或许可解綦江燃眉之急,可陛下忘了,饮鸩止渴,尤胜自缢!此举伤的怕不是肃王,而是寒了大暨千千万万子民的心!”
一句“寒了大暨千千万万子民的心”教燕礼恭惶然了,当年,先皇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以致大暨盛世一去不复返,究其根本便是“寒了大暨千千万万子民的心”这几个字了。
燕礼恭即位五年,分权制衡、任用贤能、广招寒士,好容易才将天下士子的心拴在天子门下,其中艰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足道其万一,如今却真要为那羌幽十三州重又失了人心吗?
见他有所犹豫,闻人辛知他已明了其中厉害,郑重下跪:“陛下,若说从前,幽都有肃王,微臣在那儿挂的是个闲职,说白了,也就只是您的暗卫长,暗中来去尚可。如今,微臣却真是要去做您的西北兵马总督了,您且看着,看微臣如何为您守住羌幽十三州,保住那七十万大军并让其为您所用!”
这一番话不长,百字不到,却震了燕礼恭的神,撼了燕礼恭的心。闻人辛从来轻佻妖娆,就算是面对他也是不改肆恣之意,甚少以“微臣”自居,也不曾进过什么谏言,今日如此慎重庄谨,想是已做了死在幽都的准备。
想到那样一种几乎是必然的结局,燕礼恭动容,闻人辛见他如是,忽又变得不正经了,仪态万方地起身,款款行来,待到站在燕礼恭面前,呢喃低语道:“陛下这是舍不得辛了吗?那也不枉辛十年来为您奔波劳累。”
“是啊,舍不得辛了啊。想朕第一次见辛时,辛便是这般在朕耳边低语,那调调竟不像是为太子尽忠,反倒更像是对情人的海誓山盟呢。”不知何故,燕礼恭不自主地吐了真言。
他依稀记得,那个十八岁的美丽少年,妖娆多姿地站在他面前,没有敬畏、没有恐惧,只是真心实意又轻浮放荡地对他说:“我是闻人楼这一代的楼主,以后愿为您出生入死。”然后挑逗般的一笑:“希望您不要嫌弃呢。”那样的旖旎艳丽,现在都忘不掉。
许是当时嫉妒他的无忌,便赐了他一个“辛”字,似是诅咒他一世如自己一般艰辛。他当时却是很乐意,“辛,心啊,殿下是要辛陪着您一起艰辛吗?”那样大胆放肆的言谈,自他嘴里所出来甚是惊心动魄。
怎么会不知道呢,沉迷龙阳之好的闻人辛对自己是存的什么心思,燕礼恭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也只有这样的辛才愿意为自己出生入死,也只有这样的辛才愿意为自己远赴幽都做许家的许驰远、西北的兵马总督,也只有这样,他才敢将这重若千斤的虎符交到辛的手里。做帝王的每一点都要好好利用,一点都浪费不得。
闻人辛每次被召见的时候,燕礼恭都或眯着眼、或闭着眼,他自己不知这是为了什么,只是不愿见到这个对自己存了龌龊心思的臣子,可闻人辛却是知道的:他在怕,利用别人的真心,就算阴狠如他,也是有愧的吧。
不过,今日得他一句:“是啊,舍不得辛了啊。”闻人辛却觉得死恐怕也是值的。
只是,就算死,死的也只是许家的义子许驰远,却不是那人的闻人辛……
后半夜,长安城门开了又合,一骑如飞,奔向西北。
第十五章 尘世羁
近日来越微人很忙,比之前在闻人楼的最后几日还要忙,但他忙得很安心,因为在慕华山庄燕少千绝对安全,他忙得可谓是毫无后顾之忧。
可燕少千截然相反,她很闲,比之前任何一天还要闲。人大多如此,从未见识过花花世界倒还能心如止水,可一旦尝到了其中千般滋味便会觉得原来的生活是如水般寡淡。
这一点在燕少千身上已得到充分验证,虽说她对那滚滚红尘也无什留恋,可毕竟是年少心性,怎耐得住这样的百无聊赖?
一个人一旦无聊,若找到新的事物可以转移注意,那也好办,之后最多便是引发新一轮的狂热。可若是找不到新的事物可以转移注意,那就不好办了,其中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胡思乱想。
纨绔子弟可想寻欢作乐之新法,怀春少女可想不期而遇之情郎,酸腐文人可想纵横古今之壮怀,那么燕少千能想什么呢?很显然,她能想的就是“闻人楼”!
越微人曾说过她天真,说过她任性,说过她冷血,说过她自负,却从未说过她笨!一个聪明人若是日日夜夜都在思考同一件事,那么,这件事的漏洞必然会一个接一个的暴露,而真相对每个人的影响力都是不同的,燕少千更是不能用寻常眼光来看待。
而现在燕少千困惑了,她发现越微人收养她的这十三年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所事事。很多时候,越微人都是行踪缥缈的,她开始好奇,在越微人不在慕华山庄时在哪里、在做什么。还有一点她也想要知道:那个所谓的“闻人楼是皇家暗卫的哨点”这样秘密的消息,他是怎么得到的。
燕少千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倒不是什么事情她都会感到好奇,比如:她娘和她爹的事。燕少千不好奇是因为一个已经死的人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与她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她只会好奇与自己现在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事,比如:越微人的事。
燕少千求得事实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个字——“问”。所以,她现在走在去浩瀚阁的路上,越微人也许会在那儿看书。
真相总在不经意间暴露,而且,总在最不该暴露的时候暴露在最不该知道真相的人的面前。
浩瀚阁里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的显然是越微人,至于女人嘛,燕少千不知道,应该是不认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并没有见到,她只是闻到了一种不该属于浩瀚阁且又不十分熟悉的气味。许是在闻人楼待得久了吧,各种女人的气味她差不多都能辨别。
老实说,越微人的武功比燕少千好太多,燕少千只会剑法,内力也许可属上乘,越微人什么兵器都可以用,内力自然也是上乘。
可上乘与上乘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就跟残月与满月之间有差距一样,同样是月亮,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内力亦是如此,燕少千是残月的话,越微人就应该是好几个八月十六的满月。
因此,就算燕少千成心要探查,待她走到浩瀚阁外五十丈处,越微人也就能觉察到了,正是因为这种对自己功力的极度自信,使得越微人放心地在浩瀚阁内接待了天枢阁的代理阁主——摇光。
梅子黄时,湿热异常,留在屋中的气味很难立刻散去,越微人显然百密一疏,于是,就这样,自家的另一份庞大产业暴露在燕少千眼前。
“就这样?天枢阁的情报?”燕少千觉得这答案来得太过容易。
“对,就这样。”
越微人是不会欺骗燕少千的,原因嘛,比较复杂。其一,一个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男人没有必要欺骗一个由他一手养大的小丫头;其二,强大的人都有强大的骄傲,他的骄傲让他不屑欺骗;其三,一个谎言势必要用多个甚至无数个谎言来圆,一旦被戳破,解释起来很麻烦,越微人比较讨厌自找麻烦;其四,将来天枢阁迟早是给燕少千的,早一点让她知道和晚一点让她知道,结果是一样的。基于以上诸条理由,燕少千轻而易举地解了惑。
然而,须臾光景,燕少千脸色变了,她生气了,不,准确地说,她愤怒了。很难理解她为什么要生气,至少,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但越微人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立刻就后悔了。
“一开始我想回来,你告诉我想走也走不了了,然后,我说我害怕了,你根本就是故意说出那番话激我,然后自责,好让我自己乖乖回来,对不对?”燕少千此时是面无表情的,只是从来都流光溢彩的慈悲目如今黯淡无光。
果然是自己的徒弟啊,怎么都瞒不过她。越微人心想,也许太聪明也不是什么好事。
当初他告诉燕少千走不了,是因为那时燕少千只是闯了祸要落荒而逃,其实心里并不是真的要走,若那时候回来,免不了再回去。可是燕少千却又一个缺点:那就是见不得自己伤心。
一个终日哭哭啼啼的人,落几滴眼泪,别人也不会觉得怎样,但若是一个从不掉泪的人哭得很伤心,那旁人定会觉得在他身上发生了异常残酷悲惨的事。
同样,越微人万事皆掌握在手中,难得伤心一回,燕少千定是万般不忍,那时她回来便是真心要回来,而且,为了不让越微人伤心,她也不会再想下山,如此,那滩浑水她便不用蹚了。
不过,即使燕少千明白越微人的这一层心思,知道越微人是为了她好,她也是定然不会领情的。
然而,终究人算不如天算,比如:现在。
“师父,我从未想过,你也是会算计我的。”语气一如平日,可从不知慌为何物的越微人却慌了。
燕少千是个不懂什么叫“尊师重道”的人,她也许满腹经纶,但她却不会如书中所讲的一般去行那些迂腐之事,加之越微人向来对她极其纵容,所以,她叫“师父”的次数是少得可怜的。除非她闯祸了,或是有求于越微人,她是断然不会用这称呼唤越微人的。
现下,燕少千很恭敬地说:“师父,我从未想过,你也是会算计我的。”没有任何的谴责之意,只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想法,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
越微人却是明白的,燕少千向来冷血,对她而言芸芸众生可怜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