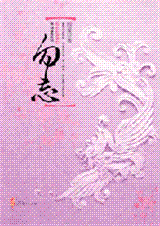清宫.红尘尽处-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梅香?什么事?”沐蓉瑛抬头看了一眼。
“回爷的话,我们格格出了痘,我爹让我来告您一声,防着痘疹流行。”
“出痘?怎么会呢?”沐蓉瑛放下笔,认真地看着梅香,“这附近没听说有人出痘啊?还是她穿了、碰了什么染过痘脓的东西?”
梅香摇头,侧着脑袋说:“我爹也正纳闷,格格这一向穿的用的都是宫里东西,也只出去了一趟,因是去祭个姑娘,爹说,只怕是冲煞了,要跟太太商议,是不是请几个姑姑53来驱邪?”
“请先生看过了?”沐蓉瑛起身走了几步。
“看过了,似乎很不好。”
沐蓉瑛想起什么似地抬了抬头,问梅香:“她去哪里祭人?”
“去雨花台下,是个从前在宫中认识的小姐。”
沐蓉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低声问:“可是姓纳兰?”
“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里种着竹子,还有个亭子,挺幽静的。”
沐蓉瑛颓然坐回太师椅上,挥了挥手:“你去吧……”
梅香去了,沐蓉瑛站在窗边,俯瞰着隔壁的博尔济吉特家。他原本以为留瑕只是皇帝身边一个伶俐的体己人儿,所以才什么都没问……窗边的半桌上放着一本线装的《饮水词》,扉页题着“桃叶女史雅正,愚兄性德顿首”,桃叶女史,正是他心心念念的桃叶红颜——纳兰洁。
从前总觉得纳兰词带着不祥,因他相信,世间没有人力不及的事,只有去不去做、会不会做的问题,事业如此,感情自然也是如此。
“洁儿……”
他看着腰间的荷包,绣着一只船,忆起往昔同乘扁舟游玄武湖,她持着一壶酒,浅斟低唱,却是山西的小曲,是戏耍,亦是表明心迹:“一绣一只船,船上张着帆,里边的意思,情郎你去猜。”
她喜欢文辞,与北京的堂兄纳兰性德多有书信往来,是纳兰性德的词,让他们在夫子庙邂逅。那年要猜元宵灯谜,正是纳兰公子词风靡江南的时候,还有点元宵状元的风雅事,她是性德的堂妹,自然在灯谜会上抡元,于是他注意到了这个清秀的少女,某次在渡船时遇见,便攀谈起来。
因为纳兰性德结缘,也因性德之死而分开。三四年前,纳兰性德病逝于北京,她同父母去祭奠,性德之母赫舍里氏十分喜爱她,百般挽留;又让伯父明珠知道她有文才,与她父母商量后,就将她送进宫给惠妃做伴,顺便教导年纪最长的三格格诗书琴棋。但是宫中向来在宫女、女官二十岁上下就会放出去,决不留人超过二十五岁,沐蓉瑛一直耐心等待着……
这么一去,万里河山、千仞宫墙阻绝,音信全无。只没想到,回来时,却是一个小小的骨灰坛和一本泪痕斑斑的《饮水词》,叫他情何以堪?
最难受的,是她从不入梦,沐蓉瑛合起那本词集,里面的性德的亡妻尚且托梦而言——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洁儿,你在哪呢?
而另一头,在杭州的康熙自然不知道留瑕出痘的事,他正由浙江巡抚金鋐、闽浙总督王騭、杭州将军郭丕、礼部尚书张玉书、熊赐履、李光地等人陪同,东奔西走,忙得不亦乐乎。
这群陪客中,金、王、郭三人是东道主,本不稀奇,张玉书是江南丹徒人,算是半个地头蛇,又是饱学大儒,被康熙点了名作陪。而熊赐履与李光地之间,则有点尴尬,这熊赐履是太子师保,前些日子丁忧守制在南京家,此番特来伴驾,他原是李光地座师,也曾举荐李光地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不知怎么,师生二人忽巴啦地翻了脸,此后明争暗斗不断,只是碍着康熙在场,不好明火执仗指脸子骂而已。康熙冷眼旁观这群近臣,隐隐察觉这些人脸上笑得开花,心里恨得咬牙,只沉默不语,静观其变。
这一日御舟过了钱塘江,泊在会稽山下,张玉书向其他人告了个罪,去忙康熙交付的差使。众人正要随驾,康熙却挥了挥手说:“你们都在这儿候着,朕也只是上去看一看就下来,朕脚程快,你们跟不上,榕村54跟来吧!”
李光地答应了一声,急急跟上去,跟在康熙身边说了不知什么,只远远瞧见康熙拍了拍他的肩膀,似乎很是赏识。熊赐履自坐了个折椅,摇着扇子,嘿然冷笑不语。
坐在熊赐履旁边的是金鋐,他在平台战争时是福建巡抚,与施琅、姚启圣等人共谋台湾,用兵在外不能没有内应,出身福建的李光地在朝中明的暗的帮了不知多少,金鋐等人因而与李光地结为莫逆。
金鋐见他脸上冷冷的,猜测是不满李光地,便想给李光地缓颊,见熊赐履额上沁汗,便帮着扇风,笑着说:“孝感公55,浙江这地方湿热,我让人熬了绿豆汤,给您降降火。”
“您受累。”熊赐履当然知道金鋐跟李光地交谊匪浅,听他说给降火,心知是要给李光地讨个情,只不肯成全他,本想拿话刺一刺,抬眼皮一看旁边,却坐着闽浙总督王騭,这人做事勤奋,很得康熙喜欢。熊赐履心中掂量,不清楚金王二人的底细,便敛了怒容,把话说得含蓄:“地方热有地方人的方法,听闻浙江的竹夫人啦、扇子啦……做得挺好,一个夏天卖下来,就是秋天没人买了,也还能过得去,抚台大人,是吗?”
金鋐把这话掰开揉碎,又怎么听不出熊赐履自叹“秋扇见捐”,不肯卖他个脸面与李光地合好的意思?心中暗骂了一声“老匹夫”,也淡淡一笑,不愿再拿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
倒是王騭拿了手巾擦擦额头,不咸不淡地从旁边插过话来:“浙江不单竹夫人做得好,汤婆子也做得好,这一带的女人家,还流行过一首竹夫人的歌,这是乡野俚曲,本是不入孝感公清耳的,只是咱们办事人多少了解些风土民情吧!郭军门,您嗓子亮,给孝感公听一听咱浙江的野味?”
“得了您哪!”郭丕虽然位居将军,却是在朝中当过侍郎才放出来的,宦海浮沉,没少见过这些龙争虎斗,心知是制台大人要揶揄这位理学大家,想了想就唱:“竹夫人原系从凉妇,骨胳清,玲珑巧,我是有节湘奴,幸终宵搂抱着同眠同卧,只为西风生嫉妒,因此冷落把奴疏,别恋了心热的汤婆也,教我尘埋受半载的苦。”
一曲唱罢,金王等人连带旁边的侍卫都笑得打跌,熊赐履虽也赔着笑,但额上青筋一蹿一蹿,王騭見他要恼,倒也不怕,只摇着扇子,一语双关:“再给诸位说个笑话,不笑可别怪。有个男子没讨老婆,就这一个竹夫人、一个汤婆子,家有两醋,闹个不休,这男子就说‘竹夫人,你是伶俐的,别为汤婆闷;汤婆子,你是老成的,也莫怪竹夫人。你两人各自去行时运,冷时节便用汤婆子,热时节便是竹夫人,我与你派定休争,各自耐着心儿等’。”
说完便与郭丕一起笑,金鋐与熊赐履心中一凛,这王騭果然是个狠角色,平日里不哼不哈,哪一边都不靠,可今日里说出这话,是不是康熙对他说过什么体己言语?要他来敲山震虎?两下都静默下来,又等了一阵,康熙与李光地下来,又各自上了御舟、官船不提。
又过了几日,这些封疆大吏、饱学宿儒更是觉得有些惶恐,原来康熙特别颁赐王騭御衣凉帽,大加褒扬他是清廉总督,圣眷顿时又高出李光地许多,对金鋐,则有意无意地提起他之前上奏杭州旗兵骚扰百姓的事,搞得金鋐惴惴不安。
而自从那次随驾观潮后,康熙就不怎么要李光地在跟前,闲暇时屡召熊赐履,却又绝口不谈李光地,只东拉西扯一些读书心得。李光地心中忐忑,熊赐履也是如坐针毡,不敢多惹是非,一群庙堂之臣被皇帝搓弄如同婴孩。
康熙在浙江耽搁了五六天,终于要回转南京,离杭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逮捕了浙江巡抚金鋐与布政使李之粹。罪名正是金鋐假造有百姓出首控告旗兵扰民,康熙自己在苏州派出侍卫观风,又亲自询问消息最是灵通的酒馆店伴,到了浙江,又派张玉书去查访,确定金鋐口中控告旗兵的百姓根本是子虚乌有,但布政使竟附会于金鋐,故一同判刑,最后,金鋐充军奉天、李之粹发配黑龙江。
李光地与熊赐履两人见此情都觉得十分不安,李光地是疑心这是康熙有心剪除他羽翼,而熊赐履则是觉得天威莫测,各怀着不同的心思,随康熙回到南京。
御舟停在丹阳,康熙侍奉太后由陆路经句容县入南京,当晚驻在句容县城。江宁织造曹寅早与两江总督傅腊塔、江苏巡抚洪之杰等人前来朝见,制台、抚台二人见了康熙就退下,曹寅倒是被康熙问了许多,等到要退出前,曹寅才说:“主子,有件事儿,原不该这时候说的,只是事情有些棘手,不能不报。”
康熙倚着迎枕,自己捶着腿,半眯着眼睛,闻言看了曹寅一眼,又懒懒地低下眼皮:“你这话奇,这本来就是个望风奏闻的时候,说。”
“这不是国政,是一点私事……”曹寅飞快地瞄了康熙一眼,低下头说,“留瑕格格出了痘,情况很是凶险,是血热痘疹。”
“血热痘疹?怎么会呢?”康熙矍然开目,坐直了身子,“什么时候染上的?”
“刚回南京两三天就染上,已经有十天左右了。”
“南京正流行痘疹吗?”康熙问,旗人、蒙人向来最怕痘疹,他自己是与太后同时得的痘疹,染过了不怕,只是不知道这船上有多少宫女还没染过,而且最怕把痘毒带回京。京里现在还有些等着要见他的蒙古王公,当中只怕还有没出过痘的,要是有个万一,蒙古局势就要生变。
曹寅自然也知道这层干系,连忙回答:“回主子的话,没有,格格家住的那一区,去年才有个先生给孩子们都种了鼻苗,几乎都出过痘,在格格发病前,也没有人出痘,奴才这才觉得奇怪,格格是从哪儿得的痘疹?”
“朕知道她,小孩性子爱热闹,她可有出去哪儿玩?才带了痘疹回家?”康熙定了定心,脸上敛了平日的微笑,却依然显得从容,只眸中反映的桌上烛火,泄露了他的心焦。
曹寅还是摇头,他搓着手说:“格格就去了一趟纳兰小姐坟上,是奴才的家生子儿赶车送去的,他说格格上坟之后,去雨花台下捡些石子玩,接着就回家了。可奴才的这个家仆也还是生身,但是没有发病,奴才与先生讨论了很久,实在想不通是从哪儿得的。”
“女孩子家爱美,生了个痘疹可多伤心?病人最怕寂寞,她又是个爱玩爱闹的性子,不定多么难受呢……”康熙默然良久,才挥了挥手说,“到了南京,你给安排着,朕抽空去看她,下去吧!”
观星台.康熙二十八年春
康熙车驾一到南京地面,熊赐履就不安分起来。他侨居于南京,丁忧守制也在南京,在这六朝金粉之地搜了许多古书,康熙一路让他侍驾,问一能答出十个典故来,倒把平日精明风趣的李光地给晾在一旁。
车驾未至中午便已经到了作为行宫的江宁织造府,曹寅昨儿深夜就赶回南京处理一应事务,康熙车驾一到,万事俱全。
康熙安顿好了太后,用过午膳后,便找了熊赐履来。熊赐履听得皇帝要单独召见,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没有旁人,更方便探探皇帝对李光地的态度;忧的是天威莫测,不知是否有什么训斥?
康熙却不在房子里,跑到园里水榭乘凉,熊赐履在水榭廊外报了名,听见阁里传他,才沿着回廊走进去。绕过几个回廊,水榭就出现在眼前,碧纱糊的四壁,又透气、又防蚊虫,一旁翠竹、流水、青石尽入眼底,真个是个清凉世界。
水榭里隐隐传来人声,熊赐履看去,见康熙自坐了张檀木螺钿贵妃椅,一脚盘起跨在椅沿,一脚伸直了放在椅面,一只手搭在椅背,另一只手拿了旁边的点心往嘴里送;旁边几上用青花瓷盘装着四色点心,甜的糖心莲子、五色糕,咸的五香豆、切丝板鸭,配上一盏清香碧绿的栖霞山茶;几子旁坐着一个汉装老婆婆,捧着个旱烟袋抽个没完。
熊赐履心中讶异,康熙不喜人抽烟,这老婆子怎么这么大胆,大咧咧地在康熙面前喷烟?
“哦?愚斋来了?来见见朕的乳母曹孙氏,虎子的娘。”康熙招呼了一声,转脸笑着对曹老太太说,“阿姆,这是朕的老师,也是朕给保成56挑的新师傅熊赐履。”
“那我老婆子得跟您见个礼。”曹老太太虽然有年纪的人,手脚却麻利,起身向熊赐履一福,“熊师傅万福。”
“老太太安。”熊赐履连忙回礼。
“阿姆,你去歇晌吧,晚些朕去看你,啊?”康熙说,曹老太太答应了一声出去,康熙收起放直的腿,盘膝而坐,瞄了瞄站在前方的熊赐履,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你坐。”
熊赐履谢了,斟酌地坐了凳子的一半,康熙也不发话,自顾自地吃东西、喝茶,慢悠悠地摇着一柄湘妃竹扇。
沉默,如同铅云一般压上熊赐履心头,那竹扇是在打磨光亮的薄竹片上镂出《东坡游赤壁》图,光线从竹片镂花的细孔中洒落,熊赐履却觉得,那透出来的亮光,有一部分是康熙的目光,正在静静地审视着他,于是把头压得更低。
“喀”的一声,那把扇子便收在康熙掌心,他淡淡地问:“你丁忧在家,健庵57可有信给你?都谈些什么?”
“回皇上的话,健庵与臣常有书信往来,都谈的是学问上的事儿。”熊赐履紧张地说。
“嗯?朕看过你写的《学统》,写得很不错啊……”康熙又懒洋洋地玩起扇子来,一手抓了几颗五香豆往嘴里丢,“都讲了什么学问,说来朕长长见识。”
熊赐履欠身一揖,略一沉吟,便将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读书心得娓娓道来。康熙一边听、一边想,却不怎么插话,听他讲完,才问:“听说你最近还研究历算之学?跟洋人学的?”
“回皇上的话,南京前些日子来了两个教士,一个叫洪若翰58、一个是毕嘉,洪若翰,皇上在京里也是见过的,这两人精通历算、星象,就住在臣附近,故而常去请教。”
“你跟榕村……都喜欢星象,到底是师生啊……”康熙拿了茶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