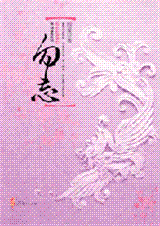清宫.红尘尽处-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旁边的大宫女连忙兑了茶过来,帮着收拾:“娘娘,可要试试这儿的东西?”
佟妃打开其中一只,一股似兰似麝的香气便散发出来,她沾了一点在手背上涂匀,颓丧地说:“试什么?都老了,再怎么搽,能把青春年华搽回来吗?”
“娘娘,您说哪儿话呀!外头传好了热水,您先沐浴,咱再来打算这些东西。”这宫女很是聪慧,赔笑着扶起她,“我奶66说,这面膏花粉涂了虽说不一定有效,可不涂呀,那就一定无效。娘娘华质丽资、风韵天成,不用粉儿花儿也比其他的小主强,只这些东西横竖放着也是放着,用起来,就算无效,看着也赏心悦目,不用倒浪费了。”
佟妃给她哄得回了心,破颜一笑:“就依你。”
沐浴过后,佟妃由着宫女伺候,先在身上涂了用人乳、藕汁、苏合香油等药方调的四精膏,这是宫中常用的体膏,能使肌肤润泽,温暖的淡香让佟妃的心情好了许多。坐到妆台前,又看了那份折子,因她脸色向来苍白、体质孱弱,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便想润一润色,遂叫宫女取了太真红玉膏给她匀脸。
这太真红玉膏传说是杨贵妃常用的,原方是要取杏仁、滑石、轻粉磨成细末蒸过,加入冰片、麝香研磨,用时再加入蛋清匀成面膏。曹寅妻子为使方子更见效,听了大夫的话,把轻粉换了珍珠粉,打开只闻得淡淡冰麝香,沁人心脾,宫女们取了蛋清来调膏,细细给佟妃搽了。
正要准备着就寝,佟妃又叹口气,有气无力地吩咐:“去问问皇上回来没有?”
宫女们答应着去了,佟妃默默地摆弄着桌上那些瓶瓶罐罐,突然见一个宫女喜滋滋地回来:“娘娘,皇上让您去呢!”
“哦?”佟妃猛地抬起头,南巡以来,还未得一幸,眼下心前,全是康熙疼宠留瑕……她抚着心口,刚稳下来的心绪又被搅乱,略定了定心便换了衣裳往康熙住处赶去。
她的住处离康熙住的后堂不远,绕过几个回廊便到,每隔几步就悬着一盏宫灯。江南夜雾,笼住满园梨花疏影,夜露渗过肌肤,竟感微凉,这短短的回廊走得人心焦。她拉紧身上披风,满眼春云轻风不在心上,只悬念着宫灯彼端。
好不容易绕出了回廊,眼前开阔,堂前一个闲人也无,侍卫都站在二门之外,金砖漫的地面洒落月光如水,康熙端了张躺椅,正独坐院中,瞑目想着心事。几个粗使丫头低着头正从配房提着一桶桶冒着热气的水往屋里送,佟妃不敢惊动康熙,拦住了他身边暂代的总管:“皇上今儿去了哪里?”
“回贵主儿话,先去了留瑕格格家探病,又去了观星台跟玄武湖。”
佟妃一听去留瑕家,也不动声色,只问:“今儿用的什么浴剂?”
“今儿没用浴剂。”
“格格生着病,我看还是去寻御医配点艾草、沉香清清身子才好。”佟妃吩咐,那总管迟疑了一下,还是去了,佟妃站在廊下,望着康熙的身影,见他穿得不厚,心头疼惜,便解下了披风,走到他身边给他披上,“皇上,夜凉。”
康熙没有睁开眼睛,却也没有把披风扯下,一手支着头,疲倦地说:“朕心里有数。”
佟妃低下身子,试探着坐到他的躺椅边,康熙没有动,任她依偎。佟妃靠在他怀中,轻搂着他的腰,纤纤素手抚过他的身子,听见他胸腔里稳定的心跳,随着心脏的跳动,她感觉到一阵阵的温热从他胸膛传到脸上。
康熙如何不懂这暗示?只他现下没心思哄她,佟妃在这事上向来羞涩,给她摸几把也还不至于撩拨得他欲火难耐,便半躺着,不动、不说话也不拒绝。他放空了心神,将外在的一切抛诸脑后,再把今日得知的千事万事全部兜在一起,在脑中分门别类。
先扫去礼仪文章,什么派了谁去祭陵、谁去祭神之类的事,再抹去各种奏请册封旌表的事件,诸如哪府哪县出了节妇烈女的事,将剩下的国政,分六部排好,跨越两部以上的大事才开始推敲,该用谁、降谁、警告谁、观察谁?该花多少钱赈济今年的凌汛?多少钱淘挖南巡看到的运河淤积处?蒙古情势要用哪个旗防堵哪个盟?宁夏、古北口、喜峰口等通往蒙古的关隘是不是该换换军备?都统要不要更换?军队要不要移防……
直想了两三刻钟,想好了明日该如何发布命令,康熙才把心神放到外部去。佟妃早已把他半个身子都摸了个透,见他还不动如山,气不打一处来,又觉得委屈,都已经从脸吻到颈子上了,怎么还在装死?难不成转了性儿,要做柳下惠?
康熙还是不想碰她,懒洋洋地扭了扭身体,闭着眼睛说:“水好了没?”
佟妃失望地撑起身子,见那总管飞奔过来:“回皇上,水已好了。”
“好了干吗不早报?谁教你这么伺候差使的?打量着朕冷死没人心疼?留瑕回来,就打发你去照顾规矩!”康熙打着哈欠起身,随手把佟妃的披风扔在椅上,嘴上抱怨,脸上却没有半丝责骂的意思。
那总管也是个驴性子,越骂越开心,笑得脸上开花,早拿来了康熙的披风给他裹上:“奴才哪舍得皇上冷?不过,照顾猫小爷可是美差,奴才巴不得呢!”
“美得你!吃了蜜蜂屎67似的,骨头轻得都快飞上天了,就你这马虎样儿,朕还舍不得把规矩给你养呢!”
康熙笑骂着往堂中走,拾阶而上,刚打开门,满脸的笑容就像凝固了似的,迅速滑落下来,沉声问:“谁让你做主用的艾草!”
那总管还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就说:“回皇上,是贵主儿吩咐……”
还没说完就马上住了口,低头退到旁边去。北京水少,就是在宫中,洗浴一般也都是擦澡,南方富贵人家则多是浸浴,康熙来了南方,也入境随俗,松乏松乏身子。闻着艾草味隐隐从房中传来,康熙却没有发作人,只攒紧了眉进去,洗没一刻钟就出来,一迭连声要人把水拿去倒了,赶紧地开窗把艾草味都散掉,而且罕见地让人再烧热水,什么都不准加!
佟妃知道自己惹他不悦,但是却不知他为何不喜欢艾草。等水的空档,康熙又去另一头躺着不动,佟妃不敢过去,等他又浸了热水,这回泡了两刻钟左右,才甘愿起身。穿得厚厚的,又用木香汤洗了脚,套上厚棉袜,自顾自地上床去睡。
佟妃站在外寝,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半晌才听康熙慵懒的嗓音从床帐里传来:“宣你来不是让你罚站的。”
佟妃闻言,心中才松了些,走了进去,宽去外衣,放下床帐,低声说:“臣妾擅自做主用了艾草,请皇上恕罪。”
康熙手臂一伸,将她揽入怀中,温声说:“你跟朕,老夫老妻了,还不知道朕最厌烦艾草。小时候成日给御医们针灸,熏都熏怕了,闻了就头疼……不过这也没什么,往后记得就是。”
“臣妾无能,惹皇上心烦了。”佟妃轻轻地抓着康熙衣襟,倚在他怀中说,“臣妾有时真羡慕留瑕格格,皇上见了她,就是怒也含笑……”
话中有话,分明是幽怨,康熙厌恶地皱了皱眉,却还是哄着说:“留瑕是个鬼灵精,羡慕她做什么?”
“皇上不就喜欢格格聪明伶俐吗……按说也是的,格格出身好、相貌好,风华正盛,不像那些刚进宫的贵人不知情趣,也不像臣妾这些老妃子死板单调,不怪皇上疼她入心。”佟妃窝在康熙怀中,喁喁细语,手指绕着他的盘扣。
话至此,康熙明白留瑕是在一个极端尴尬的境地中了。妃子们观望着,知道他宠她,还不敢造次,可要真的纳了留瑕做贵人,妃嫔们就会群起攻之。他心中一沉,暗自神伤,看来这留瑕确实是留不住了……
心头沉重,但是康熙不动声色,像一般人家夫妻临睡前谈家常似的说:“留瑕得了痘疹,这痘疹来得奇,她附近没有人出痘,你要防范着,会不会是宫里有人出痘不知道?”
“臣妾晓得了。”佟妃答应了一声,她却不像康熙那样忧心,似乎还有一丝轻快,她说,“皇上,咱们好久不曾这样说说话了。”
“嗯……”康熙骑了半天的马,又憋着气,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敷衍地应一声就想翻身睡去。
佟妃将他的手捧在心口,平静地说:“皇上,臣妾宁愿您少召臣妾去乾清宫,哪怕一年只能来臣妾宫里一趟也好,就算您没碰臣妾一根手指,臣妾也不怨。臣妾不会诗词歌赋,也不会讨您喜欢,可咱们就这样整整齐齐地说说话、扯扯家常,谁生病了、谁生孩子了、谁结婚了,这不才是夫妻吗?”
康熙心中一动,没有说话,佟妃摇了摇头,把头缩在他肩窝,闷声说:“睡了?”
康熙正要答话,却见佟妃爬起身来,给他掖好被角,便闭了眼睛装睡,听得佟妃自言自语地说:“每回要跟你说话,总是抓不准……歌儿里说梦见了情郎在别人怀里,可你梦里梦外都不在我身边,好不容易在了,可又睡了……唉……睡就睡了吧……也是我心里难舍得,我的皇上啊……别是在我怀里,可梦儿中又到了别人那里……”
突然,佟妃苦涩地一笑,康熙觉得有人把他搂在怀中,又听佟妃低声说:“犯傻,梦里去了何妨?醒时去了才是苦呢……”
康熙胸中涨起一阵酸热,感觉佟妃的手轻轻拍着他的背,像哄着孩子,他静静地伏在她怀中,止不住心中一阵惆怅。心爱的女人得不到,可眼前这妃子却又如此情深,叫他想惩治又下不了手,只能将这满腹心事锁在肚里,迷迷糊糊地睡去。
如水春月照孤单,留瑕拥着宁绸衾被,也是满怀愁思。出痘最怕冒风,不能开窗,想着今夜,玄武湖畔春柳如烟,浓艳的是湖上画舫、才子佳人,淡雅的是自家院中明月又照梨花落。幽幽冷香,冻不住心头一阵阵涌上的温热情思,待欲入梦,抬手搁在枕边,才发现腕上的白玉镯松松地落到肘间,心中一惊,这镯子打她入宫就戴着,向来只能推到手腕上三寸而已。
留瑕思量片刻,还是披衣起身,揣了菱镜,就着窗纸外透入的月光独看,看了一眼,便把镜子撂下,支颐望着瓷瓶中一枝梨花发呆。愁的倒也不是容颜减损,还是自及笄以来就烦恼至今的老问题,人人看着她事事圆满,倚仗着太后皇帝,有才有貌、有钱有势,可谁又懂得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谁又明白她最怕指给了个不争气的满洲汉子?古往今来多少才女美人,真正能幸福圆满、白头偕老的有多少?
就像她父母,算是情投意合、郎才女貌了,可谁知三藩乱起,东南半壁烽烟四起,父母将她仓皇送走。她刚到北京不久,就听说父亲带着所属军队开往岳州与安亲王岳乐合兵,为了保护主帅而死。母亲将父亲的遗体收葬在南京将军山下,随后也殉夫而去,二十载的恩爱一朝毁于战火,徒留这寂寞深院与一湖凄凉。
越是深情缱绻,分离越是痛苦难舍,如钝刀子剜肉,越挖越疼,可是要一刀斩断情缘,又谈何容易?
留瑕打开自己的首饰箱,拾起里面一个银白龙纹锦盒,盒里躺着一串天青色珠子,每颗珠子接缝处,都用银丝绕成托子,防着珠子互相摩擦,用银线串起来,垂着银白的穗子。
留瑕将这珠串用丝帕小心拿起来,乍看并不出奇,戴在留瑕雪白的手腕上,在薄薄月光照射下,银丝珠光相互辉映,泛出一层淡淡光晕,这便是最为名贵的东珠了。不同于每次可以进几十盒的普通珍珠,东珠生在东北的松花江里,禁止百姓采集,一年进上的数量只能以颗计算。未入关前,太祖更曾为了私匿九颗东珠而斩杀功臣;入关后,为表示皇室守土有责、国运如日东升,才在皇族冠服上许用东珠,而一个亲王的冬朝冠上,也只能有十颗,留瑕这串珠子的珍贵可想而知。
当然,珍贵的东西,留瑕见得多了,而这珠串后头包藏的情分,比珠串要可贵得多。这是太皇太后七十大寿时的寿礼,康熙带着留瑕到珠轩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才找出来的十五颗一般大小的天青东珠,康熙与留瑕又闷在珠轩里看了一堆样式、画了图稿给造办处做,太皇太后去世前,把这珠串留给她做个心念。
“姑娘,这串珠子,我思来想去,还是给了你……太宗皇帝从前告诉我,他说,这东珠是天赐满洲的宝贝不假,可说起来不过也是珠子,为什么这么看重呢?”太皇太后珍惜地摸着珠子,用丝帕擦干净,看过一甲子的风云开阖,人生的体悟,全在这串珠子间,“其实,这东珠从前都是要送给前明皇上的,建州左卫一颗也留不住,就为了东珠,太祖皇帝不知受了前明多少气,我们把东珠镶在朝冠上,就是要儿孙永远记住,前人吃的苦、受的难,就是为了能把自己土地上的东西留在自己手里。太宗皇帝还说,从前大金跟辽打起来,也是为了辽国要抢我们的海东青去捕天鹅,而天鹅吃蚌、肚里有东珠……”
太皇太后那苍老的眸子亮起一丝狂热,她的声音慢慢地高昂:“姑娘,我给你这串珠子,是知道你不是个普通人,你要记得我今日的话!为了能做自己的主,不管多少羞辱、多少困难,都要忍,就像珠蚌结东珠,要发光、要发亮,你就得忍着沙砾在身子里硬磨。这沙砾,那就是你的男人!满洲男人命硬,是海东青一般的性子,天不收地不管,可他们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你要忍着他们的臭脾气,把这沙砾包成了东珠,他就一辈子离不开你了!我没能把太宗皇帝包成个东珠,可我姑姑哲哲68就能,太宗皇帝爱过我姐姐,可那是迷恋,姐姐去了,到头来,太宗皇帝还是回到姑姑身边,这才是真正的东珠!这就是汉人说的‘守得云开见月明”,姑娘,你明白吗?’
“老太太……”留瑕深深地叹了口气,太皇太后的容颜消失在记忆深处,“可皇上不是太宗皇帝呀……”
南京又下了一场春雨,朦朦胧胧地洒满了这灰扑扑的石头城,把城中的春景全都洗了出来。康熙陪太后吃过午饭,太后自去歇晌,他的习惯是吃饱饭就要遛弯,午晚两餐饭后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刻,他有个好处,就是不在快乐的时候给自己难受,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