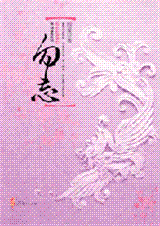清宫.红尘尽处-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的东西里。
她斜倚着床,柔顺的长发松松地扎着辫子,绣篮里,一只鲜黄色的小老虎露出两颗可爱的虎牙,傻乎乎地抬头笑着,另一只则抓在她手里,正要缝上耳朵、挑上胡子,刘婶对她说:“格格,这虎头小鞋活灵活现的,是做给谁呢?”
“这是给四爷做的,离京前,他看见我之前给五爷做的鱼鞋,说也要我做一双。”留瑕看着那只咧嘴笑的老虎,苍白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轻松。
远处传来一声闷雷,刘婶说:“怕是下雨了?”
说着就要去关窗,留瑕连忙阻拦:“别,拉下窗纱就成了,我想看看春景。”
刘婶应了一声,把厚纱窗架拉下来,顺手把趴在窗沿的雨蚊扫走,空气中,顿时充满了大雨的气息。厚纱透不进风,隐隐绰绰看得见院中瞬间变得白茫茫的一片,雨点打在瓦上,发出响亮的噪声,留瑕耐心地等着。过了片刻,雨就慢慢地变细了,轻飘飘地落在庭内开败的落花上,透过敞开的院门,可以看见湖上斜风细雨、烟柳朦胧,一派清幽。
留瑕默默地做着针线,心头数着日子,南巡已经足足两个月了,想起来,就像做了场大梦,醒来之后,康熙与她,好像更亲近了,又好像更疏远了。她隐约感觉,这次的南巡对她的生命是极大的转捩点,只是那最重要的转变何时来临,她心中还没有底。
午后细雨绵密,留瑕放下针线,沉沉地睡了一觉,梦中有一缕幽幽笛声牵引着她,觉得身子像雨丝那样轻盈、像柳枝一般柔软,也许是化作人间雨、或是河岸柳,前方江波碧水间,似乎有个相当熟识的人乘船而过,她心头顿时觉得万般不舍,想伸手去挽住,却越拉越远,梦魂中都觉得惆怅难耐……
忽而惊醒,再入梦时,依稀像在宫中,红砖墙、明黄瓦,落花满阶无人扫,长风吹动一树雪白,花雨纷飞中,有人将她牢牢抱住,待要挣脱,却又乏力,她看不清那人的脸,却不害怕,只觉得说不出的温柔甜蜜,鼻中嗅出淡淡的龙涎香,心中一宽,再不矜持。
一场春梦直到掌灯时分才悠悠转醒,帐中还留有龙涎残香,但梦中之人早无踪影,她怅然地四下看去,才发现不过是帐下踏板边一个青瓷博山炉70发出的香气。长长一叹,起身去拿汗巾,坐在妆台边将额上、颈间的汗揩了,低头一看,妆台上放着一封素纸封的信,也没写收信人、背后也没有花押,留瑕眸中一跳,却有了生气,她急忙抽出里面的素纸折子,却见一行行流利的行书写着:
谕留瑕:
前者往尔家去后,诸事缠身,不得再往尔家共赏玄武湖景,甚憾。回銮时日已定,三月初一便奉圣母太后登船溯河北上,入鲁弃舟登车,三月二十之前可抵京师。
昨日问过御医,知尔痘疾粗愈,朕心甚慰,已着御医加紧调养,料无大碍,待尔康复,再宣伊入京。朕适才去祭纳喇71女官,巧遇尔家世交沐某,伊言道与纳喇家亦是世交,故来祭扫。此人相貌看得去,略问商道也是井井有条,曹寅告朕,说沐某在旗,帮办省中事务很经心,照看尔家产业十年,未有侵夺之心,尔卧病,又常来探望,实属难得。只尔系黄金血胤、朕之幼妹,员外郎蕞尔小官,与尔往来,未免有些悬殊,朕拟加其为四品候补道,让帮办曹、李72两家事,这话只对尔言,放在心中便是。
此中还有一事要对尔言,便是规矩,尔若淹留江南,规矩当同留江宁,但朕实喜规矩顽皮灵动,万难舍弃,故先带了回京。若太后诏尔来京,朕当面奉还,若尔归嫁江南,则规矩留朕作一心念可好?
朕不日离宁,无暇与尔再见,此心此情,尽在信中,随信寄上一只南朝青瓷博山炉并一盒龙涎香,着人点了给尔安睡,物虽微而心实远也,勿笑。特谕。
这信也没有落款,墨色尚新,像是刚刚写完,留瑕看着信,眸中的神采一寸寸退去,给沐蓉瑛加官、让他与曹寅李煦一同办差,是把他当做了心腹人来看待,可是,她如何不懂康熙信中的意思?给他加官,是为了抬高他的身份,好配得上黄金血胤的她!
留瑕把这信用力一攥,她恨他玩弄了她的感情,来探病时说要她回去,此时又要她嫁给沐蓉瑛,还好意思拿规矩来表示不曾忘记她!留瑕很想三下两下把信扯碎,可是谁都不能扯皇帝的信,只得又松开。素纸松开来,像她的心一样,已经破了几个口子,疼得一阵阵发抖。
镜中的倒影也跟着颤抖,眼前的一切不知是因为发抖还是怎么了,竟模糊起来,留瑕感觉到强烈的憎恨,还有强烈的依恋难舍,她恨声说:“为什么不敢来见我!为什么!”
滚烫的泪滑过同样滚烫的脸,滴落在书案的砚台里,被墨锭辘辘磨过,听在耳里,像磨在心里那么痛苦,留瑕援笔,含悲忍泪用气得发抖的手端楷写下回信。
她用尽量恭敬的措辞驳斥了康熙意图要她嫁给沐蓉瑛的想法,因为太后绝不可能同意她嫁给汉人,她明白了当地告诉康熙,不用怕她死赖在宫中不走,她已打定主意任凭太后指婚,横竖哪一个都是满洲亲贵子弟,不需要他来加官晋爵。她越写越怒,怕自己写得太过火,丢开了笔冷静片刻才又继续写下去。
这封信很快就送到康熙手上,还附上一枝海棠花,他在灯下拆看,不恼怒,只是寂寞地笑了笑。他早料得到留瑕的愤怒,即使留瑕的激烈反应让他清楚感觉她对他仍有依恋,可是他必须要预告她这样的未来。
佟妃被送回去住处了,下午那场大胆的争吵,让康熙警觉留瑕将成为他与后宫之间极大的冲突点,而后宫,是他稳定朝政的秤子,必须不偏不倚,让各方势力保持平衡,皇权才能在这个平衡上居中谋事。
然而,对留瑕有愧吗?康熙自问,他做事从来不曾有愧,他打开手边一份折子,上面写着,“沐蓉瑛,字元贞,汉军正白旗人,父沐恒,浙江候补道任满还乡,祖沐清,前明黔宁昭靖王73后人,爵不详。顺治十六年九月甲寅生,康熙二十年捐户部候补员外郎,现居江南江宁府,帮办江宁织造署务。”
“家世不错呀!放在前明,也算是个龙子凤孙了。”
康熙轻点着折子,脑海中浮现适才与沐蓉瑛在纳兰洁墓前相遇的情形,他猜得出来,也许沐蓉瑛就是纳兰洁不愿从他的理由。而且,他感觉沐蓉瑛已经猜出了他的身份,因为他感觉到了敌意和防备:“沐兄与纳兰小姐有旧吗?”
“在下与纳兰家是世交,纳兰小姐是家母的义女,奉母命前来看看她。”沐蓉瑛撒了个谎,虽然他父亲确实认识纳兰家,但是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哦……”康熙点头,既是世交,来祭拜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沐蓉瑛岂是省油的灯,反过来盘康熙:“袁军门与纳兰小姐也有交情吗?”
康熙脸上一僵,很快就反应过来:“内人有诰命身份,常到宫里见老太太们,也与纳兰小姐熟识,此次随天子来南京,便要我前来祭拜。”
“夫人想必与纳兰小姐交谊匪浅,还惦记着,在下代纳兰小姐谢过了。”沐蓉瑛一揖,已是带了主人的派势。
康熙皱了皱眉,感觉不悦,但是又寻不出由头挑剔,毕竟人家是堂而皇之的“世交”,自己还要托言代妻祭拜,自然只能站在客位。
从人摆上香烛,康熙持香站在墓前,想墓中香魂已远,他悲伤地望着墓碑,在心里说:“纳兰小姐,恕朕不能见你最后一面;只因亲临病榻是殊恩,本来不死的受了殊恩也要死。朕原本希望你只是想亲人,让你出去养病会好些,只是没想到,一去,就再见不到了……”
“朕知道你不愿从朕,认为朕不让你自由,可是,朕自己又何尝自由?朕来祭你,也要偷偷来,怕人知道朕喜欢你,坏了你贞节,朕心里的苦,你知道吗?”
康熙持香拜了几拜,将香插进香炉,从怀中拿出一份封好的信,放进燃烧的纸钱中,看着那封信被烧开了封口,露出里面康熙那一手端正的楷书,烧掉了纸上的“情”“愁”“怨”“哀”等字。信与纸钱一同化为灰烬,康熙觉得,自己胸中的悲凉,没有烧尽,只有更重。
看着那墓上长出的短草,想到墓中的红颜,生前如何清冷高傲,死后,也不过就是这些野草的养分。思量之下,顿觉人世悠悠,沧海百年如一梦,不由得为之怆然。
康熙探口气,从怀中拿出帕子揩了揩脸,转身回到墓前的小亭里,与沐蓉瑛攀谈了几句就离去了,回行宫后便写信给留瑕,他是真的觉得沐蓉瑛好,一表人才,家产殷实,唯独就是这个汉军身份麻烦些……
突然,他目光一闪,瞄见了留瑕信上的两行字,喟然一叹,拿起来细细读了“……元贞虽好,然汉蒙之分早定,断难为老佛爷所允,俯望皇上三思。昨日小婢折了花来,言是湖外一树早放海棠。记起康熙二十五年文华殿花开之时,抚今追昔,万仞宫墙内;尚能相伴,盈盈一水间,不得相望……”
康熙拾起那枝海棠,虽比不得文华殿上那一片名贵的西府海棠,但浅粉淡红相间,也还妩媚,借花喻人,宫中朝夕相伴的人,如今隔着那一湖水,连心都变得远了……
康熙收起信与花,再不多想,起身往太后住处去,刚打了个千儿下去,太后便问:“是不是有心事?”
康熙抬起头来,仁宪太后微笑说:“都愁上眉头了,瞎子都看得出来,怎么了?”
康熙将思绪整理了一下,才试探地说:“儿子想……把留瑕留在南京。”
“为什么?她自愿的?”
“不是……”
康熙迟疑片刻,才把沐蓉瑛的事说了,却见太后的手略僵了僵,正色说:“博尔济吉特的姑娘,不能嫁给汉人!”
“母后……这沐某祖上是前明的王爷,家产殷实,人也……”
“就算他是前明的皇太子也不行!”太后斩钉截铁地说,她收回了手,交叠在膝盖上,当她以这样的姿态说话时,就表示她是非常严肃看待的,“笼络汉人是好的,你要纳汉妃也没什么不行,但是满蒙女子决不能嫁给汉人!皇帝呀……汉人的男人有多少?满洲男人才多少?要是满蒙的姑娘都嫁了汉人,不用多久,这世上就没有满人蒙人,我们就要灭种了,全变了汉人去!祖宗家法还要不要了?”
“母后,儿子没要解禁,只有留瑕是例外,况且那沐某在旗,也是一样的。”康熙辩解,他一咬牙说,“况且额娘……也是汉军旗。”
太后紧皱了眉,康熙的生母确实是汉军旗人……只是太后在宫中这么些年,虽然不怎么管事,但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一辈子所执着相信的就是满汉大防,不可能因为康熙这一两句话就抛弃了。她说:“你额娘与这沐某不一样,你额娘祖上居住辽东,本就有满洲血统,那沐某可是个正儿八经的汉人,改得了籍、改不了血。再说满蒙不与汉人通婚,既然是禁令,那就不能有例外,你不用操心这些事儿,我自有打算。”
“母后有什么打算?”康熙见太后不能三言两语说服,便想迂回攻之,顺口问。
太后喝着茶,从碗盖上方抬起头瞪了他一眼:“你办事一点也不利索,挑了好半年了,也没挑出个影儿来。我已经给她拣好了人,说起来你也熟的,就是显亲王丹臻,他几年前没了嫡福晋,也只两个侧室,都还是格格74,没身份的,只大留瑕两三岁,我看顶合适。”
“丹臻……”
这次换康熙皱眉了,他本能地想挑些碴儿,可显亲王实在没什么能给他挑剔的。太后慢悠悠地喝着茶,带着一丝得意地说:“有什么能挑的?没有吧?相貌那是一等一,人品、见识也是一流,个性温和、办差认真,头上戴的铁帽子75,家底不比你挑的那个南蛮子少,他额娘是我打小看熟的小姐妹,热心,脸面人缘又广,就连你二嫂那咋咋呼呼的人都要敬三分,显亲王有什么能挑,你给说说?”
“显亲王跟我们太近了……”康熙好不容易才挤出这个不是缺点的缺点,他瞄了太后一眼,还是说了心里话,“给他,还不如儿子自己要了呢!”
太后动怒了,她面罩寒霜,严声斥责:“满嘴跑舌头76!你倒给什么蒙了心?满世界都知道她是你妹子,多少福晋来我这里撞木钟,求爷爷告奶奶似的要我把她指给她们王府。你要了她,让我拿什么脸面跟人家说话?不行!”
康熙默默地跪了下去,他心头有太多话,别人不能听、也没身份听,只能一股脑儿全部告诉了太后。他看着地面,娓娓道来:“留瑕……其实谁都不想给,想把她留着……喜欢她,不只是想她给儿子生儿育女,想跟她说话、跟她拌嘴,看她跑跑跳跳,数十宫妃、数百宫女中,只有她不拿儿子当皇帝,她也惹儿子生气,也让儿子担心,她不以儿子的女人自居,比较像是朋友。她会耍点小奸小坏,可是儿子不觉得讨厌,觉得挺可爱,像女儿、像妹妹,偶尔也像姐姐……母后,儿子何尝不明白她不能留在身边,可是,把她嫁出去何其难受?嫁得近了,时不时地要朝参、要大宴,儿子怕见了她,就管不住自己,到时,难堪的何止是她?她的丈夫怎么办呢?”
太后沉默了,看着那张苦恼的脸,与记忆中的顺治皇帝重叠了,她轻声说:“你让我想起你阿玛……不过,你会管住自己的,人哪,想得到的事情,总是防得密不透风。原先预料着千事万事,临事才发现是自己想得太多,心中有个提防,就犯不了傻。她虽长在南方,可毕竟是格格,科尔沁出来的,至不济也要是一品诰命,哪能嫁个没名没姓的汉人?你要把她远嫁也成,顶多,你给显亲王派个差使到南方,不见也就是了。”
康熙没有答话,直挺挺地跪着。太后拉起康熙,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拍着他的背说:“我们做母子也有三十年了,有什么委屈、痛苦,当着母后,没有忌讳的,自己一个憋着,要生病的,知道?”
“知道。”康熙点头,他有种冲动,想要扑在太后膝上大哭一场。八岁登基之后,就从没有那样哭过,因为从前,不知道情字如此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