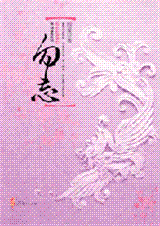清宫.红尘尽处-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佟皇后头七那天,他的父亲佟国维来见康熙,交给他一份中宫笺表。
康熙端正了脸色,皇后的中宫笺表向来不能轻用,只要中宫笺表一出,等同圣旨,虽然还要经过皇帝用印认可,但是中宫笺表所提的要求,皇帝不能拒绝,必须照允。中宫笺表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没有出现过了,只有第一任的赫舍里皇后用过一次,继任的钮祜禄皇后至死也没用过,佟皇后的中宫笺表,其实就等于是遗诏,她要要求什么?
康熙看完,讶异地抬起头,问既是舅舅、也是岳父的佟国维:“册封留瑕为慧妃?为什么?”
“回皇上话,大行皇后临去前告诉奴才,说这宫中没个主心骨是不成的,六宫之主,最要紧的是出身,论身份,没有人能比得了留瑕格格,而她这个身份入宫,也不能苦巴巴地从小妃子熬,该做个正主儿才是。”佟国维恭敬地回答,全然不敢对这外甥略大声些说话。
康熙心中一震,这将他心中的顾忌去了一半,留瑕一入宫就是主位,自住一宫,不用寄人篱下……康熙转念,留瑕没有政治后台,又连忙拒绝:“这,她不愿意进宫的!何苦勉强她呢?”
“回皇上话,大行皇后说,格格与您是亲戚,跟咱佟家也算一表三千里,攀着亲。要是格格愿意委屈,还请皇上做主,让她拜奴才或奴才哥哥为父,咱们一家也好亲近。这都还是其次,大行皇后还说,您不妨把这道中宫笺表跟老佛爷的赐婚旨意一并送给格格,让她自己选择吧?”
“她要不选这道中宫懿旨呢?”康熙心动了。
佟国维花白的寿眉轻轻一动,淡淡地说:“那就算皇上白疼了她了。”
皇后之死,像一块热炭投进表面平静的后宫,在底部冒起层层水泡,只在表面依然平和。正如佟皇后说过的,后宫不能没个主心骨,谁是下一个六宫之主?不只成为宫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外朝众臣最关心的。
台面上的惠荣德宜四妃瞬间成为众人压宝的对象,这一天,一群刚下值的内务府笔帖式闲着没事,在内务府衙门里磕牙聊天,把这四人分析了赢面,只见东首一个正儿八经上三旗出身的笔帖式先吸了鼻烟,“哈啾”一声打个喷嚏醒神,舒了舒罗圈腿说:“这四位娘娘,领的一样月例,我瞅着,赢面也是一样的。论年纪,姐儿四个都差不多;论子息,都生了阿哥、格格;论容貌,咳!那我不敢看,主子要把我眼睛挖出来。”
众人喷笑,另一个老些的笔帖式用烟杆子指着那人,笑着说:“还以为你见过娘娘,结果是放屁!有什么象牙,还不快吐出来!”
旗人忌讳多、礼数多,讲究的就是个说话的派势,连骂人都要绕个弯弯,刚才那个笔帖式也不生气,油滑地笑了笑说:“七爷,做什么说我是狗啊?犯得上吗?这不就说了。这四人里,倒还有些个差别,惠娘娘呢!占着明相国的势,肚皮争气生了大爷,大爷跟太子爷都是顶受主子喜爱的,惠娘娘的赢面原本最大,可惜就是这几年不待见。宜娘娘的家世也好,老爷子管着镶黄旗、哥子兄弟也都在旗里行走,人脉广、又得宠,五爷又养在老佛爷宫里,就是好饮酸,宫里人不喜欢,要不,高升应当是最有可能的。”
老笔帖式抽完了烟,将烟锅在炕边用力敲了几下,咳了咳才说:“其实呀,我倒觉得荣德两位赢面大,这两位虽不显赫,可性格好、人缘好、进宫又早,汉人有句话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小妾嘛,爱怎么宠是一回事,可这正头娘娘不一样,你说刚过去的中宫吧!人家虽说是国舅家的,可佟舅爷哪里比得上明相国?明相虽说现在不待见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句不恭敬的,明相的脖子都比佟舅爷的腰粗。可佟娘娘进宫就是主位,那惠娘娘还是生了大爷才升的妃,自打仁孝皇后过去,孝昭皇后又是个病秧子,这千事万事哪一桩不是佟娘娘打点,可你听说皇上特别喜欢吗?没有吧?所以我说,荣德二位赢面大些。”
一群人热烈地讨论起来,引得主官们也来聊几句,夏日的内务府,为了谁会脱颖而出执掌后宫,吵得不可开交。
六宫之事,暂时交还到宁寿宫由太后裁决,旧人尸骨未寒,群臣也不敢要求康熙再立正宫,康熙似乎不知道群臣的讨论,他依然二更左右就寝、四更起身,该做的事、该批的公文、该请的安……一样都不曾落下。只是平素起居的时候,常常一个时辰说不到一句话,要不就是抱着规矩发呆,或者走到乾清宫后,望着坤宁宫出神,魏珠与梁九功看着不对劲,连忙去禀了太后,可太后召了康熙来问,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儿子心绪不太好,过一阵子,会好的。”
人们原本也想过一段时间会好,但是太医院却开始惶恐起来,他们注意到康熙的食量日益减少,望诊、问诊、请脉时候都发现他的脸色苍白,神思缥缈,他的体重也开始下滑,魏珠等人帮他换衣裳时,偷偷摸了摸他的腰围跟上臂,明显跟从前有很大差别。
康熙对于他们的恐慌,似乎察觉了,又好像没有察觉,依然冷着脸做自己的事,什么都照行程来。整个七月,康熙都在紫禁城与殡宫间来回奔波,有时隔日去给亡者上食、当日回宫,有时直接住在殡宫旁边,五日一祭、十日一拜,各式各样的礼节、规矩多如牛毛,夏季的国事偏又不少,康熙起早贪晚、两头忙碌,加上心绪委顿,很快就得了风寒病倒了。
人们劝阻他不要再去殡宫奔忙,太子与大阿哥跪在他床前要求代表前往,可是康熙还是撑着病体策马前去。太后要拦,康熙却跪在太后跟前,冷冰冰地说:“母后,她陪了儿子二十年,儿子只剩这十日能陪她,往后就再也不能见了,求母后恩典,让儿子去吧!”
说到这个份儿上,太后还能拦什么?只得让他去了,但是康熙没有表现出任何寻死觅活、生死相随的样子,他祭完了皇后,回到宫中便宣布在皇后月祭礼后,出巡塞外调养身体。他的面容苍白憔悴,声音干得像是几天没喝水似的,冷酷沙哑:“朕南巡甫归,后丧刚满又出巡塞外,少不得有人要说朕没心没肝、不体谅民瘼,这里是直隶以北奏报上来的一份清单,北方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少了两成。朕此行所经,全都是亢旱之地,带的随从也不到百人,一个要去玩乐的人,会去这些徒增烦恼的地方吗?朕懒得多说,只你们自己想想,嘴长在你们身上,朕管不了,爱议论不议论,全凭你们自己良心了。”
众人连忙叩头表示不敢作此念想,康熙脸上没有表情,自顾自地起身,往暖阁去了。
天子居丧,以日代月,除服之后,宫中、国中虽仍要为国母心丧三年,但是紫禁城里那种哀伤、疲惫的气氛已随着白色帐幔、孝衣孝带褪去,给国丧拘束得发闷的人们,如开锁猴儿般,纷纷打理着,该洗的洗、该剃头的剃头,就是康熙,也觉得头上长出的短发讨厌,一除服,就让人来整理了头脸。
剃完了头,康熙叫来从前照顾过规矩的小太监,他跟留瑕很熟,康熙把桌上的两份旨意交给他:“你去朝阳门外码头等留瑕,她一到北京,就让她自己选要哪一道旨意,告诉她,要是选太后指婚的旨意,就不用来见朕了,省得两下难受,你去吧!”
康熙摸着剃得趣青的前额,脸上还是那样死板板的没有一丝表情,他想起了佟皇后,中年丧妻,他心中不能不感慨。走出乾清宫,绕到宫后,他望着不远处的坤宁宫,那里从赫舍里皇后去后就没有人住了,与乾清宫的人来人往相比,显得格外冷清,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在他最能大展身手的年纪,他身边的国母之位却空无一人……
思及此,他心中顿时空落落的,遥望着东方一丝随风扰戏的薄云,强烈的思念如果能写在云上、下成雨、落到留瑕手里,那有多好?他有太多话想说,可是太后跟妃子们不会懂;他有太多苦想倾诉,可是宫女、太监们不配听,这一切,都寄托给了留瑕,她会不会来北京?来了,会不会选择那道中宫旨意?还是……选择成为显亲王福晋,从此与他相望不相闻?
塞外.康熙二十八年秋
后丧足月后,康熙自乘了一辆朴素的车,带着一干侍卫跟几辆载着箱笼、饮水的车,轻车简从,往塞外去了。
天意秋初,出了京城往北走,过牛栏山、密云,一路巡视京畿防务,出古北口后,眼界顿时开阔,金风吹过千里关山,像有人拿着画彩,凌乱地在长草上染了淡淡金黄,这片草长马壮的景象,看在康熙眼里,却觉得烦忧。因为这片草原上今年庄稼欠佳,草黄得再美,又当不得饭吃。马蹄嗒嗒,踏过长草间,惊起一些黄羊、野鸡跟野兔,康熙约束着众人不许伤害动物,算是给皇后追福,只是这些动物都比从前来时见的干瘦,越想越烦,打马领着一群侍卫狂奔,才能稍稍纾解心中郁结。
康熙接见了一批蒙古王公,他们平素来见康熙,都带着大批礼品,穿金戴银的,可是此时相见,人人都是一脸疲倦,一见了康熙,全都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皇上!皇上!我们没法儿活了,没法儿活了呀!”
康熙讶异,连忙叫人把他们都搀起来,这一大票蒙古汉子半是真情、半是夸张,哭闹个不休,七嘴八舌的也不知说些什么,康熙听得一怒,气沉丹田,炸出一声怒吼:“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一个一个说!”
此时,一群男人中站出一个老福晋,她一手拉着一个男孩,伶伶俐俐地一福身,带着孩子们跪下说:“皇上,臣妾是喀尔喀部的格楚勒、丹津的妻子,臣妾的男人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是受了大清金册世守塔密尔的王爷。可那噶尔丹一个小杂种,又不是黄金血胤、又没有皇上旨意的,他凭什么来强占喀尔喀的牛羊草场?凭什么要我们给他低头?臣妾的男人跟孩子都叫噶尔丹杀了,一个老婆子,领着两个还不能拉弓的小孙孙,如果皇上今儿不能给臣妾一个回答,或者因为什么缘故不能帮臣妾报仇,臣妾不怨,只求皇上把佩刀赐给臣妾,臣妾跟两个小孙孙这就回去塔密尔,能用皇上的佩刀杀多少准噶尔人就杀多少,虽死无怨!”
说完,老福晋直挺挺地抬眼看着康熙,皱纹像刀刻似的镌在脸上,眸子里,燃烧着强烈的复仇意志。两个男孩跪在她身边,康熙还在考虑回复的答案,其中一个男孩用一口清朗的童音说:“您就是博格达汗吗?”
所有人都笑了,康熙对他招手,那男孩便跑上前去,康熙用流利的蒙语说:“我就是博格达汗。”
“我阿爸说,博格达山好高好高,博格达汗就跟博格达山一样高,可是,你为什么没有那么高呢?”那孩子问。
博格达峰远在天山,其实谁也没见过,只是听说它巍峨险峻,太宗与蒙古诸部盟誓之后,就被拿来称呼清帝国的统治者,形容皇帝如博格达峰一般伟大。康熙微笑,他对那孩子说:“因为我不是博格达山,我没有那么高,但是不管你在哪里,博格达汗都像站在博格达山上一样,能看见你、照顾你。”
“那博格达山,在你住的北京吗?”
“不在,它在天的那一头。”康熙指了指西方,仔细看看这个孩子,他有一张上翘的嘴,这个特征,几乎只要有博尔济吉特血统的人都有,康熙、留瑕还有太后、太妃都有一样的嘴,不过这孩子比康熙与留瑕更像博尔济吉特家的人,他的皮肤比较白,团脸、细眉、浅褐色的眼睛,组合成一张相当标准的蒙古轮廓。
“北京好玩吗?”
康熙哈哈大笑,他抱起那个孩子,让孩子坐在他腿上:“好玩,我的家有好多跟你一样年纪的男孩女孩,他们没见识得很,没见过大草原、也没见过成群的牛羊马匹,你跟我去北京,看看我的家、也跟他们说说你的家,好不好?”
“我的家……已经没有了……”孩子扁了扁嘴,明亮的眼睛悲伤地看着康熙,“有一群人来,把我的阿爸阿妈都杀了,把我的草原、我的小马还有我的小弓都烧掉了。博格达汗,你说不管我在哪里,你都能照顾我、看见我,那你能把我的阿爸阿妈还有我的草原都还给我吗?”
孩子的童言触动了康熙的心,他看着这个幼失怙依的男孩,只剩一个老祖母能依靠,他摸摸孩子的头,老福晋的目光中,蒙上了失去亲人的悲哀,康熙猛地想起自己当年,不也是失去父母、只有祖母吗?心中一沉,很快又清醒过来,可怜是一回事,但是现实还是现实,他还不能跟噶尔丹全面开战,他对老福晋说:“老哈屯,我还不能帮你抢回你的草原,但是,那一天不会太远的。我已经叫人给你们喀尔喀的百姓挪地方,就在古北口、喜峰口这些地方,你们先住一阵,不光是你,就是哲布尊丹巴活佛、土谢图汗他们,不久就会南下,带着你的孙孙跟百姓进来吧!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再好的水草地,不是自己的就不敢叫牛羊吃。”老福晋还很固执,她又跪了下去,“臣妾不敢要皇上的地方,只求皇上赐一些兵马,为臣妾的男人孩子报仇,臣妾的家族是黄金血胤,不能给人白白糟蹋!”
“你家是黄金血胤,可那与我满洲子弟有何相关?你格楚勒拿过银子养过我哪一旗的兵马?还是救过我哪一旗将士的生命?我是个男人不会生孩子,可我知道生孩子、养孩子不容易,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没有妻子儿女?你格楚勒孩子的命是命,难道八旗子弟的命不是命吗?你家族的命不能给人糟蹋,难道我八旗子弟就命贱,活该给你死去的丈夫儿子殉葬?”
康熙的问话一句比一句犀利,虽没有半个脏字,却冷得彻骨彻心,他的目光如刀,森冷严酷地望着老福晋。老福晋脸色一变,她在草原上位分极高,在康熙小时候就进京见过,二十几年过去,还一直记着那个“娃娃汗”的样子,根本没把康熙放在心上,却没想到当年的那个娃娃,今日如此难缠。原本想拿这些位分压着康熙让他派兵,但是站在这块由他控制的土地上,才发现这位博格达汗根本不把黄金血胤的名头看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