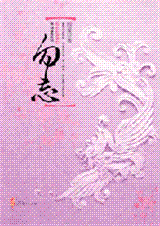清宫.红尘尽处-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这也很危险,若是引起血崩,那就是凶多吉少了。”敏嫔一口气说完,才发现太后脸色不对,讷讷地问,“难不成,贵妃娘娘肚子里的孩子……”
“御医说,就是胎死不下……”
太后颓然坐在炕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乱如麻,听着西厢里忙乱嘈杂的人声,打翻了水盆的、斥骂的、慌乱跑出去的……在那混乱的声音里,隐隐有留瑕的话音:“别乱……我还撑得住。”
西暗间慢慢静了下来,蓝嬷嬷过来东明间,眼睛红红的:“老佛爷,主子要奴才过来禀一声,御医刚才用了救母丹还有几味药,因为前头安胎药服得勤,只怕一时半刻没那么容易下来。主子说了,知道老佛爷心疼她,可她实在不能让您在这儿守着,心不安,老佛爷是不是……”
“我不走。”太后凄然,她心头莫名地一阵哀伤,哽咽着说,“就是回去宁寿宫,我也担心着。你告诉她,让她别惦记着,我就在这里给她诵经祈福,也好过在宁寿宫提心吊胆的。”
蓝嬷嬷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一蹲身退去。宫女们拿来几本留瑕常念的经文,在东明间里摆上蒲团,敏嫔与其他几个妃嫔也都跟着盘膝而坐,太后喃喃地诵读着经文。西暗间里却没有动静,银烛台上堆起高高的烛泪,太后等人累得在炕上打盹,不知过了多久,蓝嬷嬷唤醒了太后:“老佛爷……老佛爷。”
太后揉了揉眼睛,蓝嬷嬷扶起她,毕竟有年纪的人了,睡得不舒服,肩背都觉得很是酸麻:“怎么样了?”
“大人倒是平安……”蓝嬷嬷拭着眼泪,神色之间,很是不忍,“孩子可怜。”
“阿哥格格?为什么说可怜?”太后问。
“是个格格,掉下来一看,是给脐带缠死的……”
太后连忙套了鞋子就往西暗间去,进去一看,荣妃端了张凳子放在床边,德妃抱着留瑕,轻声唤着:“慧妹妹……慧妹妹……”
“留瑕……”太后过去,坐在床沿,只见留瑕的眸子里一丝神采也无,直勾勾地望着地上,长发梳成松松的辫子,几丝凌乱的发贴在额上,不哭不闹,却更令人心疼,“留瑕,你说说话呀……留瑕……”
留瑕苍白的唇上,露出一抹淡然的笑,却让太后不寒而栗,她轻轻地说:“这是,因果……报应……”
“没有的事,你不要胡思乱想,头胎本就危险,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呀!”德妃柔声劝说,可是与荣妃对视的目光里,都写着忧虑。这样把孩子硬打下来,对留瑕的身体,伤害是超乎想象的,她已经三十岁,就算勉强再有孕,能不能平安生下孩子,也在知与未可知之间。
“我……并不难过……”留瑕还是那样气若游丝地说,勉力撑起身子,德妃等人连忙扶住,她对太后说,“老佛爷,我是真的没事儿,这孩子,是我要还一条命。您别问我为什么这么想,只求您,再替我办个法会,超度这个孩子,也超度……前头刚过去的兰贵人吧!”
“好好……我一定让人把法会办得圆满,你放心、放心。”太后连声答应,虽然她觉得留瑕平静得太反常。
“这就好了……”留瑕露出凄凉而欣慰的笑,她又说,“别跟皇上说是死胎,他通医道,知道死胎比小产更伤身子,到时,定要追究旁人责任。我……是不愿再造孽了……请太后帮我圆着,就说……是我自己没注意,伤了孩子的……”
说完,她就疲倦地睡着了。众人轻手轻脚将她放好,屋子里早已收拾干净,只有那一丝挥之不去的血腥味,提醒着人们,刚才那一场生死交关的拉锯战。太后全都照着留瑕说的去做了,一封顾问行以太后语气拟的信,夹在要送去给康熙的奏折里,由快马送往蒙古。
蒙古。康熙三十五年夏
康熙知道消息,已经是将近半个月后的事情,他随即下令要顾问行把详细经过全都禀报上来,心烦意乱之下,他带着十多个侍卫,到草原上散心去了。
控着马缰,康熙静静望着草原尽处的霞光千里,火红的流云,宛如祈福的哈达,推挤着往天边流动,红云的末端,长风吹开千顷绿茵,像是有人踏马而来,金黄的阳光随着长风,吹到康熙马前,扬起马鬃,草波浮动,发出有如千万人齐声高呼般的声响。康熙直起身子,平莽荒野,却是一个让人不能不起雄心壮志的地方。
“那个谁,来唱首歌!”康熙回头,对一名刚选进侍卫的蒙古少年说。
那名蒙古少年憨厚地一笑,抓了抓头,用蒙语问康熙:“博格达汗,我唱《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可以吗?”
“你唱来!”康熙点头。
少年清了清喉咙,扬声唱了起来“……像两颗珍珠,像两朵金花,像两颗流星,那是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长大鬃似火苗,头颅像月牙,美鹿似的矫健,彩虹般的尾巴……”
一个明主与神驹的故事从少年嘹亮的嗓音里飘散出来。成吉思汗有两匹小马,围猎有功却没被主人奖赏,成吉思汗又疏忽了它们的辛劳,强行要它们继续前进。这对马兄弟心情郁闷,相约逃跑,找到一个水草肥美之地,住了三年。三年之内,成吉思汗懊恼后悔不已,而马弟弟因为不喜欢被人拘束,到了自由之地,又健康又快乐,马哥哥却思主恋恩,变得又瘦又病。马弟弟不忍心哥哥受苦,便自愿陪哥哥回到成吉思汗身边,成吉思汗看见它们回来,欣喜若狂,封马哥哥为神马,又把马弟弟放出去自由生活。八年之后,马弟弟再回到成吉思汗身边,帮助他获得许多猎物。
康熙默默地听着,这首蒙古长调音韵悠远,听起来有些吃力,但是从歌声中流露出的,是英雄与马的相知相惜。他看着天边滚动的云彩,想象着数百年前的蒙古草原,两匹小马偷偷地跑走,一匹毫不犹豫、一匹不时回眸,它们的马蹄踏在松软的黑色泥土上,分开青绿的长草……
那少年的歌已经唱完了,所有人都看着康熙,他说:“朕希望……朕死后,还能有人给朕做作一首这样的歌……”
“皇上寿与天齐……”一些从宫里跟来的侍卫们连忙拍马屁,康熙挥了挥手,要他们不要再说下去。
“成吉思汗,是个有福的人啊……”康熙轻轻蹬了蹬马,随意地走着,他的声音很低,几乎只是自言自语。
“皇上?”侍卫们以为他在跟他们说话,询问地喊了一声。
“没事……朕想事情呢……你们聊自己的事,不用拘束。”
康熙的目光落在远处,什么是为君之道?他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到底大清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他自登基以来便不停在问,可是,始终没有答案。
江南是大清、东北是大清、蒙古是大清、满人是大清、汉人也是大清,这么多的面向、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到底什么才是确切的大清?他的消息灵通,他的耳目深入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这些枝微末节拼凑起来的,却依然零散琐碎,难见全貌。
如果他知道大清是什么,那是不是就能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皇权?至高无上的皇权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在他手里,但是,皇权到底是什么?
“皇上,天凉,该加件大氅了。”侍卫们把带来的薄披风给康熙送上,他取过披上,猛然想到宫中此时该去避暑了。他惦念起自己一手打造的畅春园,是时候给太后住的地方搭上天棚防蚊了。
宫里的什么事都按着季节时令来,不到时令,就算是天气骤变,也不能随便加衣减裳,就是太后皇帝,也都要跟着既定的规则往前走,那是祖宗家法、是天地法则。康熙突然有个念头,连他都要去遵守规则,那究竟是他的意志主宰帝国的运行,还是帝国牵引着他的决策?是他驾驭帝国、还是帝国控制了他?
康熙陷入了统治的沉思,天道循环,有生有死、有兴有亡,是他刚好撞在明亡清兴的当口,成就了一番事业?还是这事业若不是他,就无法完成?他很不擅长想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他捧着头,想得头昏眼花,便决定放弃,留待回京有空再慢慢去想。他是个太务实的人,有时候务实得很没想象力。
康熙的务实表现在他对事物的看法上,每次看见一种稀奇的作物,都要先想它能不能有益民生,如果不能,那这东西大概就准备丢在荒山野岭里随便乱长。他希望每一分良田都要达到最高的效益、最好的产量,每一个大臣也都要放到最佳位置,去发挥最大功效……除了这些直接关系统治的东西,其他都是次等角色,有想没想不怎么有大碍。
霞光慢慢地暗了,一里外的大营亮起灯火,明晃晃地伏在草原上。他想起康熙三十年,前往科尔沁会盟的往事,他也是在这样的傍晚时分回去大营,明亮的火光中,留瑕在大营前等着他……
“……成吉思汗最喜欢的是忽兰皇后……”侍卫们的讨论飘进康熙耳里。忽兰皇后,是成吉思汗最深爱的女子,随军转战各地,从无怨言。她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死去,成吉思汗把她葬在冰缝之下,不让任何人打扰她的安宁,永远地,保存她的美丽。
“忽兰……”康熙念着这个已经汉译的名字,眸光又投向了已经渐渐消失的红色霞光,有人说,忽兰与乌兰是一样的,只是汉译不同,都是红的意思,康熙想起留瑕,心头一阵疼痛。
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康熙握紧缰绳,早先是抱着戏鼠猫的心态,他要全面摧毁噶尔丹,连一丝东山再起的机会都不给,此刻,却恨不能立马赶回紫禁城。他想起玛法太宗,当年在征明的时候,也因为爱妃宸妃重病,星夜赶回盛京,为什么他不能也学着跑回留瑕身边呢?
一想起太宗与宸妃、成吉思汗与忽兰,康熙就觉得十分不祥,两段霸主与爱妃的缱绻爱恋,最后都是以死亡诀别……地平线上的霞光已经消失了,草原上一片黑暗,只有满天星斗与明月权做照明。康熙看着那一轮从东边升起的皎洁,心中犹豫不决,明月升起的方向,是他魂牵梦萦的紫禁城,万仞宫墙内,月光,是不是也照在留瑕脸上?
“留瑕呀……”康熙柔声说。前方有一座敖包,敖包就是地界,但是蒙古人相信敖包有灵,只要奉上祭品,就会保佑祈愿的人。康熙驾马驰去,一下马,众侍卫都看傻了,只跪天、地、亲的皇帝,打下了马蹄袖,单膝下跪,郑重地把一把佩刀放在敖包前,才站起身,喃喃地说:“总理山河臣,爱新觉罗•;玄烨,伏祈天地神灵,庇佑臣妻博尔济吉特氏……”
一队军士护着四阿哥胤禛过来,众阿哥在营中都与康熙一同用膳,却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三阿哥这些日子身体不适,五阿哥不擅骑马,七阿哥腿有残疾,四阿哥只能亲自来寻。
康熙已经上了马,也不看四阿哥,径自狂奔而去,四阿哥只能与众侍卫追上去,跟随康熙已久的侍卫阿南达低声对四阿哥说:“四爷与其他爷这些日子可要变着法儿讨皇上开心。”
“怎么了?”
“皇上今儿接到了内廷急报,慧娘娘小产了!”阿南达叹了口气,把声音压得更低,往那敖包看了一眼,“刚才奴才们在后头细听,似乎是为慧娘娘祈祷,您瞧,皇上把那把红毛番贡的宝刀都献了敖包做祭呢……”
五月的克鲁伦河,正是水草丰美的季节,这条从汉书以来就有记载的河流,平时的水量并不大,只有在夏季才略为丰沛些。长河从肯特河往南折东而去,进入呼伦湖,随着湖水汇向额尔古纳河,再与黑龙江接头。
克鲁伦河对蒙古人有重要的意义,对有心称霸的人,更具意义。这条河,正是成吉思汗毕生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他的称汗与传说中的墓葬,都在克鲁伦河畔。
三百年前的一切都走远了,打马走过的成吉思汗已经无处可寻,他心爱的八骏马也杳如黄鹤,只剩下几匹听说是八骏后代的神驹,在每年祭拜成吉思汗时,被牵出来供人膜拜。这几匹马是从不上马鞍马具的,养得肥壮好看,只是没受过训练,自然上不得战场。
河上反射着粼粼波光,河边一溜儿生着野玉簪花,迎风摇曳。一只手擦过花瓣,轻轻摘起,淡淡的清香,为这条河所背负的历史,平添一分温柔。
康熙皇帝站在河边,在他身后,大军已经过了河,正在休整。在他们前方,就是噶尔丹原先的藏身之处,但是大军过河的时候,他们却丝毫没有临河而拒的阵式。康熙转着手上那朵玉簪花,淡淡地说:“不懂得利用地形,据河拒战,蠢货。”
一个都统过来,行了个军礼:“皇上,奴才来请示,何时出击?”
“明天,传旨下去,朕亲率中军中营,全部都轻骑简装,两日赶往克勒河,让喀尔喀的沙津亲王还有六额驸敦多布多尔济他们跟朕一起去。他们是地头蛇,打小在这河边长大的汉子,叫他们点起本部兵马,朕要追击噶尔丹。其余人等,可缓些,四日之内,到克勒河来寻朕。”康熙淡淡地吩咐。
噶尔丹已经逃走了,他没有想到康熙亲率的中军来得那么快,已经到了自家门口。半夜上山俯瞰,才警觉清军数量数倍于己,慌忙逃走,清军的探马去查看时,发现他们已经走了至少一天。
但是康熙并不急着去追,他看着自己的军队,全都是健壮男子,而噶尔丹的军中,还有妇女老弱,跑不远的。
次日清晨,康熙点起兵将,亲自去追噶尔丹,铁蹄如风,在王爷们的向导下,康熙很快就追上了被噶尔丹抛在身后的老弱妇孺。他们惊慌失措地站成一团,有些人拿起了刀,孩子吓得攀着母亲的脖子号啕大哭。康熙冷着脸,对土谢图亲王说:“让人去问问他们,噶尔丹还有多少人马?”
土谢图亲王答应一声,招手要人去问。喀尔喀与噶尔丹所属的准噶尔部在多年的征战中,早已杀成了世仇。几个喀尔喀军士问话时候,自然也没什么好口气,准噶尔人也不回答,只是拿着刀,冷冷地看着他们。
康熙眼看问不出结果,努了努嘴,叫过敦多布多尔济:“女婿,拿些金银把话骗出来。”
敦多布多尔济很年轻,才二十出头,也是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