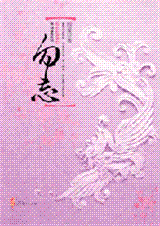清宫.红尘尽处-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错处来责骂,只是任她默默退出东宫殿,把满室的清冷孤寂留下。
就这样,留瑕整天都没有再进殿,康熙也不去召她。下午,他走出东宫殿,去纳兰洁住的长春宫,他知道她的尸身已在早晨移回家中,他不能为她举行盛大的葬礼,甚至不能亲临祭奠,至少,去上一炷心香,以慰芳魂。
惠妃不在,他径自来到纳兰洁住的小院。院门是开的,他直直地走了进去,里面的东西还是纳兰洁在世时的样子。这样秀气的少女闺阁,他只来过一次,那次是被她曼声清唱的纳兰公子词所吸引,那轻婉柔美的歌声、深切浓烈的意境让他想起康熙二十四年去世的近臣纳兰性德。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性德的堂妹,与她谈起性德,两人都觉得十分怀念,不由得大起知己之感。
初遇纳兰洁时,她只有十八岁,整个人就像是用水掐出来的,灵秀明慧却又郁郁寡欢,才貌兼备,那样秀气的轮廓不属于满人,若不是裙下那双天足,分明就是个江南闺秀。
康熙怦然心动,于是他常借机在纳兰洁教导三格格的时候去查三格格的功课,顺便和她说几句话。女孩子对这样的示好都是敏感的,她敏锐地锁住心扉,不再多说什么。
康熙的手抚过纳兰洁来不及带走的被褥,紧握着纳兰洁的那根芙蓉簪,说不上心碎,是这样若有似无的心恋,留下觉得揪心、抽去又感到痛心。芙蓉簪是他赐的,纳兰洁从没戴过,临去之时交代把宫中所有赐下的物品全数奉回,她不愿意穿戴宫中的任何一样物品离开人间。
“洁……你恨朕吗?”康熙轻轻地问,长长一叹,起身离开内寝。纳兰洁就像一层薄纱罩在他的心上,她一死,那层纱就散成不知去处的轻烟,无处可寻。
走到另一头的次间,镶着螺钿的八仙桌上放着几碟康熙没见过的点心,还有一碗龙井。他将手指搭在茶碗上,早已凉了,空气中有残存的沉水香气,一旁熄灭了的火盆里,有烧过纸的痕迹,一片被烧焦了边缘的纸落在康熙脚边,依稀能辨认得出来,是“惘然”二字,那熟悉的行书……
“留瑕……”康熙拾起那片纸,确实是“惘然”哪……他想起自己是怎样要求留瑕去说服纳兰洁入宫为妃,留瑕起先不愿意,他明着赏、暗着施压,逼着她做他的传信使者,留瑕几乎每隔两天就要来这里一次……带着他赐的东西、写的书信。
明间的地上投入一个阴影,康熙抬头,那苍白的脸庞与冷漠的气息,似乎是在嘲笑他来此地的徘徊。留瑕冷冷地说:“皇上来了?”
“这些东西,是你祭的?”康熙一摆手,指向那桌点心。
留瑕点了点头,依然平静地说:“这是南京的点心,宫里不会做。”
康熙默默地坐下,望着窗外的雪地发呆。留瑕看着空无一人的寝室,心中升起一种冷酷的悲哀,她是狠心的,没空去为纳兰洁难过,就算心绪不佳,也单单只是近似于“兔死狐悲”而已。
留瑕其实不喜欢纳兰洁,也说不上讨厌,就是没有办法跟她交心。虽然都曾在南方住了十多年,也许,她们曾经在苏州的哪条河上擦身而过,也或许在江南四百八十寺的其中一座中见过,她在康熙的压力下也与纳兰洁多有往来,但是就是亲密不了。
因为当纳兰洁进宫时,所有人都说:“啊!与留瑕格格一样的……”
虽然她们很相似,虽然她们都来自南方,然而,太过相像的两个人,要不是一见如故,就是点头之交。正因为太相像,因为两人都不愿意做对方的影子,所以每次话到嘴边,都要保留,怕对方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不过两人都知道,要知道对方想什么,问自己就知道了。
当然多少还是有不同,留瑕是黄金血胤,而纳兰家族只是正黄旗人,虽说祖上曾经出过孝慈高皇后,但毕竟也远了;留瑕心中没有人,而纳兰洁心里藏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康熙对她的关爱,只是带给她更多压力,她不想承这个恩,却又不能不受,无处可话衷肠的结果,是憋坏了自己,生了女儿痨……
留瑕与康熙,一站一坐,都想着纳兰洁,却想着不同方面的她。虽然无话,但是在无形中,都请纳兰洁做陪客,寂静,却不寂寞。
等到康熙回过神来,留瑕不知道何时已经走了,她骑了马,奔驰在京郊。她向太后请了一天假,先去明珠府祭了纳兰洁,把太后赏的东西交给明珠府的人,就独自骑着马往郊外去了。她需要好好想想,纳兰洁死了,她怎么办?
想了很久,始终没有头绪,拨马回头,她在城中寻个客栈住下。晚上,就出去王府井逛了逛,却听一阵丝竹盈耳,抬头看去,是有个戏园请了昆曲班子,唱的是《牡丹双梦》,是从《牡丹亭》中节出的《惊梦》、《寻梦》,最是考验正旦唱功的。留瑕在戏园子里找个雅座,园子里掷手巾把儿的、卖糕饼的、卖戏考的……吵闹不堪,留瑕傍着栏杆,仔细地听。
台上的杜丽娘是个干旦,大约有三十多岁了,听说,干旦娶妻后,嗓子还会更开些。只是这个干旦实在唱得不用心,虚晃一招就过去了,留瑕看着没意思,早早地离开。
客栈离王府井有些距离,离了吵杂喧闹的王府井,就进入安静的民宅,有种恍惚如梦的感觉。她轻哼着《惊梦》里的调子,今日的青春貌美,十年、二十年后还在吗?就算永远美丽,又给谁看呢?多希望,这个冬天不要离去,人生,有几个二十一岁?
躲在皇宫里,为的是避开那些无谓的争斗,身为女官,是没有人会把她当敌人的,交际也轮不到她。然而,未嫁时躲得过,出嫁后就是自己不愿意,也会因为丈夫而被迫去交际应酬,更觉得郁闷的,是自己还遇不见知心之人。
下一个冬天,她若是不成为妃子,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王公贵族的妻子,庸庸碌碌地给那个男人生儿育女、穿金戴银地给他争脸,渐渐地,变成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女人,她要胖了、丑了、俗气了,嘲笑今日清醒的自己庸人自扰、伤春悲秋,想起来就害怕。
天上飘下了茫茫大雪,提起手,如葱般细长的手指在雪的陪衬下更显白皙。她在空中一捞,感觉时光如雪,从指缝间流走,多可怕?
雪花一样穿过了康熙指间,他一向喜欢看雪,只是今日的雪,像是纷纷而降的冥纸,是给纳兰洁送葬的。
梁九功踏雪而来,康熙劈头就问:“留瑕去哪了?”
终究是不能不问的,批奏折时,没有她磨的墨就觉得胶滞难写,笔尖没有她挑过,自己伸手去捻,倒把一支好端端的湖笔弄成了岔尖。
“回皇上的话,太后老佛爷准了格格今日出宫去祭洁姑娘。因是准了整天的假,所以明日才会回来。”
“荒唐!”康熙痛斥,梁九功缩了缩肩,康熙阴沉地说,“她一个女孩子,孤身在京城游荡成什么样子!你去各个门问,看有没有她回来的记录,要没有,让九门提督派人把她逮回来!”
“奴才刚才已去问过侍卫处,格格是中午出去的,还没见她回来,只是……皇上……惊动九门提督……”梁九功迟疑地问。
康熙自知失言,惊动九门提督寻人是大事,若不是钦犯就是大官,留瑕两者皆非,甚至也不是宫妃,是原则上可以自由出入宫廷的女官,没有理由去惊动九门提督。康熙恼怒地跺了跺地,转身回殿。
梁九功已经服侍他很多年了,这样自然就是摆明要等她自己回来,他看了看天,格格……怎么还不回来呢?
留瑕隔天早上才回宫,她先回东宫偏殿换了衣服,赶到太后暂住的西宫殿缴旨,说了纳兰洁的事,正说到一半,就听通报,康熙来请安了。
太后指了指留瑕,抿着嘴说:“你主子来寻人了。”
“倒霉……本想悄悄溜回去的……”留瑕扁扁嘴。不一会儿,就看见康熙风风火火地走进来,熟练地向太后请安、入座,经过留瑕身边时,偏过头瞪了她一眼,留瑕只是装作没看见,垂首站在旁边。太后捧着茶微笑,说了几句话,就推说有些倦了,要康熙回去。
康熙告辞,留瑕还在偷看太后的反应,没有移动,康熙咳了一声:“留瑕!”
留瑕依依不舍地跟着去了,临走还要回头看看太后,太后故意板起脸,挥了挥手要她快去,等到她出了视线,才笑了起来:“真是一对儿活宝。”
康熙走得飞快,穿着旗装、花盆底的留瑕几乎赶不上,气喘吁吁地追了一阵,才好不容易赶上,康熙冷冷地问:“去哪钻沙了你?”
钻沙,自然是暗指对方是虫,是京里人不带脏字的奚落。通常留瑕一定要先跟他辩一顿,然后才回答他的问题,不过这次留瑕却叹口气,闷闷地说:“奴婢贪玩了,任凭皇上责罚。”
“这回这么乖?你真的是留瑕吗?”康熙转过头,似嗔非嗔,却看见她若有所思的神情,气就消了一半,柔声说,“怎么了?在城里受了什么委屈吗?”
“不是,只是在城里转了一圈,回来,就觉得宫里好像有点不同了……”留瑕低声说,一方面虽是真心话,另一方面,则是她知道若是跟康熙直来直往,他又要逗她,那就没完了。
康熙闻言,静静地看着她,留瑕半天没听见他的声音,偷偷抬头,看见他的眼光里,似乎有些悲伤,良久,才艰难地说:“朕……留着你……太久了吗……”
留瑕不答,在他身边,已经三年了。说实在的,有时也觉得烦闷,这就是为什么总是跟他没大没小的。她不能找太后、太皇太后或者妃子们拌嘴,太监、宫女们又都对她百依百顺,只有他才会跟她闹着玩……
“不过……奴婢离了紫禁城,还有哪里可去呢?”留瑕自嘲地笑了一声。
康熙说不清胸中那种复杂的心思是什么,有点欢喜,因为她话中似有留恋;有点惆怅,因为她话中有些无奈;有些悲伤,因为她不是说,“奴婢不想离开皇上”。
“留瑕……”他轻声唤着,看见她好像快要哭了,不知怎么,就心软下来,像偶尔哄着自己那群小格格,他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好了,只要你还想在乾清宫,朕就不会让你走。”
留瑕无力地笑了一下,皱了皱鼻子,故意地说:“那我偏要说不喜欢乾清宫呢?”
“那朕就让你在乾清宫,待到喜欢它为止。”康熙双手抱胸,微笑着说。
“喜欢了,可就不想走了。”
“那就待在乾清宫一辈子吧……”康熙说,带着笑,眼神却认真。
留瑕想了一想,耸耸肩:“那我可没办法说,一辈子,这个承诺太长了。”
康熙不语,只是放慢了脚步,好让留瑕能跟在他身后两步之内……
慈宁宫.康熙二十六年冬
“留瑕。”留瑕才刚到康熙床前,就听见他出声喊她,连忙应了一声。康熙把帐子一掀,对坐在帐下的梁九功说:“梁九功,你出去。”
梁九功迅速起身,连坐得麻木的腿都还来不及动一下,就赶忙出了内寝,顺便把夹门带上。留瑕不解地皱了皱眉,他在起床之后确实常跟她说话,但是从没有把坐夜的宫女或太监赶出去的理。她默默地侍立在旁,感觉康熙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自己身上,暗自思量着,木着脸不发一语。
“你坐到床边来。”
留瑕心头一跳,她抿紧嘴唇,正色说:“奴婢不敢。”
“朕有话对你说。”康熙的声音中加了一点冷峻,被审视的不悦之外,留瑕另外觉得有种威压的气氛弥漫开来。
她站直了身子,音调平直:“奴婢站着也听得见。”
“过来!”康熙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刚睡醒的声音还模糊,这两个字却带着无可商量的意思。留瑕愣了一下,飞快地看了看康熙,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就连平日装饰用的微笑或冷笑都没有,她的心跳得快了,脸色却苍白,迟疑地蹭过去,缓慢而僵硬地坐在床的另一头。康熙斜倚在几个皮枕上,静静地打量着她,半晌,才笑了一声说:“真稀奇,朕的山鹊儿哑了?”
“山鹊儿在南苑,宫里没有。”留瑕听他又拿她开心,别开了头,偷偷地松了口气。
山鹊是一种讨喜的鸟,也叫山喜鹊,叫声清脆,虽说是灰扑扑的羽毛,看着不起眼,但是模样细致俊秀,很会看人颜色,不像鹦鹉那么不凑趣、吵得心烦。康熙有一次去南苑避暑,听太监们说起这种鸟,当场就说:“这不跟留瑕一个样儿?留瑕,你改名叫山鹊好了。”留瑕听他拿山鹊儿比她,气得躲回太后身边去,好几天都不到乾清宫。但是,这“山鹊儿”的绰号却传遍了宫中,就连太皇太后有时也都这样喊她。
康熙微笑着看她,乍然发现她已经变了许多,略显稚气的双颊瘦了些,端端正正地坐在床边,首饰穿戴都很简洁,真像山鹊一般透出低调的俊秀来。他心头一动,随即又定了定神,用一种长辈的口气,正色说:“太皇太后昨儿说起你的婚事,老太太一向疼你,朕与母后商议,你的婚事只怕是老太太心中挂记的。这些年在朕身边张罗诸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朕实在舍不得你。只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母后见的外臣少,就把你的婚事交给朕了。再说你在乾清宫,见人也方便些,你倒是说说,喜欢怎么样的人?”
留瑕一愣,没想到康熙是这样的心思,心头一松,低了头说:“奴婢一向常见的外臣就是大学士们,自己也不知道喜欢怎么样的人。”
康熙轻笑,坐起身子说:“女孩子家脸皮子薄,这朕是知道的,又不是叫你现在就指名道姓地要人,你自己打算打算,要有了喜欢的,就给朕回话,朕要瞧见了好的,会给你个眼色,自己找机会送个茶水什么的,相机瞧一瞧,瞧中了,朕让母后寻他们的娘说话,嗯?”
留瑕知道这时候应该要说些谢恩的话,但是一开口,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又不能不说,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了声:“嗻。”
“你今儿怎么啦?可从没听你说过‘嗻’。”康熙起身,已经把脸浸到水盆里,留瑕回过神来,连忙把面巾递上去,康熙揩着脸说:“‘嗻’是奴才的用语,这个字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