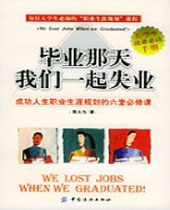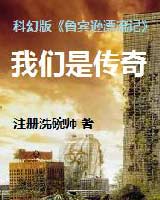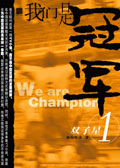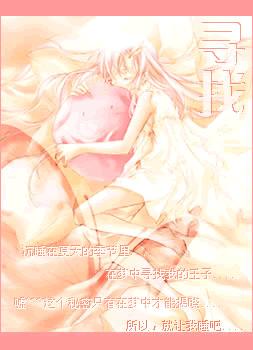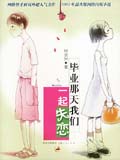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们无不希望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可是人们所能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稀缺的概念。由于人的物质欲望无限,稀缺就永远存在。各人努力用各种方式在市场上赚钱,就是为了丰富物质享受,减少自己的稀缺。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要从根本上缓解稀缺的问题,还得依靠科学技术。所以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说。确实,近一二百年以来物质文化的进步都是靠的新科技。如果没有新科技,我们非但不可能享用汽车、电视、电话、音响,恐怕连能否吃饱肚皮活下去都是问题,因为粮食增产是靠了化肥和绿色革命,这都是科技成果。对于未来,我们仍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它不断帮助我们克服稀缺,使物质享受越加容易获得。
是不是一切新发明新工艺都能够克服稀缺增加物质财富呢?并非如此。有些新发明,构思虽然巧妙,可是成本太高。换句话说,它消耗的稀缺物品比之它能提供的稀缺的物品更多。如果社会接纳了这种新发明,社会不是变得更富足而是更穷困。所以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经受市场的淘汰。
能否为市场接受的标准是此项新技术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或者说收入减去成本是正还是负。如果是正,说明此技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否则则是消耗了社会的财富。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钱可以通过商品的价格正确地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或者说,价格必须正确地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谈到这里,我们又面临了什么是正确的价格的问题,又发生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以及如何度量价值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不要说科技工作者,连许多经济学家碰到这些问题也感到棘手。有的经济学家花了一辈子时间试图搞清楚它,有时他们自己感到似乎弄清楚了,可是未能向他的学生说明白,更谈不上让广大公众去理解。好在现在独辟溪径,找到了一条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的简捷明了的解决办法。
在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内,商品供不应求时会引起价格上升,于是生产被激励而消费受压制。如果供过于求则发生相反的过程。所以通过价格的调整可以实现供需均衡。此时出现的一个特点是按照均衡价格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而且也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一切商品。于是任何甲商品可以交换任意乙商品,只要先将甲商品卖掉,再将所得的钱去买乙商品。他们的交换比例反比于它们的价格比,即价格高的商品用较少的量可以交换较多的价格低的商品,当一切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自由买卖,且价格达到均衡价格时,钱在客观上成为度量价值的单位。这是一个事实,用不着任何理论去证明。相反,如果我们提出不同于均衡价格的另一种价格理论,不论这个理论如何雄辩,在事实上它不能用来实现商品之间按这种价格来交换,这种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有何用处!
我国目前的价格比之过去已经更接近于上面提到的均衡价格,因为绝大多数商品已经由市场来调节价格。但仍不能说已经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黄金、外汇都还不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还对住房、交通、邮政(指1996年12月邮资调整之前)等进行巨大补贴,银行利率还在国家管制之下,这些价格扭曲将波及到一大批商品的价格,使得衡量一商品的价值发生困难。在一些重要的经济评价中要用到所谓“影子价格”,即设想在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之后的均衡价格。
有了均衡价格理论作基础,从事科技开发的同志就会运用价格来测定自己成果的价值,并进一步自觉用市场和价格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方向,使之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应该承认,我国有一大批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成果本身缺乏市场价值。换言之,它本来就不是生产力。相反,凡是经济价值高的成果一般都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投资的一方,帮助它投入生产。当然,市场不健全,信息沟通不够,资金渠道不畅,缺乏企业家人才,也都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但不能否认,成果本身通不过市场检验也是原因之一。
市场是多变的,价格也经常在变化。一项成果是否真正是生产力要经受一个变化中的市场的检验,似乎缺乏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规律也与自然规律不同。科技成果是否是生产力确实会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由于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竞争性产品的出现,当地资源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各种原因,使得价格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成果本身的价值也在变动。今天有利的成果若干年之后可能变得不利。长江三峡有一千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发电是三峡工程的一项主要经济产出。但三五十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新能源,电力价格对于其他价格降低的话,三峡的经济性将随着发生变化。价格变化对一项成果经济效益评价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像三峡工程这类将继续发生作用几十年上百年的大项目更是如此。这里讲的是由于时间不同,使得成果的价值发生变化。空间不同,成果的价值也是不同的。一项在美国能取得巨大经济效果的新技术,搬到中国来用就未必适用,因为两国的价格结构不同。譬如说,美国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比,比之中国的来得高。因此多投资以节约劳动的技术在美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在中国就未必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不少企业见到外国技术先进就引进到中国来,结果却并不好,成为盲目引进,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一项技术的成败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价格结构有关。过去我国的价格严重扭曲,许多经济评价失去了客观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迷失方向。可见价格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依赖于市场,不仅是它的商业化必须靠市场的作用,它是否确是潜在的生产力,也必须由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来判断。而且大量科学技术是受利润机制所驱动的。失掉了市场,科学技术将失去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也有必要学习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便能更自觉地用经济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防止劳而无功。
1995年5月25日
理性的谬误
20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们,全面地转向了以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先就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普遍进一步实施将企业所有权从国家转向个人,而且,放松管制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这个全面转型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不用说原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就以最成功的中国的例子看,虽然我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但潜在的问题仍旧深刻地困扰着我们。通货膨胀、失业、贪污腐败、三角债、企业亏损、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社会治安恶化、赌博娼妓和风气恶化,这些问题在改革以前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似乎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如何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转轨到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将发现这个体制改革却相当顺利。1949年解放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及少数大官僚的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逐步扩大到棉、油、肉、茶、糖。1956年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将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实际上是政府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以低价收购变成国营企业。这几个重要步骤的实施并未遇到有力的阻挡,相反,全国人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致拥护取消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实施永无失业恐惧的终生雇佣制,而且人人有免费医疗,不再有通货膨胀。比较一下这一正一反的制度改变,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认为基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归纳,叫“理性的谬误”。
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用理性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学科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为可以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
不要说我们这些智力平常的人,一代哲人爱因斯但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热心拥护者,他曾视为明白无误的是“人类的理性一定有能力找到一种分配方法,它将和生产方法一样地富有成效”。他还写过“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为获利而进行的生产”。我国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赞成用工程的方法来设计和组织社会活动,把社会活动看成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控制的系统工程对象。经济控制论这门课在许多大学里被传授,并列入了教委的大学教学课程之中。
为什么社会工程的想法行不通?要把这道理说透是很难的一件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那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幸的观念》(The Fatal Conceit)(有内部发行的中译本)就是专门论证此事的。凭着哈那克的学问,他还写了相当于13万中文字的巨大篇幅才算交卷。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历史事实的反省,建立起自由经济的概念不是容易的事。根据我自己的学习,倒觉得复杂的论述可还原为基本的几条原理。首先,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正确”的先知,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同的对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像没有人能预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管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但一切腐败都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
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理来说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第三者去介入。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们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价格管住。
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产所有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止各种欺骗和不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还相当渺茫。
1995年6月3日
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
1995年6月,我到南方出差,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住旅店时发生了完全不应该发生,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在退房结算时忽然冒出一笔保险费。钱数虽然不大(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深究),却完全违背了商业规则。因为保险是顾客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怕因风险发生某种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交易,万一风险成为事实时保险公司要负责赔偿。决不会有任何人在事情过去之后,因为庆幸自己没有出事而向保险公司纳贡的。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正是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保了险,事后却要求顾客支付保险费。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事先不声明保险,万一出事保险公司可以赖帐不赔。而我们手中又没有任何凭证可以作为索赔的法律依据。所以这笔“保险费”就成为保险公司没有赔偿义务的“乱收费”。
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顾客有权利投保,也有权利选择不投保。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根本无权强制顾客保险。(养老保险是例外,因为除非夭折每个人都会变老)即使顾客自愿投保,保险公司也应先将保险的条款交代清楚,特别是发生损失时的赔偿金额,同时保险公司应该将附有公司签章,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书交给顾客保管,作为万一出事时索赔的根据。而这一切在我们住过的旅馆统统都没有。所以保险费成为乱收费的一种借口,附带说一句,现在坐飞机保险时的保险合同往往和客票用订书机订在一起,旅客乘飞机时带上了飞机。万一飞机摔下来,保险合同一样粉身碎骨,罹难者的亲属根本无法证明他曾保过险。在我们所到之处,乱收费借保险费的名义能够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