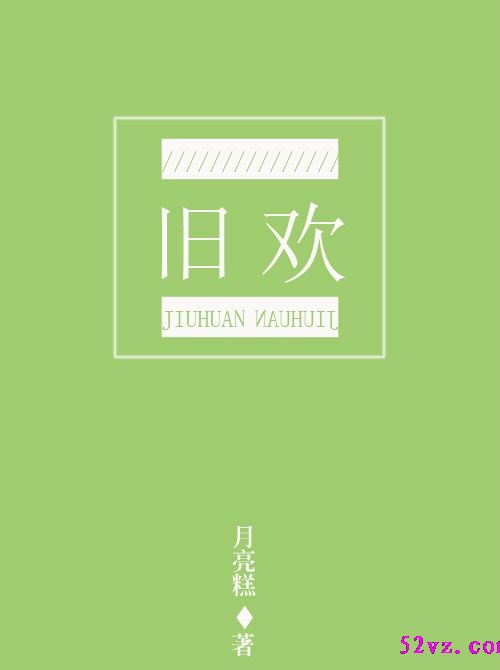俞欢欢 恶作剧天使-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都是这样,就被逼疯了。
我不要,我不要。
社团联的下场已经叫我确信,阿修绝对是靠眼神就能赢的男人。
我想试着作若无其事状站起来,就听到阿修低低的命令,
“不许走。”
乖乖坐下,陪笑。
“为什么要撒谎?”他把头凑过来,几乎抵着我的额头。
小小茶几对长手长脚的他来说,根本形同虚设。
我在精神上已经崩溃,跟气场强大的人对垒,我必死无疑。
“怎么不说话?”他把声音放低,听在我的耳朵里,居然还有点点蛊惑的味道。
“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很好听啊?!”
只要想逃避什么事情,就会开始习惯性的语无伦次。
但这次,绝对适得其反。
阿修站起来,也不再看我,只是说,
“祁萌,你真叫我失望。”
他默默地走开。
我的心好像瞬间被击穿了。
连我自己,都对自己的行径感到可鄙起来。
我似乎,的确做了一件满不上道的事情。
可是,又说不上来,症结在哪里。
我突然笑不出来了。
胸口好堵。
少青国手
我常常对于自己惹别人生气觉得惶恐。
而更加惶恐的是我还不知道对方生气的原因。
但骗人总是不对的。
所以我打算找阿修和解。
居然找不到他。
一直到周五,他都没有来读写会。
我百分百地肯定,他绝对还是在生我的气。
那么明天的安排呢?
也许他一气之下决定取消。
我有点后悔没有告诉他,我对明天其实怀有期待。
晚了。
恹恹回到家,我妈说,“妹妹头很多天没有回来了,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再度无语。
上海人的家里,父母亲总是喜欢叫儿女小名。
哪怕我们已经是20来岁的成年人,在他们眼里,还是点点大的小毛头。
像我哥哥祁连,仪表堂堂,英俊帅气,微微一笑就迷倒众生。
谁会晓得,他的小名叫毛毛。
记得他念大学时,有个同寝同学来串门,听到老妈叫他毛毛,当即笑翻。
搞得我哥极为狼狈。
他后来哀求老妈不要再在外人面前叫他小名。
结果老妈一瞪眼,“毛毛就是毛毛,不叫这个叫什么?!”
害我哥郁闷好久。
就好像我的小名,叫妹妹头。
听上去就是有哥哥的人,而且老给人一种长不大的感觉。
有点像洋葱头、萝卜头……长到一半发育不良,僵掉的样子。
Apple有次来我家里吃饭,也入乡随俗地叫我妹妹头妹妹头。
乐的很,好像占了十足的便宜。
她还跟我总结,上海小孩的小名都具有共通性,比如十户人家起码有4户孩子小名叫毛毛。
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的哥哥,小名正是叫毛毛。
反正,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见面。
吃完饭,我妈说,“妹妹头,你去洗碗。”
“哦。”回来一次,做点家务是应该的。
洗到一半,电话狂响。
老爸在外面讲了一会,喊我,“毛毛的。”
我叹口气,我发现我老哥每次电话回来都很会挑时间。
不是我在洗澡就是在WC,今天又是……
我把手上的洗洁精急急抹在围裙上,冲过去接过听筒。
那边传来老哥嘿嘿地笑声,“妹妹头,我猜猜,你这次是在上大号还是在……”
“…洗碗。”我服了他。
“怪不得今天你没抓狂。”
我几乎看到他天生的冲天发耷拉下来的失望相。
“怎么拉。”我问,“长途很贵的,有话快说。”
“嗯,我下周要回来了。回来参加一个画展。”
“老哥,你…还好吧。” 我觉得他的口气听起来怪怪的。
“还好还好,就是初恋嫁人了。”他轻笑着说。
那是我在一贯阳光的祁连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落寞。
“也好,回来疗伤吧。”我轻轻地说。
“妹妹头,我发现你突然变温柔了,好恐怖。”
我吐血,有时候对贱人太好得不偿失。
“你别回来了!”咆哮。
怒气冲冲地回去洗碗。
气归气,还是惦念着老哥。
是那个女孩子么,哥哥大学时候回来说遇到的奇特女孩。
他说,那个女孩胖胖的,但个性很可爱。
然后,他总是提到她。
她瘦了,她在减肥,她画画很有天赋……
她居然也和我一样,想做插画家。
我依稀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做莲。
能让和煦阳光般的哥哥黯淡的,会是什么样的人?
“妹妹头,碗刷好了没?”老爸又在叫。
“还没,怎么了?”
“毛毛又叫你听电话!”
我……我晕!!
气急败坏冲出去,“又怎么了?”
“突然想到,你的床再借我用用。”老哥的语气很诚恳。
这让我生起不祥预感。
“别告诉我你又带回来什么破石头烂树根。”
“bingo!还有,不是破石头烂树根,是山石根雕。”他笑。
又要把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放在我床底下,想都别想。
“不借!”
“妹妹头~~”
“不借!”
“妹妹头!”他哀求。
“不借!!!!”我吼~~喀嚓挂掉。
抓狂了。
他回来疗伤,我就要疯了。
回去继续刷碗。
手才刚刚浸到肥皂水里,电话又震天响起来。
我这个怒啊!!真犹如黄河彭湃,一发不可收拾。
三两步蹦出去,对着要接电话的老爸吼,“我来!!!”
不顾被吓到的老爸,拎起话筒就大吼一声,
“想用我的床,门都没有!!!!”
话筒那边一片寂静。
我继续炮轰,“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心软了,装可怜没用,老娘我不吃这一套!!”
“……你果然是个流氓。”熟悉的低沉嗓音,带着戏谑口吻。
火星撞地球,世界一片白茫茫。
我彻底暴走。
是阿修……
“谁要用你的床?”他的声音满是笑意。
“我,我哥。”我嗫嚅。
“哦。”
“明天是不是不去了?”我问。
“为什么不去?”他反问。
“我以为你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
这下,我真是搞不懂,是反问还是疑问了。
我说,“我不知道。”
他叹口气,“你是笨蛋,当然不知道。”
无端端被指责。
却无法反驳温厚声音的主人。
“明天早上6点,穿球鞋和最舒服的衣服,校门口见。”
“最舒服的衣服?”我想了想,“睡衣?”
“……笨蛋,”他骂,口气里却还是含有笑意,“不许迟到。”
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
怅惘的我独自伫立。
仿佛又出了次丑,可心里又有说不清的高兴。
晕晕陶陶的。
电话再度响起,我接起来。
“妹妹头……”我哥可怜巴巴的声音,“前面打不通……”
“什么都别说了,床借你。”
“……―___―”
仔细想一想,6点这个时间,由阿修提出来就很奇怪。
至少我周六的生物钟就从来没有设置在中午之前。
何况阿修那种时时刻刻把睡觉作为生命运动的人。
这让我相当好奇。
我们所要去的地方,绝对是一个压倒性战胜人类本能的去处。
但是,我忽略了一点。
是压倒性战胜阿修的本能,而不是祁萌的本能。
所以,周六,我醒来时闹钟已然指向6:00。
大惊。
阿修的急冻死光再一次,我就可以直接迈入冷冻人的行列。
心急火燎地洗脸穿衣。
一路飞奔到学校。
远远看到空荡荡的校门口,有个高瘦男生坐在花坛边的栏杆上,棒球帽的帽檐压得很低。
周末清晨,一贯郁郁葱葱的校园弥漫着浅浅雾气。
看不清那个人的脸,然而他那种淡定的坐姿,浑然天成。
仿佛和世界的宁静混合在一起的人,只有阿修。
我跑过去,呼呼喘气。
他抬头,看我,说,“你迟了。”
这样低沉淳厚,隐约还包含着点点温情的声音,就如同清晨尚未苏醒的太阳,和煦,温暖,抚慰人心。
我不由自主地停住了呼吸。
他意外地没有再奚落我,只是从栏杆上跳下。
“走吧。”
他转身,微微弓着背,在我前面走着,宽宽的肩膀可以完全遮掉我的视线。
阿修的着装一直都是宽松型的,但又不是嘻哈那种夸张风格。
皱皱的棉布衬衫,破仔裤,大码的毛衣,显出他瘦削却不单薄的身形。
漫不经心,却格外妥帖自然。
这样的季节,早晨仍然有些寒意,他瑟缩地把松垮垮的棒球外套的扣上,看着自己呼出的白气默默摇头。
我偷笑。
他停住,几步走回来和我并肩。
“笑什么?”他问。
我呆住。
简直不能在他背后做一点小动作。
“去哪里?”
“到了你就知道。”他托着头若有所思地微笑。
今天阿修的目光特别柔和,好像沉浸在某种美好的回忆中。
他的心情出奇得好,在这样颠簸的公车上,他居然也没有丝毫睡意。
但我真的忍不住睡着了。
我们要去的,一定是个很美的地方。
也许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会看到大片的桔梗和三色堇,浪漫得不行。
不过,还是大意外。
我张大嘴看着眼前的景象。
“你确定…这个…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我十分怀疑自己还在做梦。
“是啊。”他说,“很酷吧。”
如果还在做梦,那么一定是恶梦。
人生真的不能抱有太大期望。
目瞪口呆地看着阿修用脚踹开锈得斑驳的小铁门,而它很配合地轰然倒地时,我顿悟:
男人,实在是一种无法沟通的物种。
我的桔梗和三色堇呢?我的浪漫周末呢?
怎么也不应该是这么一个破败的体育场啊。
还令人几近虚脱地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招牌——青少年棒球基地。
“你觉得不好玩?”
“没有啦。”我耷拉着脸,脸上很明白地写着“很不好玩”四个字。
站在黄土飞扬的操场上,感觉自己的毛孔在被灰尘强暴。
我吃饱了撑,好好的懒觉不睡,跟来这种鬼地方。
斜着眼朝阿修发射诅咒电波,“我……”
他却缓缓开口说,“这里,是我17岁以前最喜欢来的地方。”
那个“恨”字硬生生梗在喉咙里。
“呃?”少年阿修,也是这里的一员?
“我从14岁开始就是少棒队的队员。”他的口气居然少有的得意。
“国家队?”
“当然。”他摘下棒球帽扣在我头上。
我胡乱地把遮住我眼睛的帽子扯下来,抓在手上。
凝望着棒球场的阿修居然有傲视群雄的霸气,让我几乎脱口而出,小的愿为大人效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总是入戏太深 ―___―~~~
原来,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这样深不可测。
瞬息之间,对这个大西北似的蛮荒之地涌起了熊熊的敬意。
往事如风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件小事。
某一次上选修课的时候,我听到前排的两个女生在讨论某一个问题。
“你觉得男生什么时候最吸引你?”
“不晓得也,那种感觉怎么可能会事先知道呢?”
因为课的内容实在很无聊,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她们的话题上。
“那照你这样说,只有意外发生的时候,才能吸引人的眼球?”
“嗯,好像的确是这样。”
“即是说,某个男生突然呈现出和平时不一样的状态,会令人很心动?”
“对对对,比如温柔的男生突然活泼,好动的男生突然安静,都很有魅力。”
我饶有兴趣地听完了整场对话。
心里却还是有怀疑。
真的是这样的么?
会动心?为这种一点都不持久的瞬间?还是发生在男生那种直肠动物身上?
假的吧。
我只觉得这种说法真的满好笑的。
那是我进读书会之前的小小插曲。
那个时候,我尚没有遇到阿奇和阿修。
直到他们出现在我的世界,或者说是我闯进他们的世界,我才发现。
原来,男人和女人一样,会有好多张脸。
让人觉得陌生,又不由自主想去深究。
好奇,以及带有某些感情的奇怪悸动。
那是一种连自己都会搞不清楚,是喜欢还是别的什么的复杂心情。
我在阿奇身上发现了这种东西在我内心存在的事实。
今天,阿修,再一次给了我这种感觉。
为什么,他们都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露出?
就如同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阿修,虽然一贯酷酷的神情仍在眉宇之间,却在微微的浅笑之下全部瓦解。
春风一样的英俊男孩。
居然可以用在此刻的阿修身上。
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阿修。
如果说阿奇带给我很多不确定感和游离感,那么阿修绝对是一个磐石一般踏实的人。
不论说什么,做什么,他就是那样,带着置身事外的表情,仿佛可以用旁观者的视线来解决一切问题。
令人放心的冷酷。
我没有想到,我们在来到这个破破的棒球基地后,他的整个人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凝望不远处的隔离式场地,或者黄土飞扬的操场,他一直带着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淡淡的喜悦和满足,又似乎是沉浸在无尽的缅怀之中,令人目不转睛的迷离神情。
看到我几乎忘了心跳和呼吸。
远处慢慢传来许多人跑步的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