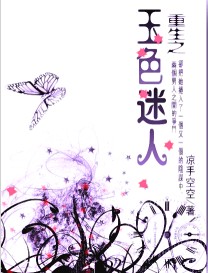沉沉玉色-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端午?你这内务总管,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吗?”
“太子莫要心急,老奴已将一切安顿妥当。进了四月,就为皇上发丧。”福英抬起头,浑浊的眼珠里生气全无,细密的皱纹布满了整张脸,声音不急不缓,又说:“殿下,清明本是皇后娘娘的忌日,为何殿下急于在三月底与兰夙公主完婚?”
“母后的事情我不会忘。”赵缎猛得站起身来,目光一闪一闪,像是正在吐信的两条毒蛇,俊美的近乎妖艳的五官开始扭曲。“他该死,我不仅要他的江山,更要权握整个天下。”
福英慢慢低下了头,说:“老奴劝戒殿下,凡事不可太过,更不可操之过急。武安王不谙权术,又与殿下为一母所出,一直以来感情甚笃,望殿下称帝后对其多加倚重。兄弟齐心,大事可成。”
“九弟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明白他不会有二心,这些话福总管不交代我也晓得。”赵缎渐渐平静下来,脸色苍白如初。“但萍妃的儿子不能留,这事我会交给九弟去办。”他淡淡一笑,挑了挑卷曲的烛芯。
“是。殿下这样说老奴就安心了。”福英面具一般僵硬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
赵缎摆一摆手说道:“退下吧。我等你消息。”
福英慢慢退出了奉极殿,风随着大门的敞开吹了进来,火烛跳跃,大殿深处传来阵阵玉石相撞的响声。
幽都的春,今岁来的迟了许多。三月底了,依然是蒹葭白露,凝水为霜,几日前的残雪尚未曾褪尽,深深浅浅点缀在青灰色的檐间,稀薄的月光下隐隐闪着光泽。风很大,从西北面刮来。
弦月如钩,渐上中天,华灯初上。
武安王府,六匹雪蹄宝马拖着一架朱漆大车。武安王赵信伸手扶下一身雪裘的纳雪,又手下吩咐道:“曹总管,王妃畏寒,暖炉多备些。”
“是。奴才马上去办。”年长的奴仆转身向府中急行。
款步踏上石阶,纳雪看见门柱后立着一名窈窕美丽的女子,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纳雪停下脚步,赵信也看到了面前的女子,一皱眉,随即说道:“毓黛,不是叫子英传话说不必来迎吗?你退下吧。”
水毓黛轻声称是,带着几个丫鬟向后院走去。
纳雪瞧她的衣饰不是下人打扮,心中大奇,对赵信问道:“她是府中的什么人?”
赵信的脸居然微有些红了,说话也踌躇起来,“她……她是太傅的女儿。是我以前的……侍妾。”
纳雪淡淡笑了,“王爷有些姬妾算得什么大事,又何必如此扭捏,以后她就是纳雪的姐姐。”心中暗道,这却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成婚之前,不是都不在乎了吗。
鄢澜圣京,三月二十九。
“父王是几时走的?”林楚轻摇折扇,漫不经心地问。
“王爷辰时出府,此时,应该出了北城门了。”纪宣答道,脸上淌着谄媚的笑容,目光在林楚脸上游走。
林楚合起扇面,敲了敲他的肩,笑道:“纪总管立的大功,本王是记得的。”
“奴才哪有什么功劳,只是识时务罢了。是小王爷恩德,奴才才能有口饭吃,奴才以后跟着小王爷,甘效犬马。”纪宣笑得更欢,腰也弓的更弯。
“好。纪总管忠心耿耿,到帐房去领二百两银子吧。是本王赏你的。”
“谢小王爷赏。”纪宣乐不可支地退出书房。
“慕晏。”林楚叫着一个人的名字,脸上的笑容早已不见。
“小人在。”慕晏的身影从门外闪进来。
“把纪宣除掉,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还有,申时陪我进宫一趟,托了她帮忙,总要有些谢礼的。”林楚将折扇扔到桌上,冷冷地说。
“是。”慕晏冷冰冰地回答,面上毫无表情。
从雍瑞宫走到内宫门,一路踏雨而来,身形摇曳,如风中冷叶一般了无生气。飞燕髻边插了支凤凰点翠步摇,琮琮泠泠的金片后,一张看不清表情的脸,绝美,却轻颦着双眉,眼波迷离,如云蔼笼罩。远远的回廊尽头,内侍邱尚思忧心忡忡地遥遥望着独自立于靡靡雨中的林冰瓷,心中顿升一阵焦躁,忍不住在原地踱来踱去。
内宫门外的小巷子,侍卫们早已经心照不宣地回避了,赤灰色的石板砖面,远远一辆四驾马车迎面驰来,华丽的朱红,浸透了雨水,显得分外奢靡。马车奔到近前,急急地停住了。车上勒马的侍从跳下来,半躬着身,恭敬地开了车门,锦冠华裘的俊美男子从车上走下来,啪的一声,车后的蓝衣侍从撑开一柄四十九骨的青竹绸伞,挡住了淅淅沥沥的雨。
林冰瓷的眼角滑过一丝水痕,淡淡的,几乎看不出。当林楚撑着绸伞走近她的面前,她微微翻卷的睫毛抖动了一下,抬起眼,眼中充溢了珠光斑驳的泪水。宫檐角坠下一颗硕大的水珠,重重打在伞上。
“你做的好。”林楚用近乎温柔的目光望着她。
雨稍大了些,落在石板上,发出砰砰的响声。
“你说的话,其实我不信。父王虽不是我生父,毕竟养我多年。我不能,如你那般无情。”林冰瓷幽幽地讲着,她垂下了眼,她不看他。
“他一日不死,你我便只能当得棋子。难道,你甘心?”林楚轻轻揽她的腰,双眸凝视,温情更甚。
林冰瓷依偎在他怀里,叹了口气,道:“罢了。做都已经做了,我也不想再听什么借口。我只要你知道,我这,都是为你。”
“嗯。”林楚将手揽得更紧,不再说话。
林冰瓷伏在他的胸口,又说道:“陈妃是极懦弱的人,我托她父亲兵部尚书陈醇将南北军交接地定在北城外,出了这样的事,他也脱不得干系,定然不会出卖你我,你不必担心有后顾之忧。”
一抹笑容绽在林楚嘴角,黯淡的雨色中,竟透着说不出的冷意,他的脸也映的更加清逸俊美。
釉青色的天幕下,凄凄离离,笼成一卷尘梦,四月将近,帝都圣京,满城萧索。雨一连几日沉沉的下,仿佛永远都不会停了。
三月二十九日,相持数年的南北军属地之争,在兵部尚书陈醇的调停下达成一致,在圣京北城门外北军大营举行交接。不料北军大营外,镇南将军林郇突然遇刺,伤重而亡。行刺者当即被南军副将沈宗钺绞杀,后经查行刺者皆为北军俘获的归陌降军。昭胤帝震怒,斥镇北将军萧天术治军不力,降一等,罚俸一年。林楚袭其父爵,由郡王晋升为亲王,食邑万户,正一品,接掌南军。
敬伽庆延帝二十九年三月三十,太子赵缎大婚,迎娶西蓥公主兰夙,西蓥千人使团来贺。庆延帝病重未出席,武安王妃亦告病未出。四月初三,庆延帝崩,举国大丧。市井皆传庆延帝为鬼魅所魇,惊风而亡。四月初十,太子赵缎即位,是为永嘉帝。四月底,武安王赵信率兵剿灭意图谋逆的金州王、诸堂王,斩其朝中党羽三百余人。锦绣公主府驸马曹烨牵扯其中,亦未能幸免。自此,永嘉元年,天下太平。
第十章
中宫太极殿,云中青鸟衔起翡翠芙蓉灯,珠玉屏帐在灯火辉照下极尽华丽,碧绿色的石阶上散落着千万条水晶珠帘,翻飞的蟠龙昂首吞云,绕柱而上三丈多高。宫鬟美姬捧着云母纨扇侍立榻畔,朱衣内侍垂眉敛目肃立于殿前。皇家气派,寂然无声。
突然,“皇上驾到。”宦官拖长了尖尖细细的嗓子,远远地从宫门外传来。
殿外是一方墨色的天,朦朦细雨乘着夜色正不紧不慢的下。
一行宫人执灯而来,黄伞盖下,尊贵的天子慢慢地走到近前,眉目冷峻,严厉的目光看着石阶上跪着的女子,他便是敬伽刚刚即位的永嘉帝赵缎。
“皇妹进宫见朕,是有什么要事吗?”冷漠的声音遥遥而至,像一缕轻烟在殿中萦绕,捉摸不定。
锦绣公主在石阶上跪得久了,手脚麻痹,她抬着头,微微颤抖着向天子脚下爬去。“皇兄……皇兄放过合缨的公婆吧,六哥、七哥谋逆之事与曹家决不相干,如今我夫君也已经死了,求皇兄恩典,给我夫家的余人留下一条活路……”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
赵缎踏上石阶,不凉不淡地又说:“朕纵然有心怜惜皇妹,此时怕也是无能为力。”
“不,不,如果皇兄都没有办法,又叫合缨去求谁?恳请皇兄即刻下旨释放合缨的夫家之人。”锦绣公主激动的一脸红晕,两眼水光忽闪。
赵缎瞧了她一眼,发出几声冷笑。“皇妹在这里等了多久?”
“合缨午时进的宫,到此时,怕有四、五个时辰了。”锦绣公主看着向来就十分畏惧的皇兄,不明白他此问何意。
赵缎紧紧盯了她一阵,长长叹口气。“朕给皇妹再许个好人家。”说罢,便丢下她往外城门行去。
雨落千行,宫城内外混沌一片,和着夜色模模糊糊地望过去,全是一片深黑。
锦绣公主望着他在雨中的背影,哑然无措。
福总管慢慢走到她面前,沉声说道:“公主是千金之体,地上寒气太重,快请起身。哎。曹氏一门今日申时已问了斩,求,也是无用了。”
话音未落,只听太极殿里传出一声凄厉的悲鸣,锦绣公主已然昏厥过去。
远处,黄伞盖的影子慢慢浅淡,宫娥长长的裙裾在雨地里拖过一道苍白痕迹,转眼就被雨珠吞噬。
鄢澜,玉剑关大营。一个白衫少年掀起帐帘,叫了一声“二哥”。
“三弟怎么来了,身子全好了吗?”军帐上首端坐的将军站起身,春风满面,几步跨过来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此人正是鄢澜大将军萧天放。
走进帐来的白衫少年文文弱弱,十七、八岁年纪,盈盈含笑,一副书生打扮,清秀斯文,与萧天放沉稳刚毅的气质迥然不同,但细看两人眉宇,竟仍有几分相似。
“月前就已无碍了。我又不像大哥二哥整日军务繁重,上次我病了二哥都能抽出时间来看我,我这闲人一个就不能看看二哥?”这白衫少年正是萧氏最小的公子,萧天湛。
“舅父和大哥都好吗?大哥看了我前些日寄去的信,心中可有计较?”萧天放略一沉吟,缓缓问道。
“都好。大哥说北军暂时还算是军心稳定,不过小林王掌印南军后,与诸多留守圣京的将军来往甚密,近日恐有大动作,大哥嘱我带话叫二哥你小心提防,及早准备,一旦京中有乱,请二哥调兵相助。”萧天湛脸上全无忧色,将这番话徐徐道来,如同背书一般。
略一沉吟,萧天放说道:“我不担心林氏此时能掀起多大波澜,毕竟皇上英明,朝中还有舅父。我最担心的是太子殿下安危,我听说近日来皇上对太子愈加不满,似有废储之意。”说罢,他拉了弟弟的手,相携入座。
“废储?皇上废了太子又能立谁?其余几位皇子的母妃大多身份卑贱,并不具备储君的资格。”萧天湛一脸懵懂,不明所理地看着哥哥。
“你忘了皇贵妃怀有身孕吗,如果是个龙子,就难说了。只盼望大哥和舅父在京中能对太子殿下多加维护。”
“二哥,我在帐外听左骑都尉淳于将军说,半月前你带轻骑在平雁山以西剿灭了一支西蓥精锐,怎么,西蓥胆敢来犯吗?”看到二哥紧皱着眉,萧天湛忙岔开了话题。
“那倒不是。只是有些私怨了结而已。”萧天放如此答道,眸中闪现一抹黯淡。
“二哥你会为私怨如此行事,我真不信呢,你……你当真是我那不乱法纪的二哥吗?”萧天湛一手指着萧天放,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萧天放也莞尔,淡淡说道:“怎么不会呢?”眉间落寞却已是难以掩饰。
萧天湛见他如此神情,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什么,几次张口想问,又忍了下来。
“天湛,我朝与敬伽订下兄弟之盟,已有多少年了?”一阵难耐的平静之后,萧天放突然开口问道。
“从延武帝六年至今,有四十年了吧。二哥怎么想起这个?”
萧天放却不答,又接着问道:“那你说,一旦与敬伽有战事,哪方的胜算大些?”
“二哥你是军中的大将军,一向是战必胜攻必克,我从没见你吃过败仗。不过我又听大哥说敬伽武安王,哦,就是跟我朝和亲的那个王爷,似乎也十分骁勇善战。兵法战略我虽然不懂,但既然未曾交锋,胜败之事又怎敢断言。”
萧天放点点头,站在帐边仿佛陷入沉思。萧天湛暗自揣度,二哥素来不跟自己提军中之事,今日这又是怎么了。
他正琢磨不透,忽又听得萧天放说话:“天湛,你回去告诉大哥,西蓥在西,敬伽居北,都正伺机蠢蠢欲动,玉剑关这五万守军一兵一卒都动不得。我日前已令虎翼将军雷翔密切关注京畿各驻军动向,只要太子那里不出乱子,其他无妨。”片刻沉思之后,他似乎下了极大决心,连望着萧天湛的目光都变得犀利坚冷。
萧天湛见他如此,心中一凛,道:“太子那里,二哥是得了什么消息吗?”
萧天放闻言一笑,站起身抖抖披风上的浮尘,“我刚才那话不过给大哥提个醒,也许只是杞人忧天而已,三弟莫往心里去。圣京距此数百里之遥,你来一趟不容易,二哥带你四处转转如何?”
“好啊,我正想看看二哥镇守的这天下第一关。”萧天湛大叫一声从椅上跳了起来,像个孩子一般欢呼雀跃。
萧天放素来对这个自小身体嬴弱的幼弟疼爱有加,见他如此,心中也不禁快慰许多。
敬伽幽都,残阳如血。一匹高大的玉花骢踏着昏黄暮色电弛而来,奔至行军队前缰绳一紧,忽然前蹄跃空,仰天嘶鸣。
“章禄,皇兄又有什么旨意了?”马上的少年顾盼之间眸飞冷霜,眉似利剑,跨马的容姿尊贵倨傲,张显出年少不羁的轻狂飞扬。
忠顺将军章禄几步迎上单膝跪倒,轻声道:“回禀殿下,陛下说今日天色已晚,此时殿下进京,城门必已关闭。连日来为了肃清叛党,城中宵禁,大军夜半进城多有不便。因此陛下请武安王在此处歇息,明日入城。”
赵信眼光一黯,挑了挑眉毛,转向章禄身后来迎的一队官员,略有些不满地道:“皇兄近来真是古怪,六哥、七哥的封地离京那么远,竟要我半月之内将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