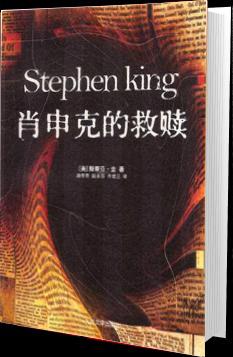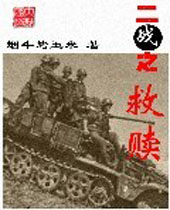赎-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赎第一部分
我叫阿难。在母亲二十三岁那年,树为了自己的成分问题和单位里的车间主任大打出手,头破血流,而那个主任最后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树因为误杀罪名成立,被判十年有期。树就这么离开了母亲,母亲在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只说了四个字:我会等你。
阿难(1)
我叫阿难。
〃难〃是个多音字,通常发音nan,阳平。外婆选这个字作我的名,取的正是阳平调,可更多的人喜欢用去声,因为去声的〃难〃比阳平调喊起来更加有力。他们叫〃阿难〃的时候通常是要来吵架告状的,显然这样的叫唤需要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我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她死于难产,直到死的那刻也没能产下不足六斤的我。医生只能开膛破肚地从尸体里取出湿淋淋的婴儿,她在子宫里的位置正常,姿势友好,谁都不明白为何这个孩子要死赖在羊水里两天两夜,直至母体精疲力竭。于是,我的出生成了一桩〃悬案〃,即使在二十多年后再次被提起,负责接产的医生依然记忆清晰。这场灾难使我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外婆几乎连踌躇都不曾有,便给了我单名〃难〃。这是一种小而细微的惩罚,我知道。她不能够恶狠狠地怪责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可她却能在这个孩子的姓名里留下灾难的痕迹,令她一生一世都必须记得〃难〃字的真正寓意。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姓翟。〃翟难〃是个显而易见的坏名字。
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为了〃翟难〃这两个笔画繁多的名字,我绞尽脑汁,一笔和另一笔之间毫无联系的逻辑关系却令我常常将整个字写得支离破碎。我不能把名字写得好看,这使得我在其他汉字的书写上沿袭了拆字的风格,我不喜欢带框的练字簿,我的汉字们常常拆卸了手脚东走西逛。或者按照外婆的理解,我是一个〃败家精〃,所有的一切只要到我的手里,就会四分五裂不得好果。像是汉字、自动笔、机械表,我一定要将它们拆得看不出原貌才甘心。一天,当我将外婆的绞肉机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卸下来的时候,她终于站在灶间的走廊上当众给了我一个巴掌。〃败家精〃!这是她忍无可忍的表示。
一直以来我都在揣测母亲的样貌,外婆的抽屉里有零星的母亲相片,它们被插在一本相册里,那种只在每页的底板上开几个小口用来插相片对角的相册。页和页之间是半透明的玻璃纸,翻起来〃哗哗〃很挺括地响。母亲的脸在黑白照片里看不出神韵,她只是冷淡淡地坐在公园的一角亭子里,或是斜靠着一把绿纱纸阳伞,微微地笑,像是含情脉脉地看着镜头那边的父亲。这样的神情,在母亲那个年代司空见惯。我也看不出母亲的肤色是否光润洁白,她只有一只深而娇媚的酒窝,微微地一笑就能显现出来。我还能从外婆的脸上揣测母亲的模样,她发起脾气来眼睛一定也像外婆这样熠光闪闪。不过,我还是希望她慈祥一些,温暖一点,靠在她的胸口可以安静入睡。
可我从来不愿在自己的脸上寻找她的影子,因为我的肤色黯淡,甚至在上海大爆发甲肝的那年,因为脸色蜡黄,屡次被邻居龃龉怀疑。而我也没有那只深而娇媚的酒窝,有的只是额头上那两个深浅不一的骨坑,一个按照外婆的话是命里带来的,另一个则是打架留下的。
外婆说,命里带来的骨坑,是个坎。有这样面相的人,命硬。
母亲死后,外婆将我带在身边,我们只有一张床,各睡一边。外婆的脚底心一直是滚烫的,腊冬里我就将手捂在她的脚踝上,汲取一点热量。我的父亲是个迷信的人,只是我想他不如外婆那样爱我的母亲,所以对于她用生命换回来的孩子,这两个同样信〃命〃的人有了不同的态度。我的奶奶更是个尖刻的小老太,她催促着父亲搬离同安里,我知道她将我视作包藏祸心的种子,同安里九号的人都知道。为此,我不喜欢母亲,因为她嫁给了这样的家庭。
从能认人起,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是个不苟言笑的高个子,他年里偶尔回来同安里几次,买一袋红润的苹果或是一件女童装。他从不与我亲热,就坐在四方桌的一角远远地看我几眼。每次来他必是要坐足两个小时的,先和外婆交待一下这一阵自己的工作情况,然后例行公事般地关心一下外婆和我的健康问题,最后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再看我几眼,或是拉开四方桌的小木头抽屉,塞一些整票进去。
外婆从来不向父亲伸手要钱,在父亲例行公事的〃关心〃后,她就走开去灶间择菜。十几年后当我回忆这段情节时,觉得外婆的走开,是有其他意思在里面的。她留下一点空隙,希望父亲能走到天井里,同那个正在拆卸东西的小姑娘说说话,亲亲抱抱一下。虽然她也不能保证,这个小姑娘会不会伸着肮脏的长爪子,一个巴掌呼过去。因为对于陌生人,她的态度一贯如此。可每次择菜回来,父亲起身打算离去的时候,外婆只能在四方桌的小木头抽屉里发现一些钞票,而在天井里拆卸东西的小姑娘,却依旧神情专注。于是她招呼一下,〃阿难!跟爸爸说再见!〃
对于这样的招呼,我从没回应过一次。
同安里的邻居们都认得父亲,因为他和母亲一样,从小生长在上海西南角的这条细细长长的弄堂里。和城市里无数条弄堂一样,同安里琐碎、嘈杂。弄堂口对着一排小杂货店,每天早晨里面做生意的外地小老板们就会蹲在马路边刷牙洗脸,他们吐出的白泡沫水沿着马路逶迤婉转。还有卖大饼油条的流动摊贩,推着裹了一层黑油的柏油桶,架着锅若无其事地走过。到了傍晚,杂货店小老板们的妻子将一盆盆洗衣水〃哗〃地倒在路边,白泡沫水拖着比早晨更长的尾巴一路向同安里奔来,却在马路中央被疾驶而过的车辆拦腰折断,遗恨万年。
阿难(2)
我始终不愿相信,这是滋养爱情的地方。哪怕我的父亲母亲在这条狭窄的弄堂里,从邻居变成了夫妻。
我和外婆住着的同安里九号原本是二房东用来出租的整套小洋房,解放后七七八八地分给几户人家。我们住在底楼南间,临着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的四围是雕镶图案的铁栅栏,每到秋天便爬满了忍冬,黄昏的时候太阳一点一点地铺上植物,然后懒散地变换着颜色渐渐褪去,那样的景色是同安里里唯一可以想见到曾经它还是老上海小洋房的凭据。所有的人都留恋着这样的景色,因此每到太阳要离开同安里的时候,他们便搬出一把凳子来,闲坐在院子前说闲话,各式各样的闲话。
在外婆发现我偷偷趴在栏杆边听那些闲话的第二天,她找来泥水工将铁栅栏砌填起变作四堵围墙,那些忍冬被恶狠狠地扯下丢在外墙,在外婆看来,那上面附着了太多的口水。她说,小孩子听闲话,是要烂耳朵的。果然,从那以后,每年冬天我的耳朵都会化脓腐烂,然后在开春的时候结疤愈合,老人们管这样的现象叫做〃冻作〃,可我却坚信是小时候偷听闲话的报应。
从砌墙的那天开始,外婆和邻居们的纠结就没停止过。开始,矛盾的焦灼点有很多,譬如院子的真正归属问题、底楼其他人家的采光问题、二楼的防盗安全问题等等。可到后来,矛盾开始渐渐统一,并且不知怎么地就变成了围墙内的环境问题,因为自从院子变作天井,二楼三楼的邻居们经常会将各种垃圾倾囊而下,那些塑料袋在黑夜铺临的时候,〃噗〃地闷声而下。那是一种报复,外婆很明白。她从不在夜里清扫天井,即使我们的屋子里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一声声〃噗〃,还有偶尔盆花被砸断的声响。她只会在每天早晨拖一把枯枝扫帚站在天井中央脸朝上,像一只井底的青蛙看很久,而后闷声不响地将压坏盆花的垃圾从花盆上仔细地刮下来,接着将天井清扫干净。她从来不数落楼上的人,也从来不和他们搭话。在公用灶间里的相遇是冷冰冰的,用两把锁将自家的煤气、水龙头锁起来,或是炒菜的时候不经意地往旁人的锅子里瞄一眼。邻居的婆娘们用上海话管我叫〃灾难〃,〃难〃用了去声,铿锵有力。
在同安里的童年,对我而言没有玩伴,只有敌人。
弄堂里长大的小孩喜欢成群结帮地窜来跳去嬉戏,用路边的红砖片在地上画格子造房子,五角钱买一叠香烟牌俯在地上把手拍得通红,女小孩还会偷一把家里的橡皮筋出来连成串,绑在腿脖子上分两组跳出各种花样。可她们从不招呼我,我也不搭理她们,只抱膝坐在同安里九号的门槛上,天是血色的,云变成血块凝结在半空。
这样的〃玩耍〃和〃观看〃原本相安无事,有的时候我会从家里带出一些小部件坐在门槛上拆卸着玩,那是有炫耀的意思在里头的。一直到那个夏天。
风从弄堂口削尖了脑袋闯进来,它贴着水门汀翻滚着身子,将那些花花绿绿的香烟牌吹得螺旋上升。女小孩的辫子在风里扬得很高,短发则被吹得露出头皮来,她们拼命尖叫着,嘲笑追着香烟牌奔跑的男孩子。可天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大怒了一场,除了前来挑衅的风之外,毫无征兆。夏天的暴雨像拳头一样有力,〃啪啪〃地打下来,弹在地上粉身碎骨,紧跟着的雨点依旧不死心,义无反顾地继续。接着是闪电,还有雷,像病入膏肓者的咳嗽声,撕声力竭。天变作乌青色,一滚云一滚云地翻腾着。所有的孩子像是被从天而降的拳头暴打得四处乱窜,橡皮筋还箍在腿上就被扯断得四分五裂。她们向我涌来,蛮横地用脚踢开我拆卸完毕的细小部件,往屋子里躲,钢笔里细小的部件瞬间被踩踏得面目全非。
我忘了自己是如何站起身子挥过拳头的,那样的袭击毫无目的性,我面对的是三个小女孩,她们最后将我团团围住。这场夏天里的殴打成为那个夏天的唯一记忆,从此,我在邻居们的流言里成为同安里最凶残的孩子,她们窃窃私语,那无疑是一种遗传。
我们在暴雨里扭打了很久,我分辨不出每一次落在身体上的拳头是谁的,或者根本是天上那位病入膏肓者痛击下来的。我看到那些撅着屁股在水塘里捡香烟牌的男孩子,显然,他们对于女小孩的战争不以为然。我反复地和不同的女小孩在水塘里打滚,用尖利的指甲划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我讨厌她们的尖叫。终于,我的额头被地上的红砖块划破,雨水流进来的时候很疼,我觉得脸上有热乎乎的液体在蜿蜒,她们停下手来,继续尖叫。
战争往往要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而我觉得我是输了。
外婆从灶间里探出脑袋箭步冲过来,恶狠狠地推开她们,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仇恨。一屁股坐到水塘里的女孩开始号啕大哭,边上捡香烟牌的男孩子牢牢握住手里湿淋淋的纸牌,惊慌失措地跑开,他们边跑边叫:〃打人啦!流血啦!〃同安里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我看到被我拆卸下来的钢笔管渗出蓝黑色的墨水,它们顺着雨水一路蜿蜒出去。外婆抱着我一路小跑出弄堂的时候,它们在马路中央被疾驶而过的车辆辗过,变作一朵朵蓝黑色的花。我在自己的脸上闻到一股苦涩的芹菜味,它们从外婆的指缝里流淌出来,埋润在那条蜿蜒的红色小溪里。
医生像外婆缝被子那样在我的额头上穿针引线,一共四针。战争不仅在我天生的骨坑边多留了一道凹陷的骨坑,更在同安里留下了我和外婆的恶名。邻居们愈发地在我面前表现出对于父亲一家的同情,促使他们搬走的,就是我这个祸害。外婆开始将我锁牢在屋子里,不再让我坐在门槛上看别人嬉戏。每天清晨,她依旧默默地拖着枯枝扫帚来到天井,一点一点地清理垃圾。我站在割栏的玻璃窗后看着她,还有地上那几盆被砸坏了的波斯菊,它们的破身子被旧电线缠绕好,唯唯诺诺地缩在墙角里。那样的场景安静得像一幅画,伸出手去又是如何都摸不到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许真是个祸害。
阿难(3)
遇到树的那年,正是我脸色发黄得最严重的日子,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脸色蜡黄是因为没有营养。
那一年上海人因为贪恋一种贝壳类水产而大规模爆发甲型肝炎,父亲有大半年没来看我们,我和外婆天天吃的就是弯过弄堂口那条马路边菜市场里的土芹菜。外婆也从来没有主动找过父亲,仿佛他是个可来可不来的次要人物,她把政府发下来的救济金分成很多份:我的学费,午餐费,伙食费,日常生活开销。。。。。。她算钱的时候总是盘腿坐在凳子上,架着一副褐色塑料框的老花眼镜,算盘珠子被打得活络作响,丝毫看不出来窘迫的模样。最后她决定让我每天回来吃午饭,而为了要赶时间做饭,她还准许我自己穿过两条马路回家。于是,中午便成了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时段,哪怕那条路短促而又孤独。
依旧是个夏天,快要进秋。在学校里,我依旧没有朋友,有的只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和额头上劣迹斑斑的伤疤。可就在那一天,我抱起〃脏东西〃的同时,遇到了树。
〃脏东西〃是一只猫的名字,它与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流浪猫毫无异处,它本来应该是只白色软绵绵的东西,可我遇见它的时候,它正躲在同安里的拐角上〃呜呜〃叫唤,身体蒙了一层脏灰,右前腿折断了,弯曲得很痛苦。我几乎是贴着墙壁走过去的,因为揣测它可能会溜走,可能会张大了眼睛愤怒地瞪我一眼,然后一拐一拐地四处逃窜。可都没有,它像是安心地在等待着谁过来看自己一眼,疑惑地观赏着我的蹑手蹑脚。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它,想看一看血液蜿蜒的图案。
小心点,它受伤了。
树的声音很低沉,我几乎就要放手丢下这只脏东西起身跑开的时候,他蹲下身子按住我的手,小心翼翼地把〃脏东西〃放到地上,绑上纱布。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刀,劈开一根小竹条,一半对一半地架在它折断了的右前腿上,再用一长条麻布扎好。
好了!他拍拍〃脏东西〃的脑袋,非常满意地看着自己包扎后的右前腿。
这是你的猫吗?我肃着脸问道,眼前的男人是个陌生人。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