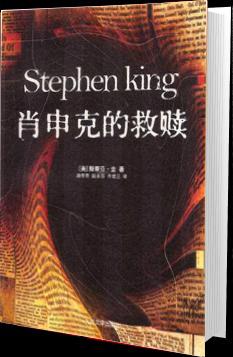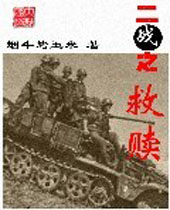赎-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你的猫吗?我肃着脸问道,眼前的男人是个陌生人。
不是,它应该是被人抛弃了的。他扶起〃脏东西〃让它站稳了,看看竹片固定得是否牢靠。〃脏东西〃〃嗷〃地叫了一声,在他的手背上划下一道血印。
畜牲!我伸手拍向它的脸,恩将仇报的畜生。
没事,是我弄痛了它。树吹了吹自己的手背,用手按了按我的脑袋,你可以把它带回去养伤吗?那儿是你的家?他指了指同安里九号的大门,我点点头。
等它病好了,我会来看它。树勾起食指轻轻地捏了一下我的脸,然后拉了拉我的耳垂,动作轻缓并且温柔。我在他的目光里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庞,她微微地笑着。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温柔,它来自一个男人。树看上去很年轻,二十六七岁的模样,头发短得很精神,眉心有一道异常明显的疤。这一年,虚岁算来,我刚好十岁。我点点头,一把抓起〃脏东西〃,按在怀里。
就这样,在同安里的巷子口,我第一次见到了树。
把〃脏东西〃抱回来的时候外婆显得很不高兴,她气鼓鼓地站在灶间里剁菜,邻居们不怀好意地一旁窃窃私语着。看到我抱了这么只肮脏又血迹斑斑的猫回来,她几乎就要挥刀砸过来泄愤。可看到它右腿上的伤,还有唯唯诺诺的神情,外婆还是从早晨清理完毕的垃圾里找出一些骨头残渣来,丢在它面前。尔后转身对我说:以后就跟它玩,放学后哪都不准去!
就这样,〃脏东西〃在天井的一个角落里有了一只算不上很温暖的稻草心篮子,它的开始安心地等待腿上慢慢好起来。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秋天没有盘固逗留,北边的风就一路侵袭而下。〃脏东西〃的伤好得很缓慢,似乎它心里怀疑怯懦着一旦好起来,恐怕又要成为一只灰不溜秋的流浪猫。外婆的脸色开始一点一点变黄,我们和〃脏东西〃相处得很惬意,一直到年末它奄奄一息地躺在同安里九号的大门口。
外婆开始显露出病态,她吃不下饭,也烧不动菜,我和〃脏东西〃便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她开始主动打电话给父亲,那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在外婆打电话给父亲的那天,〃脏东西〃因为不知偷吃了谁家的菜,而在灶间里被活生生地逮住,有人打落了它的牙齿,他们还用扫帚棒打得它的嘴唇凸肿开裂,她们扯起它的耳朵将它抛出灶间。外婆回来看到〃脏东西〃的时候,它已经面如死灰,抽搐着躺在大门口,裂了缝的嘴里不停地吐出最后一点热腾腾的血腥气。她什么都没有过问,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抱回来,邻居们还围在灶间里心痛着自家的饭菜被这畜牲糟蹋了。
外婆将〃脏东西〃放在稻草心篮子里,对着被血浆冲得睁不开眼睛的〃脏东西〃说:这是命。我知道,从那天开始,外婆开始等待死亡降临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夜里,惊醒的时候,我感觉到外婆冰冷的双脚,它们应该是在我怀里一点一点冷下来的,我爬下床,拉开灯,〃脏东西〃已经僵硬地缩在稻草里一动不动。我飞奔到灶间烧开水,满满一壶,憋足了劲提上煤气灶,然后守在一边,心里不断地催促着火苗赶紧将冰冷的液体烧得沸腾,求求你,求求你,一步不愿意离开。
阿难(4)
我为外婆暖脚,它们实在冰冷得可怕,沸水将冻僵的毛巾融化,我的手指也开始化脓腐烂,它们毫无知觉,我将毛巾绞干,敷在外婆的脚上,她的脸色蜡黄,眼睛紧紧闭住,我小声地告诉自己,外婆睡得太熟了。我凑过脸去,感觉外婆身体的温度,可哪里都是冰冷的,寒冷像是一股潮水从她的头部开始,慢慢侵吞,一直到脚底心,最后传给睡熟了的我。那时候的我,只将冰冷作为一种警告,死亡的警告,我坚信冰冷和死亡有本质的区别。我寻来家里所有的毛巾,将它们融化,变得暖烫,小心翼翼地敷在外婆身体的各个部分,我坚信只要温暖起来,外婆那个长久的梦会在天亮的时候结束。我就这样一壶一壶地烧开水,感觉着毛巾在冰冷的空气里一点一点失去温度,而后继续一块一块地将它们变热,希冀着它们能够最终让外婆在冰冷里温暖起来。
可是没有。
父亲将我带离同安里的时候,我只带走了一盆波斯菊。
班主任在发现我接连旷课两天后,上报学校,全班被隔离,卫生科的老师小心翼翼地家访,却在同安里九号底楼朝南的屋子里发现了两具尸体,还有依旧努力不懈地烧着开水绞热毛巾的女孩。我们的天井里肮脏无比,各式各样的垃圾袋横尸遍布,如果是夏天,那一定是苍蝇最乐意的嬉戏场所。我尖叫着拒绝任何人搬动外婆或是〃脏东西〃,用指甲划破每一只擒住我的手,抓花每一个凑过来同我讲道理的脸,我恨面前所有的人,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能从心底的某处抽离出这种仇恨,在最短的时间将它膨胀,直至抓狂。
可外婆和〃脏东西〃被抬走后的第二天,我却顺从地跟着父亲去了医院。离开同安里的那条路显得漫长,我抱着用电线捆扎残破瓦片的花盆,那上面还有垃圾袋里流出的鱼腥气,要是从前,〃脏东西〃一定会皱着眉头一路小跑过去,将它们舔干净,然后惬意地伸开四肢躺在天井里晒太阳。想到那些,我开始看不清东西,一些滚烫的液体从眼睛流出来,落在化脓的手上,却渐渐地感受到它们从滚烫变作栗冷。
几天的检查、观察后,医生确定我只是营养不良,并没有被传染上肝炎。父亲来接我出院的那天,身边跟着个小女孩,她长得很好看,父亲说,她叫翟佳。她怯诺地丫在父亲身后,小声地说,我就要读书了。我知道她是我的妹妹。
我从来没有看过灰姑娘的童话,从来没有。对于爻阿姨的敌意,完全是因为母亲。
佳的妈妈是父亲在搬离同安里后的第二年认识的,她是父亲工厂里的车间会计,父亲毅然离开工厂的那天,爻也辞了职,开始陪父亲一起在东安路的小杂货街上摆摊头。过去父亲从没有在意过身边的女子,可在一个雨天,父亲忙不迭地收拾五金小货时,爻打了一把黑油伞默默地走了过去。
关于父亲和爻的故事,大都是佳告诉我的,她坐在我们屋子的海绵地板上说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里充满甜蜜,我厌恶那样的甜蜜,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保持沉默,还在心里偷偷地将〃瑶〃变作了〃爻〃。爻是《周易》里解释卦象的单字,六十四卦,八百六十八爻,变幻无穷。爻待我很好,可我坚信她内心是憎恨我的,这和表面无关。哪怕现在我已经不叫翟难,而叫翟羽,可我依旧是阿难。奶奶每次叫起〃阿难〃的时候,都是厉声竭气的,她不像别的奶奶那样疼爱自己的孙女,或者换句话说,她从不像疼爱佳那样疼爱我。我告诉自己,其实我也不需要那样的疼爱。
佳比我小三岁,当她长到了十九岁的时候,捧着一大摞站在太阳底下,一路向我小跑过来,额头上的汗珠子在阳光下熠熠闪亮。
姐,你也去图书馆?
我常常都告诉自己,佳是我的妹妹,我是疼爱她的。因此从小,只要有人欺负佳,我都会像个泼妇般为她大打出手,这使我在后来转去的那所学校里恶名昭著。可是背地里,我又嫉恨着佳,因为她是父亲背叛母亲的标志。他开始了另一段爱情,在抛弃我以后,在搬离他与母亲相恋相爱的同安里之后。我经常偷走佳的新玩具,新衣服,那通常是奶奶单独买给她的。我把它们丢到后巷子的垃圾车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刚开始的时候,佳会哭着到处找那些玩具、衣服,而我却安静地坐在一旁,从不帮手。奶奶从后巷子的垃圾车里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砸在我的身体上,她一口断定这是我干的。我不作响,蜷着膝坐在地板上,这个时候佳会突然停止哭泣,一脸自责地表示那好像是她自己忘记丢掉的。这样的戏上演了几次后,佳会自己去后巷子的垃圾车里寻回自己的衣服玩具而不惊动奶奶,我也每次保证将那些东西丢在固定的地方,只是我藏着一把剪刀,将它们通通剪破。佳将那些衣服玩具捡回来后,会抱在怀里黯然神伤一段日子,我窃喜着她的伤心,可我又惧怕看到她难过却沉默的神情。我的心里有一种仇恨,它只消一丁点的释放,就会上升到不可抑制的地步。
因此,在我第一次看到树的时候,手指朝掌心,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疼痛是身体内自己对自己的预警,可当时我却忽略不计。
树不是十岁遇见的那个树。〃树〃只是一个代号,它和〃脏东西〃一样,用来指代一种族群,就像后来我所拥有过任何动物,一律都叫做〃脏东西〃。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的〃脏东西〃是一只白化的凤娇鸟,喂养它的人是佳。
阿难(5)
树是佳的男朋友,在她二十岁那年。
交通工具往往是偶遇爱情的最好地方,尤其是抛了锚的交通工具,上不得,下不了。这时候,乘客的世界是同外界割裂开来的,恐惧,焦躁,依赖,需要,因此而生。半个世纪以前,有个传奇女子写下《封锁》,虽然爱情在电车止步不前的那刻变得混沌,却直到如今还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佳告诉我她和树的相遇时,我转身从书柜里取出收有《封锁》的那本小书,递给她。只是佳和树的相遇相识,要远比《封锁》里的人物来的危险,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几万英尺的高空,颠簸不停的机舱将两个人裹在一起,裹到一起。
那年,我将佳一个人留在香港,自己改签了前一天的机票回来。走的时候,佳还在熟睡。半夜里,突然我就有了这样的念头,将还没完全懂事的佳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所措。那是我十岁就经历过的恐惧,醒来的时候,一片漆黑。我将手机关掉,一个人坐在新机场里等佳慌张地跑来寻我,可是没有。我想她一定是打回上海求救了,奶奶一定在电话那头恶狠狠地诅咒我,她会用一种在我看来谄媚的心疼语气对佳说:乖囡。。。。。。
通知到第三遍〃开始登机〃的时候,我将手机打开,心里和自己打赌,如果她打电话来,我就回去。可是没有。那天傍晚,佳改签了一班夜机回上海,闵浙风雨交加的一晚。
我是三天后才从同安里回家的,搬出同安里后,每次在奶奶那里得到一顿毒骂感到委屈时,我总还是会偷偷跑回来,我和外婆的家一切如旧。我喜欢站在隔栏的玻璃门后看天井,邻居们不再丢垃圾下来,院子里只有一些枯掉的叶子粉末,风轻轻一吹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一次重新跑回同安里的时候,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哭过了,我总觉得身体里有一种强悍的力量在支撑着自己若无其事,可这种力量一到同安里,一到我和外婆的家,一站在那隔栏玻璃门后,便彻底瓦解。之后,每次当我觉得自己应该哭一场的时候,都会偷偷跑回同安里。可回同安里的原因不止如此。
十岁后的每年生日前后,我都会在同安里的信箱里收到一张留言诡异的包裹单,寄件人地址永远是忽东忽西的:浙江、江西、湖北、河南。。。。。。他的留言永远都是:那只小猫还好吗?我知道那是同安里弄堂口遇见的树。所以我回来,守在同安里九号,等树来敲我家的门,即使他也许不过是挂念〃脏东西〃。二十四岁的时候,一年中总有几个月是在同安里度过的,父亲不再像十八岁之前那样按时来同安里接我回家,我知道总有一天,我是应该离开那个家的,那个完整属于佳的家,那不过是我成人前寄居的场所。
回到家,爻正在厨房做饭,佳不在。奶奶和三个邻居在搓麻将,她斜着眼瞟了我一下,碍着外人在场,默不作声。父亲从书房走出来,招呼我进去。他取出一张报纸,摊在桌子上,页脚不怎么起眼的地方有一条新闻:x航一客机7000米高空遭遇强气流机上五人受伤。
我有些急事,所以来不及告诉佳,便先回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解释道。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翟羽,你。。。。。。
爸爸,你又忘了,我叫翟难!我生硬地将父亲要说的话抵回去,这些年来,都是如此。他不作响,呼吸均匀,可也不看我。
外婆家原先有一些妈妈照片的,爸爸,你看到过吗?走出书房前,我又一次试探地问道,可他依旧不做回应。
母亲的那些照片,在外婆去世后,不翼而飞,每次回去翻箱倒柜地寻找,却一无所获。我坚信那些照片是父亲取了来,我用取回照片的理由让自己再留在这个家一段日子,这是生硬的理由,我用来勉强地说服自己。同安里和这个家像两头牵扯着我身体的野兽,两边都冰冷,两边都温暖,同安里的冷在于空无一人,可它装满了曾经有过的温暖记忆还有等待那个年轻的、善良的树回来看望〃脏东西〃;这个家的冷在于所有人的若无其事还有奶奶经常的冷嘲热讽,可它装满了佳和我的青春岁月,我们曾经窝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还有我在世上唯一至亲的父亲,即使他看起来并不怎么在乎我的存在。小的时候,我和佳一样常常会悄悄躲在客厅里等父亲回来,他开门进来,佳便从桌子或者沙发背后窜出来,索要一个拥抱。可我还是躲着,远远地看父亲抱佳一下,亲她一下,偷偷地看着。他们走后,我才会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黯然地走回房间,随手拿一件佳最喜欢的物什丢到后巷的垃圾车里,然后跑回同安里哭一场。这样的画面还很清晰,在我最善于嫉妒的年龄,曾经有一个星期拒绝同佳说一句话,看着她把脸逼得通红,带着哭腔问道: 姐,你在生我的气吗?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我最爱的,不止父亲,可我最恨的,是佳么?我无法回答自己。
当早晨清涩的阳光将身边的树照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悲哀。我将冰冷的手放在树的胸膛上,可却怎么都温暖不起来。我说我手上的血管一定阻塞住了,它们在冬天的时候常常拒绝血液的流动。树翻转身子面向我,不回答,看着。我又说,我的手在冬天时会腐烂,你会害怕吗?他摇摇头,握着我的手坐起身子,侧过脸:
我们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