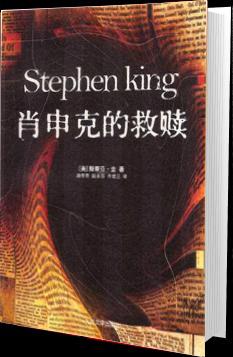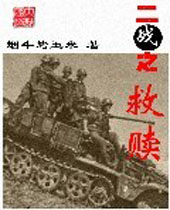赎-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至于他南下的目的,仅仅只想自己掏钱灌一张专集,他说广州是终点,可我在中途鬼魅无比地出现。
恺用与上次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语调说:menu。侍应生端着托盘过来,操着流利得可怕的英语说:WhatcanIdoforyou;Mr。Ken?
那样的口语让我在一旁不知所措,我的英语糟糕得差点没有过BAND…6,我憎恨英语,憎恨所有没有骨架的英文字母。我们现在吃饭的地方门口只有几个英文单词:CaliforniaPlaza。我不知道在上海这个中国人口密度庞大的地方怎么会允许让这样一个只有英文单词而没有中文释义的标示存在,这算什么,加利福尼亚大厦?加利福尼亚帕拉扎?荒唐。
背景音乐放的居然是Eagles的”HotelCalifornia”,轻慢的音乐带着种种遐想,每次听这首歌,不知怎么地总是让我想到纳博科夫《Lolita》里那段对于高速公路的描写:
我们的车子一口一口地吞掉前方无边际的高速公路,就像洛吞巧克力那样。
我喜欢各种各样小说里对于高速公路的描写,比如这个,还有《廊桥遗梦》里罗布斯第一次出现在弗朗西斯卡面前时经过的那条高速公路,充满着神奇的力量。
恺自作主张地替我点了菜,事实上如果把所谓的menu交给我,同样我也毫无头绪。因为可怕的纯英文餐名,我看着这些只会觉得糟糕透顶。
我没有迟到,刚才坐在那边看了你一会儿。你早到了5分钟,这是个好习惯。
他斜着嘴冲我笑笑,居然就像我们已经是熟识的朋友、恋人抑或是情人那般。Eagles那首歌的过门是好听的吉他,回旋着,似乎没有尽头。我看着他,默不作声。
我们就这样奇怪地在沉默中吃完那顿饭。末了的时候,他终于抬起头来,用乳白色的餐布拭去嘴角的些许油渍,说:我还会找你的。
我在”CaliforniaPlaza”的门口看到了Wendy,她友好地冲我笑笑,恺站在我的身边,等待boy把他的车开来。我力图让自己看上去坦然一些,
Wendy!
黛!她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鼓鼓囊囊的。平日里,我只见她有一个黑色的皮袋子,里面装着她的理发工具,十几样,不同的用途,银制的,亮闪闪的。
宽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老家那个初恋情人和Wendy很相像,那个女人是他们镇上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宽15岁的时候,那个女人勾引了他,在他发育并不完全的情况下。后来她大着肚子告诉他宽,他的寄父很早就诱奸了她,她趴在宽的肩膀上抽泣的时候,宽突然想过要去杀人,也就是说她先是寄父的情人随后又用同样的方法诱奸了他。宽总是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随让双方都是情愿的,但年长的人总是具有诱奸或是强奸的嫌疑,就像他的寄父,就像那个女人。
悲哀的是,诱奸和强奸不同,因为常常遭受诱奸的人事后会轻易地爱上对方,这里面的关系原本就是半推半就的,而不明事理的爱情随着情欲轻易地种植在忐忑不安中。就像那个女人,就像宽。
宽说,直到那个女人小产死的时候嘴里还拼命地喊着他寄父的名字,镇上的人以为她是想让寄父把逃匿在外的宽找回去,可笑的人们。寄父则假惺惺地抓住那女人的手,一个劲地说,不要说话,伤身体。
女人就这么走了,带着没有流干净的孩子盘踞在子宫里肮脏地走了。大户人家当然不会放过他们认为元凶的宽,寄母把宽的破贝斯和一些钱塞给他,痛苦地摇摇头,镇里的纷乱情况在她的口中似乎都是宽造成的。宽说他当时张开双臂抱了寄母,感觉到她苍老的身体,他说谢谢,对不起。
宽并不是很愿意提起那些事情的,有的时候我会轻易地在他的叙述中发现漏洞。后来,兴许他觉得和我这个习惯了与文字小说打交道的人撒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他就不再提起。半夜的时候,宽放在我颈下的手臂会突然地颤动,我惊醒的时候抬头看到的只是他布满汗珠的额头闪闪发光,我推醒他后,他只是默不作声地把我的身体搂得紧些。
烟逝(5)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座城市开始迷恋流星雨。
33年一次的狮子座流星雨。
在宽的逼迫下我开始翻不同的报纸寻求招聘广告,他对于失业的我恍恍惚惚惴惴不安,在我把他的肩膀咬得红红绿绿后,终于还是乖乖地坐在地板上开始翻看形形色色的报纸的形形色色招聘广告。可我轻易地走神看到了通篇的关于流星雨的介绍,
……今年11月18日凌晨2时前后(北京时间),地球将穿越狮子座流星群的中心地带。在这前后30个小时内,流星雨将出现多个峰值。其中11月19日凌晨1时31分前后,地球与狮子座流星群母体彗星(坦普尔…塔特尔彗星)在1699年回归时喷发的微粒团相遇,每小时将出现9000颗左右的流星暴雨。19日凌晨2时19分前后,地球又与狮子座流星雨母体彗星在1866年回归时喷发的微粒团相遇,每小时将出现15000颗左右的流星暴雨。
据分析,11月19日凌晨的流星暴雨,日本、朝鲜和中国处于最佳观测位置,加上正处于新月期间,凌晨观测没有月光影响,其机遇是千载难逢。……
我把报纸摊在宽的面前,我要你陪我去看。
他摇摇头,那天我要在Y2K还有几个零星的酒吧走场。
清脆的一声,我把报纸撕成两半。
后来,恺就似乎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在我寂寞难耐的时刻出现,我猥琐地答应了他的邀请。在宽出去赶场前兴奋异常地打扮漂亮,坐在他的面前,不出声响。他整理着贝斯,在矿泉水瓶子里灌满乌梅汁。冲我爱理不理的样子,他是知道我要出去看流星雨的,虽然他万分恶毒地说如果流星雨冲着飞过来的话我会被烧死的,我依然把眉毛画得轻佻无比,嘲笑他对于天文常识的缺乏。他就怒气冲冲地背上贝斯,关门前说了一句:
看的时候自己注意点,别真被扫帚星烫到。
然后留下一声温火的关门声还有无止境的寂静走了。
我站起来,裹上羽绒外套,戴上帽子、手套、围巾,留下一屋子的寂寞关掉大门。
滨江大道上立满了人,我用手机找到了恺。
他穿着VERSACE的大衣,烟灰色。头发一丝不苟地长在脑袋上,神情不可思议地一如前几次时那样,包括嘴角的弧度,眉眼的姿势。
我们站在江堤边,等待着有东西划破天空。所有的人都保持一个姿势,仰着头,仿佛古老部落人群祈福的神情。恋人们靠在一起,充满希冀耐心而又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
恺牵着我的手,隔着手套,我能感到他手心的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就好像通过这只手掌汲取我的热量,慢慢地抽干,我越来越冷,我们靠得越来越近。
就在我们肉眼看到的第一颗流星坠落下来的时候,人群开始沸腾,随后越来越多的流星似乎从四面八方落下来,黑幕色的天空变得亮堂起来。身边越来越多的恋人开始接吻,我靠着恺,双手插在他大衣的口袋里。
它们集体自杀了。我抬头看着恺,心里面空荡得不知道应该拿什么去塞满,那一刻我没有思想了,迟钝。
恺把脸低下来,我觉得四周越来越亮,不停地有银光闪烁,一颗接一颗的流星毫无规则地滑落下来。我感到他舌头的温度,依然是冰凉的,汲取我所有的热量。我更加的寒冷,我想起宽,想起他此刻应该在某个酒吧,Y2K或是别的里不停地弹着唱着,我愚昧地突然希望真的如他所说那样有流星冲着我飞来给我烧死。
可是醒来的时候,我身边睡着的已经是恺。
回到家后,我发现宽安静地睡在床上。
贝斯在皮套子里倚着沙发,装着乌梅汁的矿泉水瓶子顶着盖子躺在地板上。我洗澡后,光着身体躺在宽的边上,我伸手碰到了他的皮肤,褐色的,他的身体依然散发着檀香皂的气味。我开始亲吻他的脖子,突然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姿势睡进他怀里。宽醒了过来,开始回应我的亲吻,他的舌头是温热的,我们开始做爱,他的身体滚烫的,我发梢上的水珠散发着CLAIROL的香气。
他对一切一无所知。
我和恺保持着暧昧关系,也许我天生无法抗拒优雅的男人,挣脱不了束缚男人的欲望。我可以和恺说一些书,一起看一些书,在白天的时候偶尔做爱。恺友好地表示不会破坏我和宽的同居关系,我仍然在歇斯底里地寻找着宽偶尔写下的曲段然后把它们撕得粉碎。我始终愚蠢地以为那些会是我们之间真正的障碍,等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宽就会离我而去。
我始终没有找到工作,我对着人事部招工的主管脸红脖子粗地说脏话,让等在外面地宽失望透顶。他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本科毕业生会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我就这样寄生在他的世界里,蚕食着属于他的一切。
我只想留住他。
我要恺替我查关于宽老家的情况,我甚至于嫉妒起那个因难产而死的女人。
这样的嫉妒几乎是源于我对他的不贞,这样的情况很好笑,我在宽努力养活我们的时候,跟另一个男人偷偷地幽会。末了还怀疑起宽是否会对一个死人念念不忘。
常常,我自以为是。
我把长发剪掉后,和过去一样坐在Y2K的吧台上。宽还没上场,只是一些漂亮的女孩子卖弄风骚地跳着健康舞。调酒师说宽很早就来了,在经理室里和经理说事情。我点点头,眼角再也看不到我的头发随着我点头的姿势上下浮动的景色。
烟逝(6)
Wendy告诉我,宽下午的时候去她那里把他的长发剃成了平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直以来都很依赖于自己具有标志性的长发,就连洗发水也要买女人用的最好最贵的,每个月都会去Wendy那里做护理,对于这笔昂贵的开支他似乎从来不在乎。可他居然在某个普通的下午剪掉了长发,还理了平头,最可恨的是我居然一无所知。为了报复,我毫不犹豫地剪掉了我喜爱的长发,恶作剧地理了平头,兴高采烈地出现在Y2K。
Wendy形容起宽下午的神情,用“晦涩”二字。他坐在Wendy的面前,只说了一句:
不要了,这个。
指指脑袋上的头发,在镜子里苦涩地笑笑。然后从面前的日本杂志里随便挑了一个发型,也许是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指到的一个平头。最后居然笑着说,这样子也好,可以让他左耳的耳环更加明显。
Wendy看着不明所以的我。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我摇摇头,从三年前认识宽开始,我们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争吵,或者说他根本不屑于和我计较;我不屑于和他理论。
我们有的只是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
我沮丧地说,我不要了,这个。
指指脑袋上的头发,在镜子里问她,宽要的发型是哪一种。
Wendy抱来一大堆杂志,说她也记不详细了,一本本开始翻起来。最后终于在一个通页版上找到那个男人的脑袋,我点点头。我要像这个这样。
Wendy细眉细眼地咯咯笑着。
宽上场的时候,下面一阵尖叫。熟识的女客人开始起哄起来,宽像平日那样痛苦万分地摇晃起脑袋来,只是他的平头在灯光下显得有些不够艺术。他径直走到话筒前,撕开嗓子大叫起来,依然穿着黑色的HEAD,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件。
突然宽沉默起来,他低着头。
我和所有的酒客一样以为这是他突然爆发前的一个标准的“摇滚式”故弄玄虚。可是他突然向前鞠躬,然后把脸凑向话筒。
他的嘴巴几乎贴在了话筒上,
这是我在Y2K的最后一次演出,明天中午我就要离开上海……
后面的话无非是一些无聊的谢谢酒客捧场的话,我断定那是经理要求他说的。我跳下吧台无所顾忌地跑到台上,一言不发。我看着宽,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情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经理尴尬地把我从台上拉到后台,宽就不顾几十个吧台上起哄的声音,跟了过来。
跳健康舞的女孩子又一次仓促出场。
我们似乎都用新奇的眼光注视着对方,我不习惯他的平头,显然,他也不习惯我的平头。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的头发,
我明天中午就走,去广州。今天下午买的票,我对经理说了,这半月的出场费都给你,月底的时候你过来取。
我走上前,温柔地低下头开始像平时那样咬他的肩膀,他却一声不吭。我已经闻到牙齿缝里的血腥味,他还是一动不动。
他从一个眼熟黑色的皮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要去唱歌了,下台的时候不希望再见到你。
他蛮横地抽去我咬着的肩膀,带着血印上台去了。
信封洒落出来我和恺的照片,甚至于我们在“CaliforniaPlaza”吃饭的照片也拍得有声有色,还有那个夜晚,夜幕里流星雨划过天际。外面乐队开始演奏强烈的ROCK,微微颤抖着的空间。后台的孤寂如死一般。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那些照片。
回家才发现,宽在我兴冲冲地剪掉长发的时候已经整理掉自己的行李,抽去关于他的记忆。他在桌上留下一句话:
你已经有人照顾,我应该走了。
我端详了半天,也不没弄明白这是什么颜料写上去,触目惊心。
我仔细地洗澡,然后躺在床上闻到平头上散发下来的CLAIROL的香味在毫无知觉下睡去。宽已经走了,我寻遍所有的中午启程的火车都没有他的影子。似乎像一阵烟那样,三年前他无声无息地飘过来,在“黑蕃”唱黑豹的歌,三年后,他又无声无息地消失。
理所应当;一切都理所应当。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小屋里呆了多久,睡了多久。在厚重的窗帘后似乎没有了白昼黑夜,我倦了闭眼,醒了睁眼,往复循环。
恺打来了电话。
听完电话,我昏昏沉沉地直起身子,拉开厚重的窗帘,灰尘开始在我的周围跳芭蕾,不停地旋转,阳光射进来,我眯着眼睛,一下子看不清东西。
我还是选择洗澡,用洗澡来缓解我紧张的情绪。我带着一身香气从浴室出来的时候,突然在阳光低下看见桌上的字是紫色的,那些暗紫色的字在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