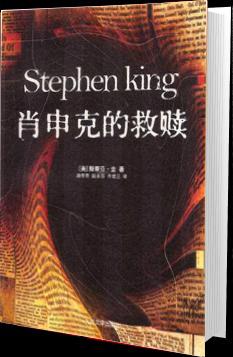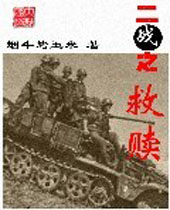赎-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庙的内堂供着的是一尊连龛只有一米来高的释迦牟尼,四壁上是西方四圣还有些神神佛佛,内堂的顶和教室的一模一样,尖顶横梁垂下一根散去朱砂色的条幅:南无阿弥陀佛。尊座前是一个打坐用的垫子,有一个窟窿,二马就一屁股坐上去学着老和尚的样子妈弥妈弥地念起经来。后来老和尚从库房里拿出两个崭新的垫子丢在地上,别磨坏了,要用到来世的。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所指的“来世”是指下个世纪,以为是下辈子,那该多久吓?就小心翼翼地坐在新的软绵绵的垫子上,明戒师父(老和尚的法号)就开始拿出木鱼先念经,由着我们在正堂内堂里穿来往去。
正堂里供着的是个笑嘻嘻的弥勒,二马说他太肥了,一定吃了很多东西才会笑得那么开心。弥勒身上的彩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青石头,斑斑驳驳的,让他的神情看上去更加的滑稽。正堂也是尖顶衡梁,只不过垂下的是双道朱砂条幅: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四壁上是各种弥勒的姿势,有坐着的,躺着的等等等等。二马就开始抱着垫子放在地上摆出各种姿势:三姑娘,你看像不?
像!
等到明戒师父做完课,就开始在正堂弥勒佛的面前给我们说一些佛经的故事,通俗易懂的,类似于释迦摩尼佛祖是如何在菩提树下顿悟化生体验到困扰人世的十二因缘三世二重因果,我们也就听得兴致勃勃,而内堂是不容嬉笑的,明戒师父说虽然这个古庙大致是荒废了,但还是得有规矩,不过弥勒要和善很多是不会计较我们两个小鬼的喧哗。二马用屁股扑扑地撞底下的坐垫,师父啊,你的意思是释迦祖师不和善?
罪过罪过。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和明戒师父有近四年的交情。院子里的石榴又开始落掉花慢悠悠地结石榴果,早些时候明戒师父开始借给我们看一些直排装订的书,我说这和阿婆的一样,因为我在库房的藤条书架上看到了我认识的最初五个汉字《大般涅槃经》,其实是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明白原来这五个汉字是和佛经等同。
明戒师父一直都很喜欢嵌在我手腕里的那个用红绳系着的佛铃,他说那个是静安寺开过光的,那时候他还在静安寺做沙弥尾,一共有五十个这样的纯金佛铃在那里开光,都是大户人家为子女求得的。
二马拉起我的手腕,疼吗?都长到肉里去了。
不疼,阿婆说不可以松。
明戒师父说他是那十年里被协会派到这个镇上来看这座基本上废置的古庙的,因为那个时候静安寺也不太平,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红色小兵闯进来厉声厉色,拉出几个“秃驴”,割掉一些尾巴之类的。所以他就很欣然地接受教会的安排,带着一箱书来到这个尚算安宁的小镇。他形容第一次来到真如庙的那个早晨:
晨光微曦。
我说,明戒师父你有没有看到在梨园浜边上刷马桶的女人?一定有我阿婆。
二马举着我的手,铃铃铃地摇着佛铃:三姑娘真笨,和尚不可以近女色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才十字出头,二马也不过十三四岁,阿婆和梨园浜,和尚和女色,马桶和真如庙一概地毫无逻辑被我们牵扯上关系。
我是不喜欢佛经这类的书的,不然家里外婆的那些佛经我应该已经熟记于心。相反的,我对于明戒师父给我的唐诗十分的喜爱,当然那些都是王摩诘的;相反的,二马却对于扭扭捏捏蝇头小字直排繁体的佛经出奇地喜爱。于是我开始翻动外婆房里白木书箱里的那些佛经,还有一些梵文版的老佛经拿给二马看,后来却是明戒师父读了梵文版的那些经书,二马因为连繁体汉字都认不全只能垂头丧气地看着明戒师父捧着枯树叶似的经书专心致志。是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二马只不过是对于蝇头小字直排繁体的汉字产生了兴趣,而不是经文本身,而梵文在他看来显然要比汉字更为使其动心不已。
后果(4)
这样的主次颠倒本末倒置的状况在后来是时常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如在图书馆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习四角号码查字法,为的是能够从《经籍纂诂》里找到自己姓氏的来源。可是等到四角号码查字法学习熟练了以后却忘记学习它的原因,沮丧万分。而我这样的状况是在上大学也就是离开真如镇之后,可二马,我始终认为他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习惯。比如砸碎大块的红砖头,拆掉家里的洋伞。
我究竟姓什么,这在我上小学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甚至一点这样探究的念头都不曾有过。生活在梨园浜边上的人管外婆叫凤姨婆,管我叫三姑娘。后来参加入学考试的时候,在蜡黄的考卷上我用三星牌木头铅写下的名字仍然是:三姑娘。一直到外婆带着我在音乐教室边的教导处填入学档案的时候,才看见王沽这两个汉字,回家的时候外婆把门口的老藤椅挪进屋子,说:囡囡,记住,以后你的名字是:王沽。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字迹过于潦草还是根本我对于这个名字没有亲切感,常常的,新来的老师都会把它们叫成:王洁。现在想想,似乎“王洁”是一个更为贴切的姑娘的名字,而“王沽”则仅仅是三姑娘的缩写,可我为什么姓王,不是别的。后来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因为大一些的时候在户口簿上看到外婆的名字:王书凤。我想我是随了她的姓吧。这样的疑团解开后,突然我又发现,户口簿上的地址并不是梨园浜,我就是这样慢慢意识到自己竟然一直生活在解不完的疑团里。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是明戒师父《王右丞集笺注》里我以为自己最能读懂的一首,至于别的念上口总是不明所以。其实一直到后来,也就是我带着外婆的那些书离开小镇后,才发现原来若干年前,自己只能是算作是在看诗,谈不上读诗,至于懂,那就更为的遥远。
二马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在明戒师父看来却算作了顿悟。
又一年的秋天,银杏树叶张着扇形的绿黄弄得古庙门口脏兮兮。明戒师父就又拿着扫吧“吱呀——”一声推开褐灰色杨木门,不同的是,这次我和二马不再是站在银杏树底下茫然地看着他锃亮着脑袋,而是随在他的身后。梨园浜边上的人家几乎都已经知晓我和二马与这个老和尚交好,或许因为和尚这个位置怎么说都是安全并且高尚得神秘的,所以并不若我和二马原先想的那样,阿爸姆妈外婆会有很大的反对。相反的,外婆开始成为这个古庙第三位有缘人。
师父(二马管明戒师父就叫“师父”,比我要亲切得多),原先不是有个年轻的师父和你一起扫地的吗?他人呢?二马已经利索地爬上银杏树。
的确,从那个老狼几点钟的傍晚开始,我们所见到的古庙里的和尚就明戒师父一人。
他走了,明戒师父弯下身子用手刮掉因为下雨粘在泥地上的银杏叶子,他那时犯错了,和一些大学生一起在中山北路上砸了人家的面包车。
似乎泥地上的银杏树叶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清除,那是个雨水充沛的秋天。明戒师父索性撩起海青,蹲下身子,开始用手一张一张揭贴在泥地上的叶子。我也开始蹲下身子,和他一起揭树叶,每揭一张泥地上就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扇形,有一些蚂蚁就在这个扇形里爬来爬去,显然是下雨前蚂蚁搬家的迷路人。
所以他被调来和我一起看这个古庙,之先也是做沙弥尾的,念起经来音色很好可惜就是冲动了点。出家人是不可以这样的,是不可以这样的。
二马一转眼已经爬得老高,师父那他去哪了?
还俗了,受不了这里的清苦。他说这里太臭了。
“嘭——”二马就这样摔了下来,可以说我和明戒师父都惊呆了。
二马是侧着身子摔下来的,幸而因为是泥地,加上水分充足,整个泥地是柔软的。不过他还是吓到了我,因为他就直挺挺地侧着身子,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我哇地大声哭了起来,明戒师父放下海青疾步走了上去。
二马——明戒师父把他扶着坐了起来。我抬头看看他刚才爬到的高度,一枝树干折佘了。没事儿吧?明戒师父举起他的手摸了摸,还好没舍。
二马却一声不吭。
我手上还攥着一枚银杏叶子,用手掌抹了抹脸颊上的眼泪,外婆说我不可以在秋冬天哭的,不然我的脸上又会涔出干巴巴的印渍。
二马突然就笑了。
三姑娘,你这样还真逗。
明戒师父突然站了起来,走回横着扫把的地方。弯腰拿起扫把,回过身子,对着二马说:
顿悟。
佛祖拈花,迦叶一笑。
可我不是佛祖,手上拿着的只是一枚银杏叶。可二马却真的顿悟了。
或者说,明戒师父看出二马终会顿悟。
这当然是在更久以后,我才渐悟到的。我一直都承认二马比我有更为灵活的思维,他看经书也似乎是一夜之间才专心致志的。
我和二马最大的差别也就是“渐”和“顿”之间。
“渐”谓“先习小乘,后趣大乘,大由小起。”
“顿”谓“不习小乘,而直说大乘之无上法门《华严经》。”
外婆是在明戒师父借给我看《王右丞集笺注》时,发现我开始和古庙的老和尚成了“有缘人”的,随后她又发现白木箱里的经书少了几本。
后果(5)
外婆就开始去敲那扇杨木门了。
她是去要书的,因为那是她最为珍惜的东西,可是后来,反而书没有要回来,相反的,最后连白木书箱也一起搬去了古庙的库房。外婆身上开始也有了弥久不散的印度檀香的气味,云云绕绕的。
有的时候,我和二马会在古庙里遇上外婆。她坐着一个崭新的垫子穿一身灰蓝色和明戒师父在内堂里打坐念经,我们就搬自己的垫子去正堂,看明戒师父借给我们的书。
很快地,梨园浜四围就有了闲言碎语。关于外婆和明戒师父的。
镇政府开始思量着怎样利用废置的古庙房赚钱。也许是借鉴了某个中学的破墙开店,他们决定把古庙的库房整理干净,破一个窗口,做面包房,这当然是要得到明戒师父的同意,毕竟他是佛教协会派来这里打理真如庙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戒师父并没有为难镇政府,点头答应了。
二马已经搬离了梨园浜,因此只有我和外婆去帮明戒师父整理库房。原本整个庙是有内堂、正堂、偏堂和库房的,还有一个算不上宽敞的院子。现在就只剩下正、内堂和院子,偏堂很早就借给我的小学作音乐教室,现在库房又要变成镇的面包房。
明戒师父搬去了内堂,在释迦牟尼的背后搭了床,扎了帐子。把藤条书架靠在闭落脚里,明戒师父撩起帐子挂在帐钩上:这是注定的,一个和尚一个庙,半个厢房香火燎。
外婆就利索地把库房里搬出的一些新的旧的海青、坐垫、木鱼什么的放进白木书箱,和那些梵文经书什么的挤在一起。还有一整箱印度檀香,这是每半年佛教协会送来的,我趴在纸箱上闻到没有点燃的檀香的气味,冲得很,立刻就不住地打喷嚏起来。
三姑娘,阿坏特纸箱,就糟蹋檀香了!气!外头白相气!外婆掏出手帕擦我的鼻子,又用力地拗我的屁股。我已经十五岁,跑起来佛铃还是不住地响。
书凤,随她去吧。
我清楚地听见明戒师父这样称呼我的外婆,似乎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什么时候他不再管她叫“三姑娘的外婆”,也不和浜边上的人一样管她叫“凤姨婆”,而是叫她的名字,没有姓氏。
二马是一年之前搬走的,他的爸爸做股票发达得不得了,就在市中心买了房子,走的时候他搬来飞行棋之类的玩具摆在我家门口,我是看到的,就一声不吭地搬了进去,关上大门。
后来,我想,他应该是去古庙和明戒师父告别了。
还有那棵银杏树。
就在二马从银杏树上摔下来的第二天,我问外婆:阿婆,“顿悟”是什么?
就似灵光各意思,一记头开窍。外婆坐在阳光里,还是那把老藤椅。
我就拉着二马去爬银杏树,然后兴奋地从树上跳了下来。一屁股坐在柔软的泥地上,懵了。我预期的灵光和开窍都没有,只是觉得下腹部开始变得热乎乎潮湿的,脚跟处还有一些黄绿的银杏叶子,清楚地看到上面的纹路和一些不知疲倦的蚂蚁。
三姑娘,怎么了?二马从树上串下来。
二马抓着我的胳膊拉我起来,我脑袋还是晕乎乎的,下腹部的潮润感却是越来越明显。
三姑娘,你流血了!
四周还是有雨后秋天南方盐碱的气味,我穿的是浅褐色的薄棉裤。
我看不到自己身后的状况,只是别转头拼命地低下,想看个究竟。伸手一摸,果然湿漉漉的,手指上有淡红色的液体。
我就蹲下来哭。哭得很动容。
那时我是以为自己被蚂蚁咬了,就像银杏树那样。
血!那么多蚂蚁咬我,我就出血了。
三姑娘,这个,这个好像……你好像来月……
二马吞吞吐吐的,我挣扎掉他的手,顺着野桑树拼命地跑啊跑啊,我的腹部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脸烧的很厉害。
二马没有追上来。
从那以后,每个月,痛经如期而至。
而我和二马就再也没有一起玩过,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甚至于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会知道那些。那天晚上,外婆说:
囡囡,侬长大了。
我长大了。是的。后来我知道,二马念的重点中学已经开了人体卫生课程。
我和二马都很希望在小学毕业后能够考进一样的中学,像杨树桥下面的重点二中。
二马念的是镇的中心小学,而我念的只是一家建在残破古庙里的小学。明戒师父说命中注定,那年重点二中把原来给我们学校的一个名额划去给了中心小学,这样二马学校的名额就变成十一名,而我们的就是零。
画一个很大的圈,回到原处,那就是零了。
结果,我依旧是第一名,二马是第十一名。
二马的姆妈来发糖的时候,外婆脸色很不好看,说了“又不是结婚,发什么糖”之类的,甚至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