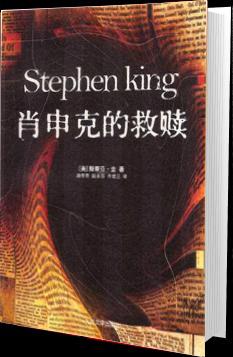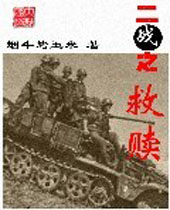赎-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结果,我依旧是第一名,二马是第十一名。
二马的姆妈来发糖的时候,外婆脸色很不好看,说了“又不是结婚,发什么糖”之类的,甚至于之后二马在我家门口野桑树底下叫“三姑娘”的时候,她竟要赶他走了。我愣着看,她转脸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
去吧去吧。
我就放开腿,跑着跟在二马身后。跑到一半,转身看一下,外婆又坐在门口老藤椅上,在阳光里愣愣地看着梨园浜边上的矮墩。
我看到明戒师父牵外婆的手,在弥勒佛祖的面前,我想起他说过,弥勒比较的和善。
后果(6)
古庙开始不烧印度檀香,虽然如此但我依然可以清晰地闻到,或者说是想到或嗅到那样的味道,云云绕绕的,弥久不散。
有顾客开始埋怨面包房卖的面包有一股檀香的味道,让人倒胃口。有些称自己见过市面的人说那味道和市中心高级厕所里的味道一样。所以,谁都不肯买有厕所味道的面包了。镇办公室的人又找到明戒师父,奇怪的是,他们还没开口,明戒师父就把内堂正堂的印度檀香灭了。
可是不知为什么,面包房的生意却没有因此好起来。
梨园浜边上的邻居开始怂恿我管明戒师父叫“阿公”,她们的眼神里有轻易可以捕捉到的不屑,我说和尚是不可以近女色的(这是二马曾经说过的),于是她们就夸张地大笑起来,提着马桶一扭一跨地说说笑笑走过我的身边。
念到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发胖,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外婆说我像她,她也是这个年龄开始发育完全的。发育完全后就要发胖么?我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不过,我还是以惊人的变化迅速胖起来。
这样一来,我的手腕开始越来越难以忍受佛铃红绳的束缚,我觉得疼,紫色的淤血。我伸手给外婆看的时候,她居然痛哭起来,泣声:造孽,这都是造孽。
外婆从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洋铁皮匣子里取出一把黄铜剪子,扣着我手腕上的肉一刀剪下去,佛铃就应声掉在她温暖干燥的手心里。我清楚地在白炽灯微黄的灯光下看到手腕上一道清晰的横沟,四周是紫色的淤血。
外婆把佛铃放在我的手心里,囡囡,这个你要收着,佛祖面前开过光的。
我用拇指和食指撵起佛铃,放在耳朵边上摇起来,“铃铃铃铃”,这是小时候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因为我胖起来,现在如果奔跑,佛铃只是颓答答地靠在手腕肥赘的肉上,没了声响。我想到明戒师傅的话,把脸转向外婆:
阿婆,我们是大户人家么?
一种亮光,兴许是眼泪折射的白炽灯光。总之,外婆的眼睛里闪过一点亮光,随后把黄铜剪刀放进洋铁皮匣子。
很晚了,睡吧,明天还要考试的吧?
她起身关掉白炽灯,我抬头看着灯泡,亮光一灭,眼前就闪出一个蓝绿色的光影,头开始晕玄起来。外婆身上印度檀香的气味还是充满了整个空间,我就这样昏昏沉沉睡去。
中考后,我还是没能进入真正的重点高中。因为地域限制,我们的小镇出来的优等生只是进了镇上的一家准重点的私立高中。
二马则顺顺利利地直升了重点二中的高中部,只是这次他姆妈没有再拿喜糖来发给大家。事实上,自从二马搬走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梨园浜。有关于他们的消息,只是多多少少从去市中心和他姆妈搓麻将的姆妈们那边传来。
他家的旧房子一直空着,没有出租也没有拆掉,每次上学的时候,我总能看到。我还能想到我在野桑树底下叫“——二马”的日子。
虽然之后他就没有再去过古庙,可明戒师父总是说他还会回来的。
你说二马,明戒师父?不会了,他们搬走了,市中心离这里很远。
明戒师父就不言不语。
面包房已经关门大吉,库房也腾空出来,只是明戒师父没有把东西搬回去,也许是想省得再搬出来。古庙又开始烧印度檀香,外婆说那是她最喜欢的气味。
我说,我也是。其实,除了印度檀香之外,我已经辨别不出任何的气味。
进高中的那年开始,我的体重急剧下降。
手腕处被佛铃红绳勒出伤痕已经变成一道肉色的印迹,我一直都在想如果我再戴上佛铃一定不会觉得疼了,可是我却找不到它。
我失去那夜用拇指和食指撵起它放在耳边摇出“铃铃铃铃”声响后关于它的记忆。
它就消失了。
可我的体重却真切地下降再下降,是否还是得益于外婆的遗传我不知道。外婆也没有告诉我她发育完全后是否发胖,发胖后又是否恢复正常,甚至于比原先还要的瘦小?
我也没有问。
我已经习惯了接受一个又一个疑问,却从外婆那里得不到任何的答案。
我再一次见到二马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他的模样。只是他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五块钱一张的“香花券”,冲着明戒师父叫“师父”。
就是这一声“师父”让我捕捉到很多年前二马的样子。
他已经从重点高中辍学。从梨园浜零星的消息源那里知道,原因是暴力倾向。
他的爸爸早一些的时候吞掉了厂里的公款炒股,亚洲金融风暴多多少少影响到国内的股市。于是一切都曝光了。
一切都曝光了。
二马站在银杏树底下这么对我说。阳光透过银杏树叶打下来,银杏树已经不再是我们触手可及,它的周围用黑色的铁栅栏圈了起来,上面挂着一块铝合金锃亮的牌子:千年古树——银杏。
银杏树叶掉下来几张,展着扇形落在柏油路面上。古庙的门口还有上等的大理青石铺排着,二马闭上眼睛。
你在干什么呢?我抬头看着他。
看过去。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过去这里的样子。
我闭上眼睛,
我也想看过去。
当很多人都展望未来的时候,我和二马站在我们都熟悉不过却陌生的地方寻找记忆。依靠闭上眼睛来寻找过去。
后果(7)
一瞬间,整个空间安静下来。奇怪的是,我闭上眼睛看到的第一个影像是那晚外婆关掉白炽灯后留在视网膜上的蓝绿色的光影,我就顺着这个光影慢慢地看过去,依顺着回忆寻找过去,这一刻甚至能够听到银杏树叶掉落在泥地上,啪嗒、啪嗒……
也许只有嗅觉是回不到过去的。
虽然我们的嗅觉系统已经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变得不那么灵敏,但是无论是两年前的我还是现在的二马都闻辨出了古庙里不同的香味。
二马睁开眼睛:
三姑娘,师父烧的香换了么?
我停止追溯,睁开眼睛,点点头。
一年前,我用同样的口吻问外婆:
阿婆,明戒师父烧的香换了么?
那是昂贵的伽楠香。
我进大学的第二年的秋天,外婆在家门口的老藤椅上睡了过去。
赶回小镇的时候,四周的人告诉我:你阿婆走了。
明戒师父给外婆做法事,他的徒弟们跟在身边,外婆的照片和骨灰放在古庙的院子中央。这本是不可以的,但明戒师父是这里的住持,他坚持也就没人反对。
我跪在地上,是否哭得厉声泣气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没有看到二马,他应该走在明戒师父的徒弟的最前面的,因为他是大弟子,理所应当的大弟子。他脑袋上的戒疤应该已经完全脱痂,露出淡粉色的戒疤。我看到别的弟子有的也已经烧了戒,大家专心地跟着明戒师父围着院子念经,“度”外婆的今生来世。
只是没有二马。
可以闻到的是印度檀香的气味,和过去的一样,云云绕绕的,弥久不散。
二马在那次见到他后的第三个月——或许久一些,整理了一个简单的包裹回到小镇。他告诉我,他的爸爸判了无期徒刑,他的姆妈死了。
孓然一身。
他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的现状。
孓然一生。
他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今后的状况。
我清楚地看到他下巴青色的胡渣,二马离我很近,我却看不清楚他的脸,自从第一次在古庙的院子里见到明戒师父被太阳光折射到视网膜后,我就成了深度近视。(这在前面,我已经叙述过了。)
二马并没有回到那第十三棵野桑树斜对面的老家,而是让我陪他一起去了古庙,正门口的红木牌上雕刻着:真如古刹。
就在面包房关门后不久,镇政府办公室的人又来到古庙,和明戒师父在弥勒佛的背后说了半天话。走的时候,握住明戒师父的手说:
报告已经打上去了,您今后就是住持。
明戒师父清淡地微笑。
弥勒佛笑得非常的和善。
不久,镇上开始大兴土木,那块明代的牌坊被整修一新,从牌坊开始,后面的小街整体拓宽,两边的房子全部推倒,造起了仿古建筑群。
而古庙也开始不太平起来,原来的弥勒佛说是年久失修不知道被一辆蓝色的卡车车去了哪里,释迦牟尼也被涂脸抹身体的,金色的,丹红色,亮光彩彩。古庙开始翻修,明戒师父也就没有了安静的地方念经颂佛,于是他开始常常来我家,那箱白木书箱和藤条书架也一起搬了来。
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那些邻居:
三姑娘吆——你阿公在你家哦,晚些回去吧,可别搅和了好事啊。
随后哧笑着扭着腰跨着步走开。
我开始不知道正确的回家时间,来回在家门口,看着当年外婆刷在青石墙上的红漆大字,一直到明戒师父从里面出来:
三姑娘,怎么在门口站着不进去?
我不作声,咬了一下嘴唇,居然咬破了,尝到血腥的味道,跨步进去。
外婆合上大门:
囡囡,阿是又听到什么乌七八糟的话了?
我看到桌上摊开着一些经书和梵文字典,觉得自己和那些婆娘一样无聊。
那以后,明戒师父总在我放学之前离开我家,我回去也看不到桌上有任何的经书,丝毫没有明戒师父来过的痕迹。
我开始初中最后一年的冲刺,毫无结果的冲刺。因为在这之前,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地域限制,小镇上的孩子进不了重点的高中。于是,镇政府利用古镇要办旅游景点的商机和一位深圳老板谈妥在镇上建一家私立的高中,设备完全按照重点高中的要求,生源也严格控制。
果然,那一年这家私立高中的分数线并不低于杨树桥下的重点二中。
私立高中承袭了古镇考试的做法,贴出了考分前十的红榜。
外婆又开始拿着喜糖奔走相告:阿拉囡囡教怪聪明,第一名。
小镇被纳入这座城市旅游节的一个特色景点,所有的建筑都标榜上“古代建筑”。牌坊用褐色的油漆漆得锃亮,上面的字用金粉重新勾勒。古庙的老杨树门不翼而飞,一扇气派十足的黑漆带俩抓环的铁门和两尊公母狮子。
明戒师父穿着绣金丝的新袈裟,站在拓宽的院子中和镇长并排站着。镇长缓慢却有力度地说: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小镇……
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站着的地方,曾经是一棵石榴树,像模像样的果实,如拳头那么大。
一些在静安寺烧戒的年轻和尚陆续地安顿,明戒师父指着最大的一个说:你是二师兄。
后果(8)
似乎从那天开始,整个镇上的人才意识到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原来还有个可以进香拜佛的地方,女人老太们再也不用乘几个小时的汽车去静安寺烧香,每一天,古庙用它和颜悦色的新面貌迎接所有进进出出的“有缘人”。
我站在家门口,总是可以看到古庙方向飘起的香烟,云云绕绕的,气味却清淡得让人疑惑。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问外婆:
明戒师父那里是不是着火了?那么大的烟。也不是檀香味的。
古庙开始不烧廉价的印度檀香。
佛教协会不再运檀香或是海青坐垫之类的过来。明戒师父说一切镇政府都包了,镇办公室的人说:
我们一定会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古迹文物也是职能部门必须做的。
我记得他,有天他来到古庙,委婉地说:
明戒师父,顾客投诉面包里有印度檀香的味道……
二马回到小镇的当天就住进了古庙。第二天梨园浜周围的姆妈开始交头接耳奔走相告:
阿马的大儿子要出家了。
剃度的仪式由明戒师父亲自主持,这是这座古庙修复后的第一次剃度仪式。
仪式在小镇所有人看来都是神秘的,而镇政府则聪明地打算安排一个旅行团进庙观摩,当然额外的费用还是相当昂贵的。
有我在,不相干的人今天都不准进来!
我是第一次看到向来和颜悦色的明戒师父有这样的神情,从小学进庙开始明戒师父都应该是妥协的,和顺的,与世无争的。可我今天却清楚地看到了微红脸色的明戒师父,看到了神情沮丧的二马。
二马拉起我的手走到门外的银杏树下:
三姑娘,可不可以亲一个?以后,以后我就不能近女色了。
阳光打在二马的头发上,那些很快就要不复存在。
你在说什么啊,现在的和尚还是可以结婚的。
我甩开他的手,像很多年前从银杏树上摔下来的那天一样,甩开他的手跑了起来。我开始闻到明戒师父灭掉伽楠香重燃印度檀香的味道,所有关于小镇、外婆、童年、古庙、明戒师父、佛经、古诗、银杏树、杨树门、石榴树……一切一切的记忆开始袭击我的视网膜,我又开始觉得眼睛疼痛,闭上眼睛看到那些过去以光年的速度重新开始重新演绎重新生长重新变化……
外婆以现代的方式火化后,根据遗嘱,洒进梨园浜。
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肉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选择清澈的溪流或是气势浩瀚的汪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肉体的灰尘进入这条粪便、死猫都会漂浮的梨园浜我还是不知道。
不过很快,镇政府决定把这条浜填掉。因为有游客埋怨它太臭。
所有的人都嫌它臭,只是我们和它一起生活,所以麻木——或者不是麻木,而是习惯。
没人告诉我二马去哪了,明戒师父只是说:他是个顿悟的孩子。
我的小学不复存在,学生和老师合并给镇中心小学。音乐教室很早就还给古庙作为供游人买纪念品的偏堂,我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