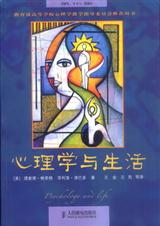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张抗抗-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主讲人简介: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66年初中毕业,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在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50余种。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全国第三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德艺双馨奖,以及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奖。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曾出访南斯拉夫、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
内容简介:
我们都知道文学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我们怎样把生活中的感受变成文学?而作家的文学素材是从哪里来?是不是必须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作为一个作家,他在生活当中,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是为了写作去关注生活?还是由于关注了生活,作家才会写作?这些都是每一个写作的人经常困惑的问题。
那么生活到底是什么?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而生活中的人们就是一个个的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要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你的感官有问题了,你的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还会不会感动?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真是不能写作。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作家,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年一直笔耕不辍,有好多作品。一提作品呢,大家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这两部是这几年引起了轰动和争议的,今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请带我走》,她就是作家张抗抗女士,大家欢迎张女士上场。
说到文学写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文学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提炼生活素材又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的,很多写作者呢往往是一头雾水,以至于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怎么老上不了道。所以今天呢,我请张抗抗女士为我们来讲《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大家欢迎。
张抗抗:朋友们大家好,像我这样二十多年一直在从事写作,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房里面度过,但是当时八十年代还谈不上书房。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面对着纸,面对桌子,以后是面对着电脑,或者是面对着很多书本。那么我们写作的这些素材和写作的那些文学作品,它所承载的那些内容和思想,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一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呢?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那么我是生活在我的写作当中?还是生活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我的心理状态。我究竟是生活在写作中呢?还是生活在生活中?这有点绕嘴。第三呢,我是为了写作而去关注生活的呢?还是由于我关注了生活,而我会写作?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有兴趣知道的问题。因为今天面对我们大量的书籍,我们那么多的写作者,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恰好昨天我很偶然地看报纸,看到一个笑话。我有时候比较愿意看一些笑话,轻松的版面。它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很淘气,他淘气就被他爸爸打了一顿。闯了什么祸了,他爸爸就打他。那小孩就非常委屈,他就去跟他妈妈说,假如说你的孩子被别人打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希望在他妈妈那儿得到一些同情和支持。这个笑话是比较幽默的,如果你的儿子被人家打了你会怎么样?他妈妈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我就会把他的儿子打一顿。这小孩一听,坏了,因为把他的儿子打一顿,那么“他”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儿子还是他自己。我看了这个笑话以后我觉得很好笑。我想想有意思,我突然找到了某种关系。我就拿这个笑话做个比喻吧,因为这个比较形象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是它这个主体相对的这个客体两个对应的父母实际上落到这个主体上它仍然是一个人,还是这个儿子。所以他期望得到同情和支持的时候呢,结果反过来他很可能受到的是另一种落在他头上的一种报复。就是把他的儿子打一顿就是又把他给打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笑话,它用一种幽默的形式阐述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我要讲的写作和生活的关系。
尽管任何比喻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任何比喻都是有偏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它像在哪儿呢?父母他是这个儿子的创造者,那么必须有父亲和母亲才可能创造这个儿子。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比喻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父母是什么呢?产生这个作品,产生这个作品我们从文学上讲,从写作上讲,产生这个文学作品,它的父母我觉得就应该是生活。而单独有生活它是不可能,仍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生命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它需要的是思考,它如果没有思考和这个生活的结合的话,你就占有无穷无尽的生活,你占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它依然不能创造生命。我不知道我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没有。
我们先来讲生活到底是什么呢?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生活对于作家来讲,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信息,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的一种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实际上我觉得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甚至充满在空气当中,充满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它在任何地方,我们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存在,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它也是某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个接收器它在接收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全方位地在接收。你不可能说我走到哪儿把眼睛闭上。当然特别恐怖的时候我把眼睛闭上了,你也不可能到哪儿说我不听。你在公共汽车上都会听到传过来的两句对话,是不是?你在散步的时候,你走过去的时候,走过去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在任何时候,你的接收器都是打开的,那么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哪些东西是被我们用电脑的术语说它会被粘贴,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个我想根本上是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所以我想说,因为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在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被这种理论驱使到黑龙江去,驱使到北大荒去。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我们要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后来我发现生活它不是要你到某处去,它才有生活。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我这是引申的他的这句话。我们总是认为生活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那么我们拿《作女》来做比方吧,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大概看起来是如此雷同。上班、下班,然后今年流行滑雪就都去滑雪去了,那么在这种我们大家所感觉到非常重复的或者说是雷同的、相似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究竟还有哪一些东西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个我想这就给写作者提出很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写《作女》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呢,很少关注女性文学,或者女性小说。我想八十年代我写了大量的书都是跟“人”这个概念有关,“人性”,所以写《作女》它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想,比如说写女性小说,它写什么呢?婚外恋、家庭关系和子女的关系,然后是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或者是写女强人的事业发展过程。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仅仅是文学。因为它有很多我们今天的媒体、新闻它都可以记录这些事实。文学是什么呢?你得找到它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把它能够提取出来。下面我会讲到我的小说《请带我走》那本小说,里面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芝麻》就是很多很多琐碎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但芝麻它不是文学,你得把它磨成香油的时候,它才是文学。所以面对这么大量女性现象的时候,我非常想为中国的女性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对很多女性问题的看法。那我从哪里下手呢?不能写。我一直没有找到根本的那个核的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个核,我就不能写。我写出来的话,我又跟别人大同小异,讲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已经太重复了。
后来呢,就是在我这样反复的思考当中,我碰到了那个字就是这个“作”字。这个汉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当中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那些特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女性,她区别于西方女性,或者区别于亚洲其他的女性。我突然碰到这个“作”字的时候,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老家是杭州人,我们杭州人用这个“作”字是用得很多的,还有上海人,上海人也是用得非常多。这个词就是单用在女人身上的,或者是小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每次到她家去,你都会发现她们家的家具又搬过地方,她隔两礼拜她不调整一下她难受。她觉得我每天进来都会面对这样子固定的地方。家里面就这么大嘛,对不对?她不可能隔三个月换一个房子是吧,每天进来的那种重复感,她觉得家里每次走的路线都是一样的,我拿东西的这个动作都是一样的,这个生活简直是不能忍受,那怎么办?搬家具呀,把它换个地方。后来我的小说一出来,人家说对呀,对呀,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得到了很强烈地呼应。女孩子不断地换发型,然后她头发长了要剪短,短了以后再养长了,养长了它烫了,烫了又给它拉直了。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很短的小文章,是《南方周末》还是哪儿,它说头发七次改变发型就走完了女人的一生。我原话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说,它说头发是女人改变自己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吧。她有的时候改变不了生活,改变不了命运,那怎么办呢?就改自己的发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吧,总之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真的是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在我写《作女》前一年,我有一个朋友在郊外买了五十亩地。挺大一个庄园,她说是庄园,然后说让我一定到那里去看一下,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一个五十亩这么大的地方,里面盖了一个房子一个平房。房子里面非常混乱,当然完全没有乡间别墅印象中那种庄园的感觉。因为她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根本忙不过来。然后一看五十亩地全种的玉米。我说你应该全种树,种点苗圃。她说是呀,明年就开始种树,今年先种点玉米。然后养了十个狗,分别关在五十亩地的各个角落。各个不同的方位全都有狗。每个狗都被关在铁笼子里边,关在十个不同的地方。我说如果碰到歹徒的时候,你怎么能把你的狗把它放出来?你如何迅速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救你呢?她说反正到时候有办法。然后每个狗面前都放了一个脸盆,里面都是玉米糊糊。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干吗?她说看玉米呀,这么多玉米丢了呢,她说得看玉米。那我说你种那么多玉米干吗?喂狗。我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回来你就得想这事,你不能说你乐了回来说这人神经病。我们通常会这样看待问题。可是我想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女主人我认识她从三十岁不到我就认识她了。她现在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也快五十岁了,充满着热情对她的生活。我觉得狗和玉米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不产生效益的这么一个过程性的一个事物。种了玉米喂狗,狗来看玉米,那么她效益在哪里呢?没有效益,她的效益在于她过程中的快乐。她喜欢狗,所以她养了很多狗。狗得吃呀,所以再种玉米喂狗。这个过程中,她觉得她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又养活了这些狗,她又看到她五十亩地长满了绿色的庄稼,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当然这是个很极端的例子。首先我们得有很多的钱,我们得买得起五十亩地。我们还得去买得起十条狗,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说的是她也不是有很多钱的人。但是她有一点钱,她的钱用在能使自己快乐的地方。她也不是什么大款,但是她觉得这种方式她觉得非常愉快。因为她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她虽然是一个不产生效益的同义反复。但是,她的快乐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要去做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