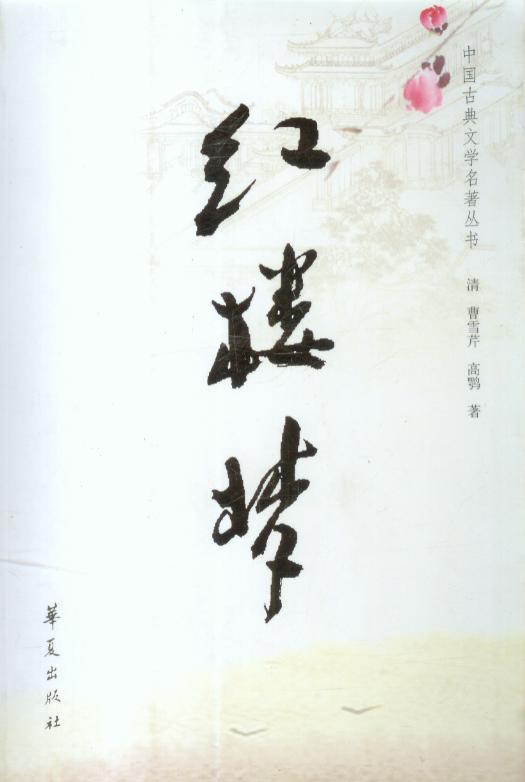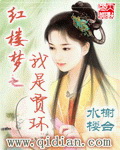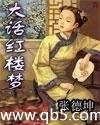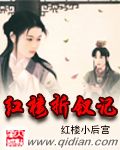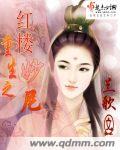定是红楼梦里人 作者:周汝昌-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五十篇 七宝楼台——“胡适派”?
综观张爱玲的红学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论点很多,就中以下列数端尤为居要而凸出——
她对雪芹原著,爱之深。
她对高鹗伪续,斥之痛。
爱之深,却无正面颂赞、赏会之音。令我想起“至大无名”,她大约是不想轻下一字的断语。因为,一下断语,就“框”在那句话的范围等次之内,就是贬低了雪芹。
因此,她对伪续的痛斥,口不留情,以至惊倒俗人,却正是反衬她对原著的无比热爱崇敬。
原著与伪续是貂狗,是泾渭,是云泥,是冰炭……。这是她的最大原则,断不容混淆,更不容调和。
这也正是她在红学上的最高品格,最分明的宣言——这就是一种贡献,因此力斥恶疽,捍卫本体。
她的心思极为细密,记忆力之高强令人惊叹不已。她毕竟是女流,故其考证,具有女性的特长与特征。
她看清研究与认识《红楼梦》,必须由版本学入手。文本是非正误还弄不清,所谓鉴赏评议又从何谈起?这就说明:反对考证,反对版本研究,即是不懂“红学”为何事何务。
张爱玲的版本学,并不是“胡适派”,这是一望而可知的。所以,版本考证并不与“回到文学创作上来”的红学革命论调有什么势不两立。她的研究,正是为了文学创作。
所惜者,她研究考证的结果,却把雪芹之书“肢解”了,弄成一个“支离破碎”的七宝楼台。
不知是在海外无法对作者雪芹生平概况作些研究以便与他创作过程更紧密地联系一下,还是她对此并不感到有其联系的必要?总之,她的版本研究似乎只看书本子而毫不考虑雪芹彼时是何困境了,以致太多地想像那些表面的“矛盾”,就是她大拆改的遗迹疏漏了。
她治红学中,无论“脸色”还是“眼色”,都是端庄正派的,认真严肃的,不像有的人那样不光明,不正大,有居心,有心计。她的品格是高尚的。因此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怀念。可励后学,可医文风。这也是她一大可师之处。
最重要的,还在于她虽博通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而且具有很高的“小说史观”评论,但她终究没有陷入洋八股的牢笼中。她的考证见解和文字风格,还是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即须有相应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和修养,方能写出像她那样的文章,并不让人感到洋气熏天,眼高一切,动不动引洋人洋书,吓唬老实人。她懂中国诗,也有古代文学的根基,此点可供后人做一深长思。
张爱玲的重要贡献是她在实际上承认了“自传说”,也承认了脂砚是女性,是湘云的“原型”。
在这一要义上,她却以迷惑眼睛的标题让人发生极大的错觉。她说“是创作,不是自传”,而看完了全书,方知她所谓的“创作”是指“大拆迁”“大搬家”,并且以这种自认为“定案”的“创作”方法来证明“不是自传”,然而她又承认麝月是留在作者身边的丫鬟(即书中人乃是真有其人),承认大观园是作者、脂砚从小萦思结想的失乐园!
你看,她的自矛攻盾,又是多么明显而又“隐蔽”!
不过,我在此“揭穿”了她的文词表面与认识内衷之间的矛盾,就分清了现象与实质,就让读者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的一种欣幸和快慰。
诗曰:
不拘一格降人才,久叹才难究可哀。
才女如伊能治学,中华文化是胚胎。
第五十一篇 绛珠是谁
张爱玲考证黛玉原先无有,是后来由湘云“分化”而虚构出来的人物。
她这一妙语,必使世人大为震动,也难以接受,因为从来就是黛玉的红楼梦,如何能“让与”湘云来承当这一“重任”?
张爱玲所说,有理无理,其立论能否成立?俱不必先行判案,应当从另一个线路去审视一下,看看有无特异的迹象,才是讨论的步骤与道理。
我想让大家先温习一下第五回宝玉神游这段奇文中的大可注意讨究之处——
那是宝玉到后,警幻“自我介绍”已毕,便唤众姊妹出来接待贵家。于是有四仙姑出现。她们见宝玉,便都怨谤警幻,说道:姐姐曾说今日今时有绛珠妹子的生魂来此游玩,故我等久候,如何反引来这浊物污染我们清净之地?
对此,警幻并未正面答解,让人自己去玩索:第一,绛珠到底来了没有?警幻没说她不能来的原故,又来了一个“小厮”“浊物”,是何情理?她都避开了——当另有不答之“答”。
于是,我们必须再听一下她先对宝玉说了些什么。请注意——
……因近来风流冤孽绵缠于此处,是以前来核察机会,布散相思。今忽与尔相逢,亦非偶然……
让我提醒你:凡到这种地方,如不懂雪芹的独特笔法,你就会莫名其妙而泛泛读过,把含于文内的要害当作闲文了。
第一,“风流冤孽”要在此“绵缠”者,是谁?第二,说宝玉今日相逢,亦非偶然——即是预先注定的机缘,此又何疑?第三,“绛珠”的生魂早已预定“今日今时到此游玩”,这一注定也并未撤消或“改期”。此为三要点!
只要一综合,这三点说的是什么?就大大有趣了!“译”出来就是:“你之来非偶然。绛珠之来亦预定。所谓风流冤孽在此绵缠者,即是宝玉、绛珠二人”清清楚楚也。
——这可让人吓了一跳:难道是宝、黛二人曾同入太虚幻境而“绵缠”相会吗?
非也。
因为,下文说明了,警幻之“妹”名“蒹美”者,是兼钗、黛之美点,另是一女,绝非黛玉“单个”了。
这就奇了,还有谁呢?
还有的,不是别个,就是湘云。
理由也分明:只有湘云是兼钗、黛之容貌才德的,别无第二者具此资格。第二,不要忘了,宝玉入梦前所见室中所悬之画,正是“海棠春睡图”。第三,室中对联明言“芳气笼人是酒香”,只有湘云是能饮而“香梦沉酣”的。
——有人说,弄错了,绛珠妹子只能是黛玉,与湘云难以钩连。我答:你忘了,湘云的牙牌令正是九点满红,牌副儿名色是“樱桃九熟”。而雪芹之祖父曹楝亭(寅)之咏樱桃诗,正谓“瑛盘托出绛宫珠”。“绛珠”的出处与本义,就是樱桃。
得“绛珠”牙牌的,是湘云,不是黛玉!
(可参看《红楼夺目红》)
其实,张爱玲也已推考了:湘云幼时依史太君而住于荣府,与宝玉一处,并曾与袭人说过小女孩心中天真烂漫的愿望:等长大了和你(指袭人)一同嫁二哥哥作夫妻。
这才是“太虚幻境”一回奇文奇境的真情实义。
但张爱玲已然“参”透了雪芹文笔狡狯的一个层次,却未进而深究。这里显然就是她只被“绛珠即黛玉”的假方式给“固定”,就不去想想瑛为红玉盘,绛珠是樱桃的典故了。
诗曰:
瑛盘托出绛珠红,幻境传来幻笔工。
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评坛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誉世界而兼作红学研究的,以张爱玲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响,超迈等伦。
这是事实,并非夸张抬捧之俗态。
但,红学流派甚多,风格各异,她属于什么“派”?价值何在?为什么她有过人的见解和成就?这都应该深入考论一下,方能使流辈获切磋之功,后贤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个“胡适考证派”。
她不是书呆子,弄书本,作校勘,别的不会;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译,创作小说剧本,曾获最高评价,列榜第一。她读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不知其数,烂熟于胸中——这样,才真算有资格作个被人嘲贬的“考证派”。
她的红学学识,集中在作者、版本两大方面,就表明了这即是“胡适先生红学”一线的继承者。
她学贯中西,所以不仅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朴学”的流风遗韵……。
这就值得世上自命为“红学家”的许多人闻声失色。
“胡适考证派”的骂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远之。“红学革命”的呼声也不满于以研究作者、版本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这个“考证派”,曾被认为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想回头”,呼喊“红学革命”。这“命”怎么“革”法呢?据说是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
这个“革命口号”和“宗旨”,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红楼梦》所以产生“红学”的内在原因是不知重视的,对中华文学传统的“知人论世”这条原则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学创作”这个观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那么,这种“革命”由学者教授去领导、实践好?还是由大作家担任好?
无疑,应属后者,而由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实现“红学革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不知缘何,让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证派”,即“革命”的对象!
这个事例十分耐人寻味。
张爱玲在香港生活,后转美国,她应早已闻知那个在香港首倡的“红学革命”了;可惜她没有认识这条新道路。
她的“考证”可谓变本加厉,细腻之极——也繁琐之甚了!
我并不喜欢她的“考证走向”。我佩服她治学的精神态度,专诚挚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创获,为人所不能见,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认一部伟大作品须有一个大家基本共识可读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即应视为艺术既定型体,而不再是逐步制作、修改、打磨、润色的“历程”,即片段的积累组织的“工序”状况。无奈,张女士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却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组缀,如何改动,如何“补苴”……。
曹雪芹的《红楼梦》,魅力由哪儿产生?绝不会是那么琐琐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张爱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为“用武之地”了。
对此,我是惋惜而感叹的。
诗曰:
尽如己意世间难,何必吹求仁厚宽。
敬佩心情兼叹惜,通达理会味悲欢。
第五十三篇 人间恨事多
张爱玲有人生恨事,从海棠无香到《红楼》未完、狗尾妄续。我今效颦,也列三恨——只指看罢《梦魇》的三点恨事——
第一是她拆碎了七宝楼台。
南宋才人吴梦窗(文英)的词,文采奇丽,人所惊叹;便有人说“闲话”,说他的词像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
此乃嫉才,有意巧加贬词也。
不服气的就反击:好好的楼台七宝,谁让你拆的?若都拆碎,哪座楼台不是“片断”?何独梦窗之惊才绝艳?岂非有意“找岔子”?
而张女士偏将她自己一生最爱最迷的红楼绝作,亲自动手拆得七零八落,“大卸八块”(旧时杂技戏法的一个名色,将一个活孩子“卸”成零块)。
此一恨也。
张爱玲在一部书中,讲的都是大拆大改、后添后加;这都是女主角的故事。唯独不讲全书中心主角贾宝玉——他在这么多的“拆迁添凑”中是怎么样的地位、关系、感受,表现上又有何变化,即随着她自信的大量拆添而发生的相应“改写”和“加文”,又皆何似?
我不信她对宝玉这个中心人物“不感兴趣”,也不信她的创作理论中是可将宝玉置而勿论的课题。
原因不解。此二恨也。
对《红楼梦》,考证、研究、索隐、猜谜、“挥拳”、吵骂……,都所为何来?其中有个理解认识之争,观照鉴赏之异。无论高层解悟还是低层“看热闹”,至少有其内心感动享受的一个方面:故事?人的命运?书的意蕴?抑或文笔的优美,境界的超逸……,总得占其一项,方是道理。
但是,张女士于此,又是一字不言,翻尽“全集”,也难巧遇。
使她最“着迷”、最陶醉的,到底是什么?
竟不可知。此三恨也。
随带着的是,她承认了脂砚是女性,是作者自幼相爱的亲人。后来又为之作了批书人,书名即定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对此,她岂无感受之源,考证之理?因为,这太重要了。此即整个红学的一个最核心、最要害的隐秘——“真事隐去”。难道她又真的漠不动心、置而弗论?我不相信。
真实如何?无人解之。
这么重大的几点,闭口无音,却写了一本“九连环锁”的《红楼梦魇》来,目的何在?学创作——也用此法?寻奥义,自此得出新悟?为艺术享受,由是而在精神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高价值的艺术天地?
不明白,没答案。
我陪她绕了无数的一回“蚁穿九孔”的大圈子,终愧智低不悟这有何益?
人间恨事多,此其一例耳。
和尚说宝玉:“自从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是极。梦之有魇,皆由自寻,通灵如她者,也正是投入人间自己找了这么一个“魇虎子”(注)。
不免兴叹,不免伤萦怀。
诗曰:
人间恨事几重重,读罢奇书梦魇中。
到底通灵为何事,不知何处问芳衷。
甲申清明佳节写讫
'注'魇,乡语“压虎子”,第二字轻读,不知是否“虎”字。“压”即“魇”,不念yàn。
卷后不尽思(一)
写这册小书,一为“补课”,向她学习,以偿1987年“失之交臂”之憾。二为对此才人致我甚深的哀思,觉得她对红学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而我们却没有相应的答报之可言,是应该反省而谢过的。
看看张爱玲的多方面的造诣,看看她自述诸文章中的散碎回忆录,也足证她对中华语文、艺术、饮食、陈设……的博通与会心,处处闪烁着灵性的光芒,非庸流俗辈所能梦见。——也就是说:这种被名之曰“红学”的研究,是中华大文化之高层次的事业,绝非“小说文艺”这一观念所能理解与解决。眼前的例子就不乏其尤显者,名作家不自禁地步入了“红学”这个独特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