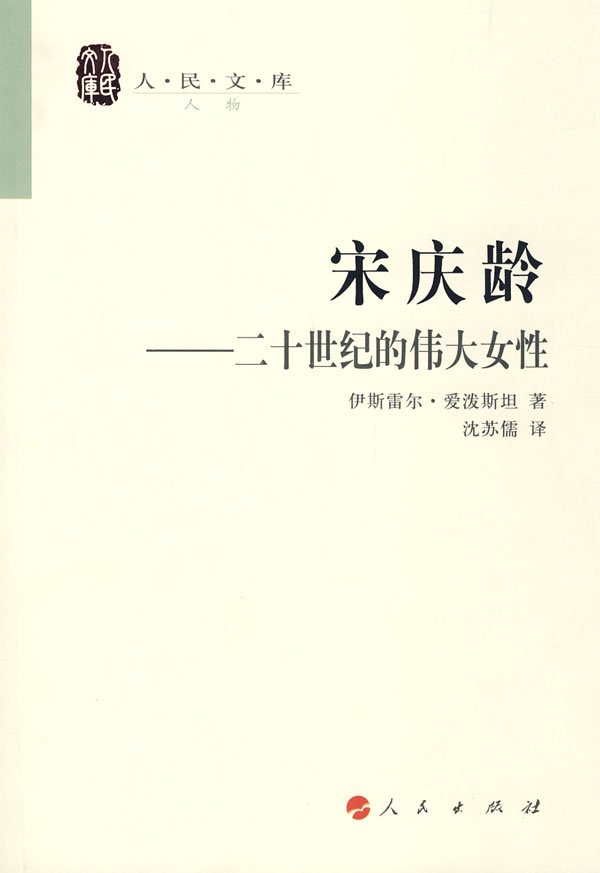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个基础上,经院哲学在大学的工作范围内,通过它特有的评注方式发展起来。
练习课程:“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
经文的“评注”(lectio)是基础。这是一个深入的分析,从细扣“字词”(littera)的语法解析开始,进而达到提供“意义”(sensus)的逻辑的说明,最后以阐明科学与思想内容(sententia)的诠注作为结束。
评注就会引起讨论。辩证法使得有可能超出对经文理解的范围,并处理理解经文过程里产生的问题;于是经文退居对真理的探求之后。诠注由一系列疑难问题所取代。经过相应的处理过程,“评注”(lectio)转变成“研究”(quaestio)。大学知识分子就在这一时刻诞生了,这时他对只是一份基础材料的经文“提出疑问”,这时他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determinatio),是他思想的成果。
在13世纪,“研究”甚至完全脱离经文。它是独立存在的。在教师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下,它成了讨论的科目,从此它成了“辩论”(disputatio)。
曼东涅修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段经典的描述:“当有教师举行学术辩论时,学院里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师和学土们开设的课程全都取消。只有主持辩论的教师简短地讲一点课,直到助教们到达,然后开始辩论。他占用那天上午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学院全体学士和辩论教师的学生必须参加这一练习课。其他教师和学生似乎可以做自由选择,不过视辩论老师的名望和讨论的课题而定,参加人数无疑相当多。巴黎的教士和院长主教们,以及其他途经巴黎的教会人士们,看来都非常喜欢这一激动人心的论战。辩论是教士们的竞赛。
“辩论的题目事先由提出辩论的教师确定。这些题目在规定日期内通知学院的其他部门……
“辩论在该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但实际上他不是辩论人。他的学士担任答辩者的角色,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学习这种练习课程。来自不同的方面的异议,一般首先由在场的教师们提出,接着由学士们提出,最后也许由大学生们提出。学士解答列举的各个论点,必要时教师给予支持。简而言之,以上所述是一次通常的辩论过程,但这只是第一部分,虽然它是最主要和最生动的部分。
“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固定程序提出,没有驳难的异议,最后形成相对地说不是那么有条理的教学材料——但与其说它们是战场上的残骸,不如说它们是建筑工地上的半成品。所以继这一预备讨论后,是第二步的‘主导论证’。
“在第一个讲课日,当时人们这样说,也即主持辩论的老师能够宣读讲稿的第一天(因为星期日、节假日或别的原因可能会妨碍第二天继续辩论),教师在自己所在学校,再次把头天或前几天辩论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首先他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把针对他的论点提出的异议,按照逻辑顺序或依自然次序列出,最后确定它们的最后措词。列举这些异议后他就自己的理论作若干论证,然后再就辩论的问题举行了一个内容多少增加了的讲学报告,这是‘论证’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他逐一答复针对他论点的理论所提出的异议,这样练习课就结束了……
“由教师或听众笔录下来的‘论证’,形成文稿,我们称为‘辩论之问题’,它们是‘辩论’的最终文本。”
在这一范围内,同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形式:随意性辩论。教师们每年可以举行两次会议,他们在会上即兴发挥,讨论“不论什么人提出的不论涉及何种题目”(de
uuolibet ad voluntatem c…us-libet)的问题。格罗吕伊主教关于这一练习课程有以下的描述:“会议大约在四、五学年间或第六学年开始举行;不管怎样都在早晨开始,因为可以长时间地进行下去。它的特点正是在于它的随意与即兴式的方式,以及在会上飘荡着的捉摸不定。它是一种辩论的会议,论证的会议,像其他许多别的练习课程一样;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主动权教师转到助手们手里。在通常的辩论中,教师事先通告题目,事先加以思考和进行准备。在随意性辩论中,谁都可以随便提出什么问题,而这对接受提问的教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敌视的或好奇的问题与异议,跟往常一样,会从各个方面袭来。人们可以怀着善意征求他的意见,但也可能试图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逼使他探讨他极不愿意谈起的棘手问题。有的时候是好奇的陌生人或不安份的家伙,有的时候是心怀忌妒的对手或好奇的教师,试图让他陷入困境。有时候问题十分明晰与有趣,有时候问题又含义双重,确实叫教师感到实在为难,难以把握它的确切外延及真实内涵。有些问题都是属于光明正大的纯知识领域;另一些问题却主要含有政治性的或诽谤性的用意……所以谁要是打算经历一场随意性辩论,那他就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决断能力,和几乎有通晓万物的学识。”
这样,经院哲学严格遵循理性法规,作为学术上严谨的教师和创造性思想的激励老而发展起来。西方思想借助理性的法规已取得显著进步,理应永远保留它的印记。当然,这是就 13世纪由机智和严谨的思想家们所运用的、处在全盛时期和繁荣兴旺的经院哲学而言的。中世纪末期那种狂热的经院哲学,它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谟、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视。巴曼克式的经院哲学,也势必引起马勒伯朗士的厌弃。但经院哲学的精神与传统融合进西方思想新的进步过程中。不管笛卡尔怎么说,他得力于经院哲学的地方就很多。艾金纳·吉尔森在其所著的那本重要著作的结论部分写道:“如果不坚持把笛卡尔主义同经院哲学对照起来看,就无法理解笛卡尔主义。笛卡尔主义鄙视经院哲学,但本身又植根在经院哲学之中;因为笛卡尔主义采纳了经院哲学,由此人们可以认为,笛卡尔主义从经院哲学中汲取了养料。”
矛盾:如何生活?靠工资还是靠领地?
然而同样由于经院哲学这一武器,13世纪的知识分子却要面对许许多多捉摸不定的苦恼,并且必须作出一些困难的抉择。这种矛盾状况在大学一系列危机的发展过程里表现出来。
第一类问题是物质性的。它们造成了深远的后果。
首先一个问题是:怎样生活?一旦知识分子不再是由自己的团体关心的修士,他就必须自己设法解决生活费用。在城市里,食宿、衣着和装备问题都令人操心,书籍是昂贵的。从现在起,大学生活越长,费用就越大。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教师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学生或者靠助学金,或者靠教会薪俸。工资可以有两种形式:教师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或者从世俗权力机关方面得到报酬。助学金可以是私人赞助者的赠予,或是经由公共机构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提供的资助。
在这些解决办法后面,有着不同的责任。第一个基本选择是工资收入与领地收入之间的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感觉自己像个工匠,像个生产劳动者。在后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靠他的职业,而是他能够从事这项职业为生,因为他是领年金者。由此决定他的整个社会经济地位:他是劳动者呢?还是特权阶层的一员?
在这第一个选择中,体现出另一种虽然程度有限,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意义。
作为工资收入者的知识分子,在学生们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商人;在地方当局或封建王侯给他工资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官员;而当他依靠赞助者的捐款生活时,他就是某种类型的仆役。
知识分子在依靠教会薪俸生活的情况下,同他担任的特殊角色相联系,能够得到一份领地,这使他成为一名专业化的教士;或者他能够继承一份领地,这就已经把他同另一种牧师角色,即教区神甫或修道院神甫联系在一起。随之他变成了在担任教会职务外偶而为之的知识分子。
从12世纪以来,人们部分地根据地区和时代的条件,部分地根据个人的处境和心态而作出抉择。
但仍可以确定总的趋势。教师们倾向于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力,即不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资助者的长处。这样的解决方法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最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惯例,他们觉得自己就属于城市。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与学说,就像手工工匠出售自己的生产成品。他们为这样的做法提供了许多辩解的理由,它们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的辩解理由是,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有报酬。忏悔神父的手册确认了这一点:“作为工作与辛劳的代价,教师可以接受学生们(collecta)的金钱。”大学成员们经常向人提起,1382年帕多瓦大学的法学博士们是怎样公告于世的:“依照我们的观点,劳动者不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报酬是不理智的。因此我们宣布,凡以学校名义接受一名学生参加自己的讲解答疑的博士,应该从这名学生那里得到三磅啤酒和四瓶葡萄酒,或一枚杜卡特金币,作为对他工作的认可。”由此也就发生了教师们对不情愿付钱的大学生的不满。波伦亚大学的著名法学家奥多弗雷杜斯就曾写道:“我今通知你们,明年我将以我过去一贯表现出来的同样的认真态度,完成份内应尽的专业课教学,但我不想提供额外的专业课,因为学生不是好好付钱的人。他们希望长知识,而不想付钱,正像俗话说的:‘人人愿意增长知识,谁也不愿为此付出点代价。’”
就学生们方面说,他们首先努力争取从自己的家里或慈善家那里得到资助,这是我们根据他们那些或者是真的或是在通信手册中作为例子引用的信件中得知的。
教会,特别是教皇们,把处理这一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他们宣布一项原则:教学无偿。这样做的最合法的理由,是希望对那些穷苦学生敞开大学的大门。另一理由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并与那时狭义地说只有宗教课程的时代有关,它把知识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知识就是买卖圣职罪。对这种观点来说,教学是教士天职(officium)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圣伯纳德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稿中,把教师们的收益称为“可耻的利润”(turpis
quaestus)。
教皇们因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宫教廷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就已宣布“教学无偿”的原则,他的继任者时常引用这一决定。与此同时,每个天主教大教堂附近都应开设一所学校,它的教师靠授予领地获得可靠的生活保障。
由此教堂也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绑在一起,因为知识分子不得不请求教皇赐予领地。这样一来,教皇们卓有成效地阻遏了或至少延缓了知识分子转化为世俗教徒的运动。
这样一来只有甘心情愿在物质上仰赖教会的人,才能够成为大学教授。虽然有教会极其顽固的阻力,在大学以外肯定仍然还有世俗的学校,不过这些世俗学校不从事普通教育,只限于技术性的、主要是为商人需要开设的课程:书写,会计,外语。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之间的界限就这样划分开来了。由此教会从英诺森三世代表的立场中,获得了它的重大影响力。英诺森三世在他的《对话录》里说:“每个有才智的人……都可以教学,因为他需要通过教学,把他发现是背离了真理或道德的正确方向的兄弟,引回正道。但布道,也就是公开的宣讲,只有另外的专门人员,也即主管灵魂拯救的主教和教堂神父以及修道院院长,才能承担。”在这个重要著作里,这位“教廷之王,”尽管对新事物抱着怀疑态度,还是承认了因普遍的发展而形成的教会机构与教学机构之间的必然差异。这种看法,无疑存在于一个充分基督教化的社会的具体历史联系中。但教会的最高层人士,至少在教会的布道者中间,承认了教学的世俗性质。众所周知,这段文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
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世纪数目众多的教师和大学生是世俗教徒。尽管如此,他们也向教会索要领地,这就给中世纪和大革命前旧社会制度时代的教会造成了一个巨大负担:教会收入与采邑分配给了世俗教徒。此外,在每个学校中心分给一个教师特殊领地的做法,很快显示出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教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通常的领地,这增添了教会的另一个苦恼:神甫们没有固定任职地点。
最后,教会的态度加剧了那些通过教学寻找非宗教性任务的人的困难,尤其是民法与医学。它们经常被迫处在非法的境况之中,因为首先是学习法律的热潮虽然中止了,但这一领域仍不断受到教会高层人士的攻击。罗吉尔·培根对此解释说:“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质。谁投身于这样一门粗俗的艺术,谁也就脱离了教会。”由于民法无法正式在大学中出现,一系列负有强有力地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命,但却丝毫没有直接的宗教性质的专业,在今后几个世纪之久就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冲突
一个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震动了各大学的严重危机,揭开了知识分子处境的两重性,以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不满。这涉及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斗争,涉及世俗化教士对来自新的托钵修会的教师在大学里占有越来越多席位的强烈抵抗。实际上,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从一开始,就试图打入大学;修会创始人的本来宗旨——布道和同异端邪说进行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