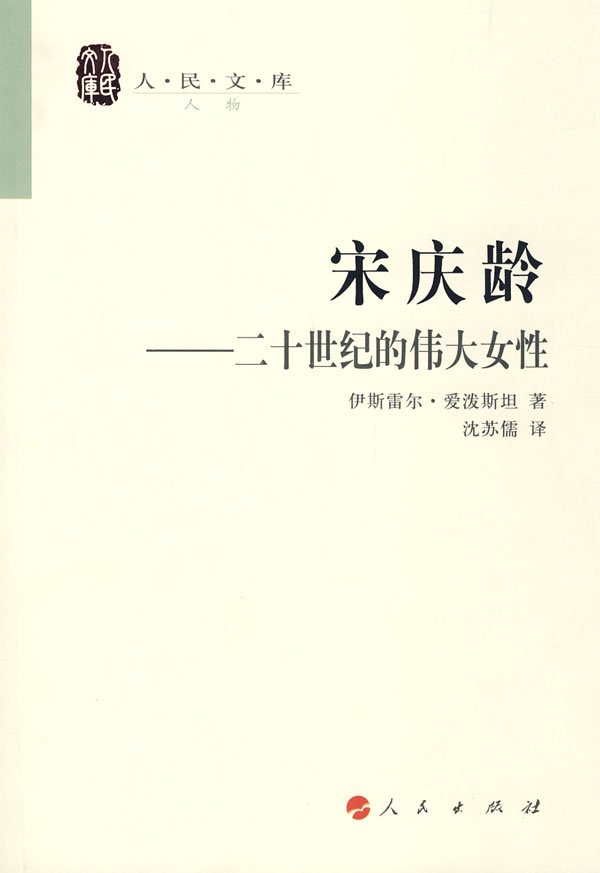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婚姻是一个可憎的束缚……大自然并没有神经错乱到这等地步,以致马洛蒂仅仅是为了罗比逊才安排到世界上来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还有为玛丽叶特安排的罗比逊,或阿格涅斯,或佩雷特;大自然替我们——对此不该有怀疑,乖孩子——替一切人安排了一切人……”
《玫瑰传奇》还以拉伯雷的风格,作了著名的长篇激情独白:“我的先生们,让上帝保佑你们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不知疲倦地听从自然天性的召唤;只要你们出色地创造自然的杰作(工作),我就原谅你们所有的罪孽。要敏捷得像松鼠,轻快得像鸟儿!加把劲儿吧!活动一下你们的五脏六腑!跳跃吧!别让你们冷却或发呆,挥舞起你们所有的工具……干起来吧!愿上帝保佑你们,爵爷先生们,干起来,并让你们的旧面貌焕然一新。脱掉你们的裤子,让它迎风招展,或者只要你们乐意,脱得精光赤条条,但别使你们太热也别太冷;用你们的双手举起你们犁铧的扶把儿……”以下写的文字就未太有失体统了……
这样一个沸腾汹涌的生命力在向敌人挑战,在向死亡挑战。不过就像凤凰一样,人类也始终是从焚烧的灰烬中获得新生的。在死神的肆虐以后,总有幸存者留下。“死亡吞噬凤凰时,凤凰仍继续活着;即使死亡吞噬掉千万只凤凰时,凤凰还保留着生命。这只凤凰是一个普遍的形式,它反映了个体的自然力,而当它不赋予其他人以生命时,它也就整个地消失了。宇宙的所有生物都有这个同样的特权:只要有一个样本还存在着,它的种族将由于它而继续生存,死亡也就永远够不着它……”在这自然对死亡的挑战中,在这一人类永远再生的史诗中,在这个狄德罗式的活力论中,哪里还有基督教的存身之处,还有什么“悼念来自尘土与回归尘土的经文”(Memento
quia pulvis es et in pulverem reverteris)的位置呢?
这一自然主义也可以进而发展成为卢梭式的社会理论。约翰·德·墨恩在他关于黄金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的描述中,把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弊病来描写,同时用原始平等的乐园来取代,在这个乐园中没有任何私人占有。“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他能守护茅屋,消灭罪犯和为申诉者实施公平,其权威没有人敢于冒犯;他们聚集在一处,以挑选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中间选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正直、最强壮和最有力量的人,使他成为他们的王侯和保护者。他立下誓言,在每个人都向他交纳供他生活的一定物品的条件下,他将维护权利,保护他们的家园;而大家也心甘情愿这样做。他长期以来恪守自己的职责。但狡猾的奸贼看他孤身一人,就纠集一起,经常偷盗别人的财物,以此骚扰他。为此民众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承担起捐税的职责,使王侯手下增添几位军官。他们自己共同纳税,向王侯交地租和贡赋,并把大量土地献给他。这就是世界上国王和诸侯的由来。我们由古人的著作了解到这一切,他们把这些古代的事实留传给我们,为此我们对他们怎么感激也不过分。”
信仰与理性的艰难平衡: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阿威罗伊主义
13世纪的知识分子会知道维持另一种平衡,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吗?13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探索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理性主义意义完全不同,经院哲学的理性也有不同于斯达吉拉的其他渊源,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仍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学说而进行的。
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不再是12世纪人们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他首先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主要是位著名的逻辑学家,现在依靠新一代的翻译家,人们进而了解到他还是位物理学家,著有《尼可玛伦理学》的道德学家,以及形而上学家。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注释。从一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附有阿拉伯的重要哲学家,特别是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评注。这些评注把亚里士多德推向了极端,尽可能地让他远离基督教的学说。
进入西方国家的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相反,至少有两个亚里士多德,一个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一个是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事实上还有更多,因为每个、或者说几乎每个评注者都有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但在这一运动中显示出两种倾向:一个是多米尼克修会的重要学者、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致力于把亚里士多德同圣经互相统一起来的倾向;一个是阿威罗伊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发现并承认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他们准备同时遵奉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圣经。他们为此发明了双重真理的学说:“一个是天启的真理……另一个只是纯粹哲学和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里是我作为哲学家的理性的答案,但因为上帝不会说谎,我同意由他启示的真理,并通过信仰把我自己同天启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阿尔贝都·马格努斯从另一角度作了说明:“倘若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当作上帝看待,必然由此出发,认为他不会有错。但如果人们确信他也是一个人,那就毫无疑问,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可能会犯错误。”圣托马斯深信,阿威罗伊“与其说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曲解者”,而阿威罗伊主义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说:“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已完成各门科学,因为迄今为止,也就是在十五个多世纪里,还没有一个后来者能够对他的著作有所增补,或在其中发现什么重大错误……亚里士多德是神的化身。”
不仅有对阿尔贝都和托马斯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强烈反对,还有对阿威罗伊主义的强烈反对。这一强烈反对是由圣奥古斯丁学说的信奉者提出的,他们以柏拉图为权威,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然而,尽管圣奥古斯丁是经院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但主要的经院哲学家们坚定地反对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新奥古斯丁主义。对他们来说,学院派的隐喻式思想是对真正哲学的严重威胁。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写道:“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见解时,他反对的主要不是基础,而是形式。因为柏拉图表述的方法很不好。在他那里一切都是形象化的,并且他以譬喻示教;当他举例说明灵魂是一个循环过程时,他在词句的意义之外又放进了某些别的东西。”托马斯主义反对这样的混乱思想;在整个13世纪,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奥古斯丁学说和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都在同理性主义的所有革新进行斗争,并维护保守立场。在13世纪,他们的策略主要是把亚里士多德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把圣托马斯同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托马斯主义一直紧接着阿威罗伊主义遭到攻击。
13世纪始终贯穿着反亚里士多德的攻击,这在当时是大学的危机所在。
从1210年起,巴黎的大学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1215年和1228年罗马教廷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十分正统的图卢兹大学从1229年建立起就宣布,为了吸引学生,在巴黎被禁止的著作将在该校讲授。事实上禁令在巴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受到裁决被禁的图书仍列在教学大纲里。托马斯主义出色的理论体系似乎已解决了问题,但阿威罗伊主义的危机又将对一切提出质疑。一大批人文学院的教师,由西格尔·德·布拉邦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领头,讲授着包括阿威罗伊在内的哲学家的激进论点——亚里士多德已成为哲学家的典范。除了双重真理,他们也讲授——否定创世的——世界的永恒性,拒绝承认上帝作为事物起因的特权——上帝仅是终结原因——,并否定上帝对未来偶然性的预知。有一些人——这在西格尔本人那里并不明确——赞成行动的悟性的独立性,并进而在个体的层次上否认灵魂的存在。
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在1270年已对阿威罗伊主义者作出了判决,圣托马斯也离他们远远的,并从他的立场出发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抨击。1274年他去世后,掀起了一个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大规模攻势。这个攻势在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拜宣布的双重判决中结束。
斯特凡·坦比尔列出了一份有219条被判为异端邪说原理的目录。那是一个庞然杂色的混合体。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阿威罗伊主义的论点外,大约有两打的原理或多或少涉及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另外一些原理引用了在哥利亚德激进派继承人中流行的见解,它们为阿威罗伊主义者所吸收——
第18条:哲学家不应该赞同未来的复活,因为这种事不可能通过理智进行检验。
第152条:神学建筑在传说的基础上。
第155条:人不必要为自己的葬礼操心。
第168条:节欲本身不是美德。
第169条:完全放弃肉体的结合,对美德和人类都是有害的。
第174条:基督教的法规,就像别的宗教一样,有传说的成份和谬误之处。
第175条:这是科学知识的障碍。
第176条:幸福属于现世,而不属于来世。
这一“要目”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多米尼克修会丝毫不加理会。罗马的埃吉丢斯解释说:“人们无需为此操心,因为这些说法并不是在巴黎的全体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提出的,而只是受某些浅薄愚蠢的人的指使提出的。”
神学院的一个世俗化的教师,方丹的戈特弗雷德对这份目录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消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发表和它不同的见解。
虽然禁令并没有怎么得到遵从,阿威罗伊学派还是因此被夺走了自己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肯定死于非命。他的死亡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据说他是在意大利被囚禁后遭到谋杀的。这位神秘的人物,由于但丁而获得了不朽,但丁把他同圣托马斯和圣波纳梵杜拉一起安置在天堂里:
这是西格尔的永恒之光,
他在福亚累街讲授知识,
用三段论推导不受欢迎的真理。
这一位不大知名的西格尔,是一个更加不知名的圈子的代表,这个圈子在一段时间里是巴黎大学的灵魂。
西格尔实际上代表了人文学院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管人文学院曾经有过何种声誉,它是大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人文学院里,实施的是基础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学院。
在那里,人们接触到贫穷的教士,他们还没有得到讲课准许证,并且更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博士学位,用他们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使辩论富有生气。在那里,人们同城市民众,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关心谋取神职的薪障,也最少去理会,是否会引起教会统治集团的不快。那里世俗的精神最活跃,人也最自由。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在那里结出了它全部的果实。就在那里,人们把托马斯·阿奎那的死当作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流泪痛哭。就是这些“人文学者”,在一封动人的信件中,要求得到这位多米尼克修会杰出博士的遗体,这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人文学院的阿威罗伊学派中,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最为严肃的理想。达齐恩的鲍依修斯申明:“哲学家(他这样称呼知识分子)天生品德高尚,清心寡欲,循规蹈距,正直、坚强而大度,温和又慷慨,庄重典雅,遵守法规,摆脱娱乐享受的诱惑……”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出自恶意、忌妒、无知与愚昧”的迫害。
“宽宏大量”——这个伟大词汇昭告于世了。就像高梯尔修士出色地描写的那样,人们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发现了高尚的最高理想,这一理想在阿贝拉尔那里,就是首创的美德,也即“希望的激情”。它是“对人类使命的热情,是人类力量的源泉,是对人的技能的信赖,它是帮助人类力量完成人类使命的唯一保证。”它是一种“典型的世俗的唯灵论,它是为那些植根于现实世界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再像僧侣主义唯灵论的门徒那样直接寻求上帝,而是通过人类与现世。”
理性和经验的关系
除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还有其他难于实现的统一,那就是理性与经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首先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是以杰出的学者、牛津大学的总监与林肯的大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术界,其后则有以罗吉尔·培根为首的牛津大学的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们。罗吉尔·培根在他的《大著作》( Opus
Majus)里确立了他们的纲领:“拉丁人已经在语言、数学和透视法方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我现在要研究实验科学提供的基础,因为没有实验数据,人们不能充分了解任何东西……如果尚未见过火的人,在理论上得出结论说火会燃烧,它会改变与毁坏事物,那他听众的心灵并不会得到满足,而且,在他把自己的手或其他可燃物放进火里以亲手验证结论之前,他不知道要防火。但一旦取得经验,心灵就会安定,并在真理的光芒中获得想息。这就是说,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这里经院哲学正在否定自身,平衡不久就要被打破,经验论破土而出了。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特别是医学家以及同他们有关的外科医生和眼镜匠,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阿威罗伊说:“没有事先的理论研究,仅仅通过实践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