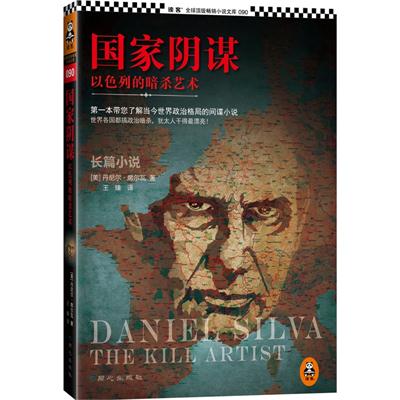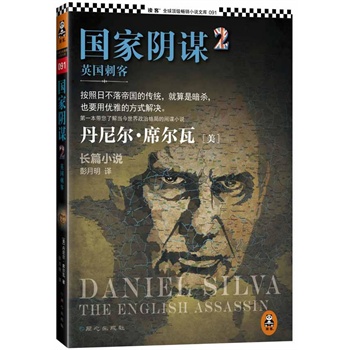国家兴衰探源-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国家管理还没有发展到繁琐的程度,而政府机构也没有那种稳定社会的特点。
这一理论也提出了对法国经济增长经验的一种新观点。当法国的投资环境经常处于劣境时,为什么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有较快的增长?(到70年代,法国国民收入可与其他先进国家媲美)外来侵略和政治的不稳定妨碍了资本积累,但这些因素也中断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由于法国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中一次又一次的大变革,其意识形态生活中的鸿沟必然加深。这些意识形态分歧的深化又将进一步削弱该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至少大的集团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劳联的发展在纳粹占领期间受到压制,以后又受到思想意识分歧的影响而受到阻碍:这种分歧将法国的劳工运动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三种工会。这些发育不良的工会经常是在同一工厂内竞争,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任何一种工会对工人也没有垄断性权威。因此法国工会对决定劳动法规或工资标准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无力强制工人入会,其结果就是大多数法国工会会员从不交纳会费),较小的团体如商业联合会和有名望学校的校友会(如推论3所预言那样)则能够较好地组织起来。但这类组织在最近20年来对法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受到下一章内将讨论的一些因素的限制,在那里还将阐述另一个原因,说明法国经济为何在60年代发展得比其动乱历史所预兆的要好得多。以上关于法国的论述也部分适用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被入侵的国家,受到这些组织阻碍其经济增长的危害也更大。利用这一推论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大英帝国 —— 这样一个主要的国家在长期未受独裁统治、外国入侵及革命动乱的情况下,在本世纪内它的经济增长率却比其他西方发达的大国缓慢得多。英国拥有非常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这一事实恰好与此处所述的论据相符,即在一个国防巩固和民主发达的稳定社会中所能预见到的情况,英国产业工会的数量及其势力已举世皆知而无须详述。该国各种专业团体的生命力和权威也是令人瞩目的。如果再考虑一下英国初级律师与高级律师之间的明显差别,这在没有英国那种职业协会或政府明文规定的其他国家自由市场上本来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英国,初级律师垄断了个人转让房地产业务中的法律事务,而高级律师则垄断了在重要的诉讼案件中作为法律顾问的专门权利。在英国还有强大的农民组织以及大量的行业协会。总之,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强有力的各种组织和行会,从而使它患上了机构僵化症,以致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
不可否认,在英国的院外游说活动不像在美国那么流行,但英国的游说往往更加广泛而且通过续密的安排来影响政府的职员以及部长和其他政治家。此外,在英国, “ 团体 ” 一词也获得了新的含义,尽管有时该名词可能被滥用,但它仍然代表那种非正式的组织,后者只可能在稳定的社会中逐渐形成。不仅如此,在英国很多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范围都比较狭窄而不是广泛性的。例如,在同一工厂里经常有很多不同专业的工会,每一个专业工会只包括某一工种或某一类工人,而没有哪一个工会可以包括全国大部分工人。英国也经常被引用为社会 “ 失控 ” 的例子。鉴于英国具有长期有名的民主传统以及英国人民向以奉公守法著称,近来居然社会 “ 失控 ” 使人特别惊讶,但正是本书理论所预言的。
与其他人的解释不同,本书理论对英国战后经济发展为何缓慢的解释符合以下事实。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即由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显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的确,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这就意味着不能从某些假定为英国人民或其社会所固有的或长期不变的特点来解释其近代发展缓慢的原因;因为这种分析是与英国过去在经济增长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相矛盾的。任何对英国相对增长缓慢的正确解释都必须考虑到逐渐发生的 “ 英国病 ” 。在 19世纪最后几十年内,英国的经济相对增长率开始落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多数对英国近代发展相对缓慢的解释都并没提出与英国近来显然不同增长率的历史经验相联系的时间模式,但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却能反映这种情况,即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和聚集(推论2)。
(三)
毋庸置疑,极权主义、动荡和战争使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锐减,而稳定与和平却使英国的这类集团持续发展。作者的同事彼得 · 默雷尔( Peter
Murrell)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团体成立的日期并在《各国经济团体一览》内刊登。虽然这肯定不是一份完整的资料,而且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有缺点,但它是在1973年出版的,因而这就不可能是在故意赞扬作者此处的论点。默雷尔从这些资料中发现:1971年在英国存在的各种团体中有51%在1939年以前就已成立,在法国此数为37%,西德为24%,日本为19%。当然,在1949年以后英国所成立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占29%,对比之下法国有45%,德国和日本有52%。英国各种组织拥有的人数显然要比法国、德国或日本的多得多;在这一范畴内相比只有美国的人数才大大超过了英国。当然,我们需要有一种对各组织力量及其会员人数进行权重的指数才能相互比较,但作者并未见过这种资料。
默雷尔为验证这一假说做出了一套巧妙的试验,可以校核英国因特殊利益集团而使其经济增长率比西德的增长率减少了多少。默雷尔推论说:如果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与英国的经济增长缓慢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在与西德对手相比较时,就应当发现英国的古老工业由于已有特殊利益集团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劣势,而新兴的工业则由于还来不及组织特殊利益集团,两国的经济效率相当。这样默雷尔进一步提出,英国新工业与旧工业的增长率之比应该大于西德相应的同样两类工业增长率之比。但为此要给出明确定义和进行计量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得不使用不同的定义和标准。将这些结果综合起来,就能清楚的看出:它们是与这一假定相吻合的,即英国新兴工业的增长率与旧的小工业的增长率之比要比德国新兴的工业增长率与它的旧工业的增长率之比更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结果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由于它们是统计上有效这一偶然性而产生的。此外,默雷尔还发现:在重工业方面,工业的集中程度和工会的控制通常比轻工业中更大,这方面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并且与以上论断相符合。
(四)
在很多其他的解释中,大部分属于肤浅臆测性质。某些经济学家把战败国的经济恢复速度归因于人的资源优势,并认为它比毁灭的物质资源更重要;但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大量的青年和训练有素的成人惨遭杀害,同时战争使教育事业和工作经验中断了许多年。然而,生产技术知识并没有被战争所毁灭,由于战败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战前,同时这些国家又需要重建被毁坏的建筑物或设备,因此它们的发展速度自然会超过平均增长率。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后,甚至在人均年收入超过英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比其他国家快。
另一个常见的肤浅解释就是英国人,或者说其中的工人阶级,不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卖劲地干活。其他一些人通常把德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它们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勤奋性格。就字面上说,这类解释也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虽然这在逻辑上可以归因于一个民族的勤奋 “ 增长率 ” ,但按上述论点的原意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某种程度的勤奋就必然会相应于某种收入的高水平呢?不容否认,当考虑到具有创造力的人们勤奋时,或考虑到努力程度和储蓄量之间的可能关系时,勤奋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即使把工作积极性的差别也作为一种解释时,还应当问为什么在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中人们反而更努力工作,而在增长缓慢的国家中人们却愿意懒惰?由于在争取更快增长率的竞争中很多国家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某个国家的人却勤奋起来的原因也需要加以解释。如果勤奋程度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话,为什么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曾经那么勤奋而后来就变懒了?同理,德国人在 19世纪上半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时,他们必定是懒惰的,而当佩里海军上将初到日本时,那些赤贫的日本人也是懒洋洋的吗?
一种看来有理的可能解释就是勤奋也是随着不同的国家内人们所习以为常的工作动力而变化的。这种动机,无论对于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企业家,都受到了特殊刮益集团降低生产劳动报酬与增加休闲这种有吸引力政策的强烈影响。在调查劳动意愿不同的原因时,特别是调查为何英国的怠工现象出现在经济增长率低于平均值时而不出现在增长率最高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经济体制的政策,以及本书内对于经济增长率差异的更本质的解释。
(五)
某些观察家试图用所谓的国民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程度来解释特殊的增长率。特别是 “ 英国病 ” 通常被归因于英国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生活。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不少在战后英国政府干预经济失误的例子。然而,塞缪尔 · 布里坦( Samuel
Brittan)在《法律与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并无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一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大;按政府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英国位于各国中间水平,而不是居于前列,正如按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的百分比计算,英国与德国和法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也是居于中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些年代中,英国政府异乎寻常地干涉较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过,但这也不会超出布里坦的第二个论点,即英国出现增长相对缓慢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大约一百年以前政府的经济活动还少得可怜的时期(可以附加一句,特别是在大英帝国)。
有些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当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当作一个集团看待时,似乎可以看出在政府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反的联系。这种更加普遍化的分析方法比前面那些肤浅臆测的解释更为高明,因此,按此理论进行统计的检验当然应受到欢迎。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上述关系似乎十分微弱,最多只能表明较庞大的政府和低增长率之间具有某种含糊和不确定的联系,其中只有日本是具有这一特点的最好例子,它既有高增长率又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最小的一个政府。本书的推论9中也预言了政府的相对作用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具有不太明显的相反关系。
(六)
众所周知的一种对英国增长缓慢的主观解释是归因于阶级意识,据说它会减少社会的流动性,养成了排他性和正统观念,从而阻碍了竞争和革新,并用中世纪的偏见来反对经商活动。由于英国大约有一百年的时间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英国后来增长缓慢不能归因于任何英国性格所固有的特征。事实上可以证明,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并未有过现在那样明显的阶级差异。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公认: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可比较的地区相比,社会的流动性特别强,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社会各个阶级都关心商业、生产和经济利益,而当时英国的邻邦却都卑视这类职业。
“ 当时的英国社会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开放。不仅收入分配得比海峡对岸更为均匀,而且阻碍流动的关卡较少,对身份地位的限制也更为放松 ……
“ 看来似乎很清楚, 18世纪英国的商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比,显得异常有朝气和活力,对改革十分开放 …… 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比英国更大地满足商人阶级的欲望 ……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的决定比英国更少受到权威和习惯势力的无理约束 …… 有才能的人都纷纷从事商业、实业和发明创造
“ 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 …… 对商业的兴趣促进了不同地位和阶层人们之间的交往,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无与伦比的。
“ 在商业之内企业家的流动就更加自由了,资源分配比其他国家更为灵活。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传统的职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仍然占统治地位 …… 而英国的补鞋匠不会死抱着鞋楦头,商人也不只盯着自己的一宗买卖 ……
“ 除了英国之外,欧洲的商业仍然是一种阶级活动,只能由习俗或法律限定的小集团内补充新人。在法国,商业在传统上被排除在贵族地位之外 ” 。
毫不奇怪,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 “ 小店主 ” 的国家,甚至亚当 · 斯密在抨击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时也认为使用这一名词是中肯的。
普遍的观察表明,欧洲大陆目前的阶级结构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比英国更为灵活;这就是暗示我们应该探寻欧洲大陆如何比英国更快地消除阶级壁垒的过程,或者反过来探寻在英国如何形成或筑起比欧洲大陆更多新的阶级壁垒的过程,或两者兼而有之。
(七)
使欧洲大陆中世纪社会结构只留下一丝遗迹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结构与当今发达世